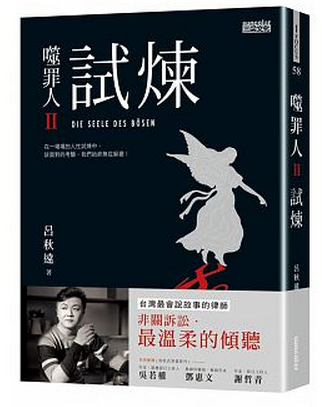多大的夢想,值得用性命去交換?現實的殘酷與人類的無情,又是誰來該接受責難?
她搭上這班前往台北的火車時,嘴裡哼的歌,是林強的〈向前行〉;心裡想的事,是爸媽流著的淚。她一定要上來台北,躲開這個窮鄉僻壤的惡夢。在這裡,永遠就只能像是爸媽一樣,一輩子沒出息。他們家信仰的主,雖然讓爸爸戒了酒,但是卻沒能讓媽媽的病好起來。醫師說,還得要一筆很龐大的醫藥費,才有辦法進行手術,光是靠她國中畢業以後的收入,又能怎樣? 她離開了原鄉,無所畏懼的往前進。她在台北的朋友告訴她,只要上來台北,她這樣姿色的女孩,隨便都有辦法在一、兩年賺上百萬。她,從小就是大家喜歡的漂亮寶貝,現在十八歲,但是已經有一百七十三公分。又因為是原住民,所以臉部輪廓很深,但是膚色卻是出色的白。一頭黝黑的長髮,從小學就開始留,散落下來就像是發亮的黑色瀑布一樣,或者就像是「柳絮因風起」,也是爸爸最常稱讚她的優點。
她腦中編織的淨是台北的風光。只是這風光,很快就到盡頭。她的第一晚,就住在朋友家,這時候她才知道,原來她的朋友,在林森北路的酒店上班,她朋友之所以要她北上,就是她的經紀人請她「廣發戰帖」。朋友再三向她保證,不用脫、不作 S(sex,指性交易),很快就可以存下百萬。她猶豫了一個晚上,心想既然不用跟男人做那些事,應該也就無所謂了。善牧的主,不會讓她迷失的,也會把她這頭羔羊找回來。 她忘了問,如果真是如此,為什麼她的朋友已經上來三年,從沒回去過。
她朋友的經紀人又年輕又帥,雖然是漢人,但是竟然會講幾句他們家鄉的原住民語,應該是朋友教他的。他那不標準但充滿誠意的原鄉話,經常逗得她們開心大笑,忘了被酒客上下其手的悲哀,以及每天茫醉到吐的無奈。況且,第一個星期,她就領到了四萬多元,比起她過去在小七打工的月薪還要高。 她屈指算算,一節一百六,如果一天有一個小框,那就有二十二節;框到底,就有四十六節;她是新來的,每桌客人幾乎都喜歡點她上台。
只要陪喝酒、唱歌,一天就可以有五千多元,朋友果然沒騙她!即使,她幾乎每天都是抱著那隻爸爸送給她的泰迪熊,含著酒意與眼淚睡覺。如果她還沒喝醉,如果她還記得什麼是眼淚。 她每天要上班前,都會記得打電話給爸媽,告訴他們一切都很好。她在夜店當業務行銷,成績也不錯,應該不久以後就可以升上經理。有好幾次,宿醉都還沒退,但是她忍著頭痛,還有昨晚男人在她身上磨蹭的屈辱,告訴他們,工作很開心,有一群好朋友。爸媽總是很欣慰,也告訴她在台北一切要小心,人心很複雜,不像是我們原鄉這裡。
她第一個星期,就把薪水的四分之三匯到爸爸的帳戶,說是要孝順他的。爸爸急著說,這是她的錢,沒有人可以動,包括他自己,他會幫她保管到嫁人那一天為止,家裡不缺錢。 白天,她永無止境的睡覺,因為她不知道晚上會面臨什麼狀況。就像是那天晚上,她被一個客人框到底以後,買了全場去吃宵夜。她以為就真的只是單純的吃宵夜,況且還有一個姊妹跟著,應該沒問題。 沒想到,那兩個男客人,竟然帶她到所謂信義計畫區的「豪宅」。
那真的是豪宅,她一輩子沒見過,家裡竟然可以有游泳池。她從來只在電影裡看過,豪華的吊燈、數不清的房間、高貴的壁畫,讓她這個鄉下來的女孩,覺得自慚形穢。她連踏上房間的地毯,都深怕會弄髒這種奢華白,而猶疑著沒能行動。 男客人有點喝醉,問她要不要游泳?她有點怕,囁嚅著跟他說,「沒有帶泳衣。」,男客人竟然一把就把她推下水,看著她載浮載沉,哈哈大笑。她喝了幾口水,酒意全醒,趕緊把旁邊睡著的姊妹叫醒,逃也似的離開那間豪宅,她只聽到他們在背後放肆的訕笑。
回到租屋的地方,她不可抑止的大哭,「我好想我媽媽,我好想回家。」。她的經紀人,聽到酒店幹部回報,立刻趕到她的住處。看著她手腳到處都是瘀青,心疼不已,把她一把擁進懷裡,跟她說,「我明天去找他們算帳。」 在台北,已經沒有人這麼關心她了。她覺得這男人是真心對她好,所以決定,當天晚上就搬去他家裡。 總算有人照顧她了?是的。因為他帶著她,一起用安非他命。他告訴她,這可以讓她忘記許多事情。連做愛,都會特別容易到高潮。 他對她真的很好,出手闊綽,她再也不必上班,只要陪他做愛與吸毒就好。
延伸閱讀:親切是有界限的,遇到職場性騷擾怎麼辦?
那天凌晨,他神祕的拿了一些藥丸與水,要她一起用。她問了他,這些東西是什麼?他沒說什麼,只是笑著說,這會讓她很開心。 服了藥、喝了水以後,他們瘋狂的做愛,就像沒有明天一樣。但是,就在高潮以後,她突然失去了知覺,身體也開始僵硬。男人慌了手腳,摸了她的脈搏、呼吸,發現似乎沒有任何反應。 她死了?怎麼這樣? * 女孩醒過來的時候,她發現自己已經在深水中。她已經顧不得自己還很暈眩,急著要抓住些什麼,然而卻不自主的吸了幾口水,嗆得她更想呼吸到新鮮空氣。然而,張大嘴巴,卻只有河水不斷湧進。她的鼻子則是不斷的進水,讓她更難忍受。她想抓住水草、木板,什麼都好,雙手亂揮,但是什麼都沒有,雙手能抓住的,只有冷冰冰的粼粼河水,和那一抹皎潔的月光。 她的心中開始浮現爸爸的笑,媽媽的臉,過去十八年來的一切,就像跑馬燈一樣,掠過她的腦海。
她決定放棄掙扎,因為腦袋好重,呼吸好費力,她想離開這沉重的身軀了。 再見,我最親愛的你們。 * 新北市有許多聯外橋樑,橋下則是河濱運動公園。近年來,因為自行車運動盛行,市政府將許多小徑規劃為自行車道,一大早就有許多民眾騎自行車或者運動。 那是一個星期一的早晨,大約五點許,天還矇矇亮,一位老伯騎著自行車經過河堤,這條道路,他已經走了數百個清晨。然而,他遠遠的就看到,一個蒼白的身軀浮在水面上,衣著整齊,而河堤旁,就是一雙鮮紅色的高跟鞋。 * 這個爸爸,臉部的線條非常堅硬,就像是賽德克族人要赴死前的表情。媽媽只能乾嚎,我想,是因為眼淚早已流乾,只剩下血而已。
我看著判決,檢察官以殺人罪起訴這位被告,但是一、二審的刑度竟然都只有一年十個月。因為地方法院與高等法院,都相信這應該是過失致死罪與遺棄屍體罪。 我還不懂案情,與這對夫妻的悲哀,但是我一眼就認為這兩個判決是有問題的。我簡單的向這對夫妻說明,「這兩個判決的邏輯不通,因為你們的女兒是生前落水,如果是過失致死的結果發生在落水後,這位被告怎麼會有遺棄屍體的問題?他把你們的女兒丟下水時,她可還沒死,怎麼能算是『屍體』?」 顯然的,他們聽不懂。只是一股腦的向我鞠躬,媽媽甚至想向我下跪,只求我能把對方繩之以法,讓法官以殺人罪判處被告死刑。然而,我心中想,這個題目的難度也太高,都已經二審判決,而且兩個法院的看法都一致,我怎麼有辦法說服最高法院發回更審? 最嚴重的問題恐怕還在於,他們竟然已經與對方和解!
我翻閱二審的判決書,問他們到底發生什麼事情。「如果你們不同意法官的判決,認為是殺人罪,怎麼會想跟殺害女兒的兇手和解?」,我皺著眉頭問他們,看來案情真的很不單純。 「我不知道!」爸爸說。「法官與我們的律師一起告訴我,如果不和解,我什麼都拿不到。法官說,對方已經願意給我們五百萬,如果我們不同意,他只能依法判決,這個禽獸只有二十歲,就算是判決贏了,我們也拿不到錢。不如現在就和解,還可以拿回來一點錢。」,看得出來他渾身發抖。 「我同意和解,但不代表我願意原諒他。他殺了我女兒,到現在都還只肯承認是誤殺!」,他憤怒的說。 「唉!」,我只能嘆氣。
因為和解,在法律上的概念,就是原諒對方。對於這對夫妻而言,如果知道拿了五百萬元,換來的就是他們的正義,恐怕他們會心死。 「我只能盡量。」我說。最高法院很快就發回更審。倒不是因為我的法學素養豐富,而是在二審的判決中,法官並沒有查明,究竟為什麼「過失致死」的結果是在水中,但是遺棄屍體的時間點竟然是在溺水前。既然死亡在水中,被害人在溺死前當然不是屍體,被告所為,也就不會是遺棄屍體,這判決在邏輯上有明顯的錯誤。 * 高等法院很快又再開庭。然而,不要以為正義在被害人身上,一定可以得到伸張。
因為,我國的刑事訴訟法,對於被害人而言,只有在場權,沒有參與權。簡單來說,在刑事訴訟的審判程序中,主角只有三方,法院、檢察官、被告(包括辯護律師)。被害人或許可以「表達意見」,但也就只能表達意見而已,除此之外,聲請調查證據、詰問證人等等,都必須仰賴檢察官才能進行。然而,檢察官並不是被害人的律師,不可能照著被害人的想法去做。 被害人即使聘請律師,擔任告訴代理人,在法庭程序上,一樣無力。
法院開始準備程序,檢察官表示沒有需要調查的證據,而法官倒是希望可以就犯罪事實訊問被告。他一頭金髮,相當鎮定。 「當天,我發現她自己嗑藥過量,我有立刻檢查她的呼吸跟心跳,當時她的身體已經僵硬,我認為她死了。所以我把她移到橋邊,但是我不知道那裡會有漲潮的情況,所以她後來淹死了。我知道我要負責,而且我也賠錢了。」他說。 法官繼續問,「那麼你為什麼要擺一雙高跟鞋在堤防邊?」 「因為我想要製造她自殺的假象。我以為她死了,會跟我有關係,如果是她自殺,跟我就無關。」,他倒是回答得很快速。
法官看起來似乎沒有問題了,但是女孩的爸爸,一直想站起來發問。我努力的制止他,因為程序上不能這麼做。 法官看到這位父親的掙扎,告訴他,「最後會讓你作陳述,不用擔心。」 「我不擔心!我是傷心,他殺了我女兒,良心會安嗎?」他嘶吼著。 法警緊張的要他安靜,現場突然只剩下媽媽的啜泣聲。「對於法醫的鑑定報告,認為死因是溺斃,兩造有無意見?」,法官繼續進行程序。 辯護律師與檢察官都很快的回答,「沒意見。」 「我有意見!」爸爸又站起來。 法官皺著眉頭,「我知道你很傷痛,但是畢竟和解金也已經拿了。這件事情可不可以交給法律處理?你如果繼續破壞程序,我們可能要請你出去!」 他跪下來,趴在證人席前面哭泣,「我不要錢,我是被騙的。」
我心中百感交集,怎麼會沒有人告訴他,收下和解金,其實就是同意和解? 我跟法警把他扶回座位,我再三向法官保證,他不會再「破壞秩序」了。 他的眼神很紅,幾乎就像是燒焦的木炭一樣,無奈的是,淚水也無法澆熄這場大火。 法官快速的完成調查證據程序,檢察官與辯護人都回答:「沒意見。」,書記官則以飛快的速度在鍵盤上敲打,剪下來、貼上去,完成了一篇漂亮的筆錄。審判程序終結,法官也定了宣判期日。 辯論結束,被告飛也似的離開法院。父親只來得及在他背後高喊:「天主不會原諒你這個罪人的!」,他的喊聲,迴盪在法院的迴廊中,久久不散。
這時候,我想起了《流浪神狗人》這部電影。故事支線中,原住民尤勞尤幹因為肇事導致人命傷亡,非常沮喪,冷酷沒血淚的律師到警察局,要求尤勞尤幹否認因為閃躲小狗而肇事,堅稱是對方超車所導致的結果。尤勞尤幹照作了,然而卻引起教會牧師相當不滿,他激動的對尤勞尤幹說,「你這樣作,天主不會原諒你的。」;然而尤勞尤幹卻也生氣了,他對牧師說:「我不在乎天主是不是原諒我,我只在意我的兩個寄養在別人家的小孩,不會因為我肇事而回不來家裡。」;尤勞尤幹說,「我戒酒,上帝有看到嗎?我認真工作,上帝有看到嗎?如果有看到,為什麼要讓我這樣?」;牧師當下很憤怒的說:「這是上帝給你的考驗。」;尤勞尤幹回嘴說:「我不需要上帝的考驗,我需要我兩個小孩回家。」
他的孩子已經不能回家了。而司法又能給他什麼?而究竟,這是誰的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