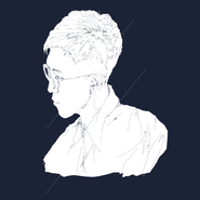為零食分配不均就把家裡的東西砸爛、自己跌倒卻怨恨是媽媽害的⋯⋯兒童精神分析師 Klein 說過,面對難以排解的負面情緒,小孩會卯足全力地表達怨恨,這反映出幼年精神病之典型攻擊特徵。小孩的成長本身就多少帶有反社會與犯罪傾向⋯⋯。
我們與精神病的距離
上一篇文章,筆者在難以區分的群體與個體之間,給出「我們與惡的距離,只是一種錯覺」的回應,而今天我們將以另一個角度出發。從轟動一時的鄭捷事件、小燈泡、到《我們與惡的距離》(下稱《與惡》)中「惡」的主題,都是由精神病及隨機殺人所造就的社會創傷。為此,也許我們要先繞道而問:「我們與精神病的距離,有多遠?」
人人都有過的幼年精神病
成長,只意謂著我們以相對文明的方式來承載及應對早期生命階段的特質,尤其是「幼年精神病(infantile psychosis)」。相信每一位媽媽都能作證,即小孩面對各種挫折,總是以肢體動作來宣洩,用一般成人的「合理性」來看,其行徑絕對是「不文明不道德」的:為遲到一分鐘的奶而哭鬧、為零食分配不均就把家裡的東西砸爛、自己跌倒卻怨恨是媽媽害的、無法得到玩具就在百貨公司的地板打滾、為了買自己喜歡的東西而去偷父母的錢,甚至直接在店家偷竊⋯⋯。
相對地,若對自己的童年夠誠實,或在臨床經驗中發現的,受挫折的小孩其實早早學會以滿腹恨意來反擊,(我)他們心中能夠抱持著「折磨與殺害」他人的幻想(一般指向父母)。誠然,為獲得滿足,有些小孩很清楚以怎樣的方式折騰重要他人。所以很簡化地定義「文化」,就是忍受挫折,延宕滿足,且讓「良心道德」把隨憎恨而來的「反社會傾向」潛抑、轉向、昇華。
惡/反社會傾向,從無法言傳的痛苦中萌芽
被各種挫折與不適感包圍,缺乏語言、僅有原始的心理防衛應對⋯⋯這都說明了在生命早期,每一個人都經歷過難以置信的主觀苦痛。小孩恨使他們受挫的照顧者,各種可怕的幻想(吃掉、糞便、毆打、碎屍萬段等)油然而生。若沒有得到修復的愛,未來可能會轉化成實際的犯罪行為 [1]。兒童精神分析師 Klein 說過,面對難以排解的負面情緒,小孩會卯足全力地表達怨恨,這反映出幼年精神病之典型攻擊特徵。
由此可見,小孩的成長本身就多少帶有反社會與犯罪傾向,一再以孩子式的實際行動表達。但同時,他們也深怕父母會殘酷地報復或懲罰他們的攻擊幻想,常見的懲罰恐懼莫過於「不再被愛/被丟掉」。為此,在幼年精神病中,小孩被強烈的攻擊衝動與被罰焦慮包圍,往往無法獨掙脫這種惡性循環,逼近反社會傾向所引致的犯罪 [2]。
忽略照顧→反社會傾向
在諮商工作中,我看到許多臺灣上一代的家庭都有著忽略照顧的問題。一位個案 W 是家裡的獨子,因為父母要忙生意,所以他從出生起就交由外婆帶大,直到三歲才回去跟父母生活,卻發現父母依然忙於工作,所期待的家庭溫暖從未到臨,他便一個人躲在店鋪後面的房間長大。同樣的,《與惡》的李家父母也許沒有家暴或婚姻問題,但忽略照顧本身的確可能造就孩子的精神健康問題 [3]:李媽媽坦誠她太自私、太忙,忽略去照顧李曉明,使他不滿於情感的現實。

圖片|《我們與惡的距離》劇照
個體的情感成熟是從情感依賴開始的,若早期生命缺乏跟父母間的情感連結,在臨床上,孩子內心萌生的憤恨會遠比表面上看得到的更強烈。孩子也試將憤恨導入可怕的幻想之中,因為逃離現實的幻想是他們的避風港,且不讓幻想去配合現實,即他們很擅長隱藏內心極大的痛苦 [1]。李曉明,或其他的隨機殺人者,都是這樣長大的嗎?
除了幻想,忽略照顧所造就的精神健康問題,還有情感遭剝奪以後的「反社會傾向(anti-social tendency)」。遭受剝奪後的負面情感會引發妄想,此時人們會把攻擊性轉以尋找和破壞這個迫害來源的妄想系統 [3]。好比 2016 年震驚全國的內湖隨機殺人事件(小燈泡事件)中,罹患思覺失調症的王景玉說道:「要找一個四川女孩傳宗接代,還要找女孩,要殺了她。」[4] 這或許說明了小燈泡誤成為王景玉的迫害妄想來源,他認為只要殺一個女孩,他就可以有後代。
延伸閱讀:【心理學解析】從鄭捷到小燈泡 ,當「有問題」的人消失了之後?
到底他們為甚麼要隨機殺人?
《與惡》沒有回答「李曉明,他到底為了甚麼而殺人?」,那我們只好繼續靠精神分析的經驗,試著釐出真相!社會大眾一般認為罪犯、反社會傾向者、精神疾病患者等,是沒有良知的,在幾宗隨機殺人事情以後,這種看法也變得無可厚非。但在臨床經驗中發現:
「再小的小孩,都努力地對抗自身的反社會傾向⋯⋯而在最具虐待性的衝動出現後,他們會表現出最大的愛意,以及不惜犧牲一切以獲得關愛。」(Klein, 1927)
Klein 認為所有小孩都遭遇過恐懼與罪疚感的煎熬,而一般人不理解的是,從童年的內心痛苦發展為外顯的犯罪行為,並不是沒有良心道德(術語上稱「超我 super-ego」),卻是良心的運作方式異於常人。即他們心裡其實充滿了恐懼與罪疚感,但所表現出不在乎處罰與無所畏懼的樣貌,完全誤導了我們。
失去了良心?或是有著嚴厲且絕對的良心?
犯罪傾向不是因為良心的寬容所造成,而是來自運作方式可怕的良心:遭感情剝奪的小孩隱藏對父母的恨意,但其良心仍然對此作出恐怖的譴責,在巨大的焦慮與妄想中,個體可能會被迫去傷害他人,這種難以抗拒的衝動就是犯罪行為或精神病的發展基礎。事實上,在傷害他人時,個體其實是在防止侵害極愛又極恨的親人,即所謂逃脫伊底帕斯情結。
世界只剩下敵人,這正是罪犯心裡的感覺 [2]。在犯案當下,由於個體已經處於持續的迫害壓力下,他唯一的考慮只是個人安全,因此他視自己的侵害行為具有絕對的正當性。所以,犯罪傾向不是外界認為的缺乏良心,反倒是這個良心過度嚴格而絕對,才導致違反倫理道德、反社會的罪犯行為。
最後的希望:讓社會知道自己被剝奪的事實
表面上,罪犯缺乏人類與生俱來的善念,但臨床工作中我們發現:
「當一個人碰觸到恨與焦慮的根源處所產生最深的衝突時,他會發現那裡也存在著愛。罪犯身上的愛並沒有消失,卻以這種方式被隱藏、埋葬起來」(Klein, 1934)
前文提到遭情感剝奪的小孩,內心其實既對父母有攻擊幻想,又恐懼被報復,為此,他們為了處理此罪疚感,會去作更多的惡來換來處罰。這在於真實世界的處罰,總是比從父母來的懲罰(失去愛)來得不可怕與安心,一如鄭捷和《與惡》的李曉明都一心求死刑──而筆者推想,李曉明一直不願意跟家人見面的原因,也許正在於否認對他們的傷害,以及逃避想像的懲罰。直到他知道家人因為自己的行徑而受苦時,即認清自己真的深深傷害了所愛的人,衝突中的愛才被重新點燃,使他終於答應跟家人見面。同樣,對所有罪名供認不諱的鄭捷強調「我不會後悔」而拒絕向受害者家屬道歉 [5],也許這表示他渴求死刑處罰來處理內在衝突的一面。

圖片|《我們與惡的距離》劇照
隨機殺人,也許對他們而言,是最後的希望:把多年來的內心戰場演活,以讓社會知道自己被剝奪的事實 [3]。他們以反社會行為引起社會的關注,但更重要的是引起於童年忽略照顧他的父母關注。很不幸,也常常是在罪案發生以後,父母才發現自己不了解自己的小孩,才開始關心他有著怎樣的需要。
結論:我們與惡的距離,一如我們無知於惡與我們的距離
在《與惡》中王赦對美媚說:「因為你們這些人遇到這些事情,只有憤怒、害怕,你們膽怯,你們根本就沒有機會去了解他們背後到底發生甚麼事情」,事實上,我們也絕少了解到自己的歷史到底發生了甚麼,我們真正害怕的是內在的瘋狂,才叫我們把幼年精神病的惡切割,把憤怒、害怕、膽怯都一一投射到加害者身上,卻「無知」於他的故事。
組成「人性」的,必然包含生命早年受挫折後出現的惡念與惡行,即反社會的犯罪傾向,不管是對一般人、精神官能症、精神病、或一般的犯罪者來說都是一樣的 [1]。我相信許多家庭的確是無知的,「全天下沒有一個爸爸媽媽要花個二十年去養一個殺人犯」!只是,唯有看見「無知(ignorance)」而為之的惡──情感剝奪、忽略照顧──怎樣造就家庭中一個又一個受苦的靈魂,我們才能抱持希望,找到未來努力的方向。為此,筆者認為:
我們與惡的距離,一如我們無知於惡在我們內心的距離
一如小燈泡的母親表示「政府應該要從根本、從家庭從教育著手!應該讓這樣的人(隨機殺人者/受苦的小孩)消失在社會上。」[4] 本文也不認為只用「眾生皆有病」的方式,卻應以「朝向精神健康」角度來看社會 [3]!讓我們從家庭起步,使每個小孩都不受情感照顧的剝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