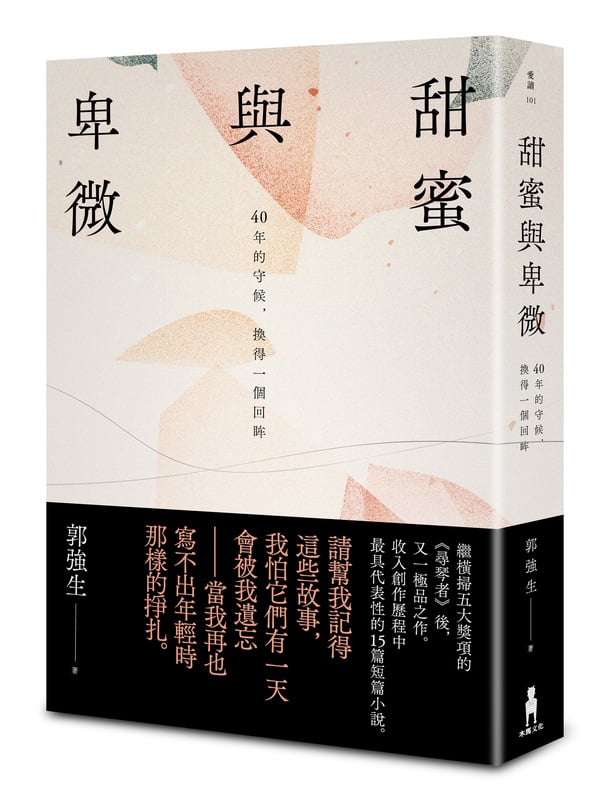郭強生的〈等待的女人〉,描寫狩獵愛卻也期待愛的女子。當她以為將對方玩弄於股掌之間時,怎料自己不也正陷入對方的掌控中?
文|郭強生
等待的女人
收錄於《希望你可以這樣愛我》(一九九七,已絕版)原名〈可以這樣愛我嗎?〉
羅薇的首次攝影展是在一棟施工中的大樓內舉行的。建設公司因為財務糾紛遲遲未能交屋,一座水泥恐龍孤單地成日站在寸土寸金的台北市中心,羅薇每天經過都要駐足向牠行注目禮。
十層大樓一扇扇窗口都還只是混凝土牆上挖出的洞,沒有窗框,沒有玻璃。羅薇一回爬上了頂層,站在窗洞邊朝下望,感覺自己的生命也是如此不整全,像這座永遠完工不了的建築,當初設計師的夢想與期待,現在彷彿已註定是空。
那就拿我的照片來填補一下這兒的空洞吧,羅薇心想。也許有一天,這座半廢半興的建築會成為台北許許多多邊緣藝術人的家,一種新的座標,因為未完成,所以才有空間去接納。
羅薇的作品展出後令藝評家震驚。
掛在一面面彷彿水泥都還未乾壁牆上的,全部都是她的自拍照。影中的她幾乎都是全裸的,有的在胸前綁上禮品似的大緞帶花,有的頭上裝飾了白絨絨的兔子耳朵,有一幅甚至在口中含啣了陽具模型。
系列命名為,等待的女人。
羅薇靠著為幾家時尚雜誌攝影養活自己,專拍那些瘦扁如柴的女人穿上各家名牌服飾。模特兒們努力地在開麥拉前擺出各種姿勢,但是她們的眼神卻都是如此的空洞。
她們的身體可以做各種角度的扭曲,但是羅薇從她的鏡頭看出去,她們注視的目標都是一致的。
總希望有某個男人在看著自己。
這樣的假想,令那些搔首弄姿的女人期待卻又不安。現場並沒有這樣的男人,所以她們的目光總是模糊無依。每次版面打樣出來,羅薇看見畫面上的女人搜索的目光都溢出了紙張,在翻頁的手指間流失。
不知從哪個年代起,女人早都忘記了狩獵的眼神,無力讓自己的慾望對焦,只剩下這樣無助的召喚。
首次個展大膽地挑釁了男性目光,也嘲弄了同類永遠活在男性注視下的缺乏自覺。展覽還在進行,羅薇已忍不住開始思索,自己接下來該嘗試什麼樣的主題。

圖片|Photo by gilber franco on Unsplash
在她住家大樓對街的收費停車位,總有那一輛雪白的 TOYOTA,在她起床前已停妥,下班時間前會離去。她決定要看看車的主人,於是那個大清早,她提前了兩個小時出門,去展場前先完成了隔著馬路窺察車主的任務。
原來是個中年已微微發福的男人。羅薇起初很失望,但是看見對方臉上平板無趣的表情,她突然有了一個讓自己都要笑出來的主意。
在中年男人停好車離去之後,羅薇在他車窗的雨刷上夾了一則留言:
「每天都在等你,我是一個期待愛的女人。
明天傍晚六點,請到國父紀念館光復南路大門,
我認得你,該是你認得我的時候。」
在展覽會場的這名男子,已經是第三次出現了。
是專程來看某一幅的嗎?會是藝術品買家嗎?看那年紀不像⋯⋯羅薇與他交換了一個微笑,並不擔心對方認出她就是畫面中的女子。甚至當他注視著相片中自己的裸身時,羅薇感覺到一絲靈光如電流竄動起來。
男子理著短短的平頭,高挺的鼻樑上架著一副銀框眼鏡。他喜歡蔴紗質料的襯衫,顯然瞭解自己䠷長的體型適合這樣休閒的裝扮。
傍晚的空樓,氣流沉悶。男子的背上漬著汗,沁過了白蔴紗,羅薇可以看見他背脊中央陷下的部分,那微帶泥土色的肌膚若隱若現。
羅薇穿了件破舊的男用夾克,頭髮用橡皮筋一繫,帶了她的相機來到指定的地點。她在臨近的速食店找著一個靠窗的座位,視線正好鎖定對方可能出現的方向。約莫是六點過十分(竟然敢遲到!)那輛白色轎車果真前來赴約。
羅薇拿出相機,換上長鏡頭,從窗裡瞄準了窗外那個不知道自己已被偷窺,光憑了一個不知名女子留言便躊躇滿志的對街男子。
中年男子竟然還為此新理了頭髮。
羅薇按下第一張快門。男子的眼睛裡閃爍著期待。然後羅薇以持續的速度,拍下了男子赴約的整個過程。
這樣一個準時上下班的男人,對這個盲目的約會是抱著相當高的興趣的。當羅薇注意到他四下搜巡可能的留言女子時,竟有一些些的靦腆和不知所措。他顯然也在懷疑,對方正在觀察自己,等待適當時機現身。
羅薇猜他或許已婚。靠在車門上的他,不太習慣路人的目光,尤其是他的手中還捻了一支玫瑰花。他開始意識到自己作出這樣欠深思的事,並不符合他的身分與年齡。
男人原來也是努力在扮演別人分配給自己的角色。羅薇企圖把焦距再調近些,好捕捉他臉上的細微表情。這個男人並無能力為自己編寫腳本,仍在東張西望的他,不能像女人一樣掏出粉盒來補妝與檢視自己的容顏。他只能單調地站在原地。
十五分鐘過去了,男人開始頻頻看錶。
二十分鐘。
三十分鐘。
男人臉上開始露出了不耐和焦慮。間中有大概長達三分鐘,他曾陷入了空白,眼睛瞪著前方,腦裡在想著其他的事,面無表情地打發了一些時間。當他回過神來,他趕緊伸了個懶腰。
開始有一些憤怒了,他面部線條緊繃,不友善地對所有路人的好奇反目相向。
你是一個可悲的男人,羅薇開始同對街人影說話。你以為今天是上天賜福的一樁豔遇,你以為一朵玫瑰花就代表了浪漫。當期待中的陌生女子出現時,她會毫不考慮地投向你的懷抱。
這就是男人給予女人的全部,羅薇之前就已經預料到這樣的發展。男人不必害怕等會兒出現的究竟是一個醜八怪,還是一個老太婆。他們總是大剌剌地來,無所謂地走。他們甚至事前都不用花太多時間揣測幻想,什麼樣的女人膽敢做出這樣的事。
反過來自己會怎麼做呢?羅薇知道身為女人,她會疑慮,她會害怕,她會想逃,她會想哭—這是一個不敢當面自我介紹的男人,他對自己的興趣隨時可以像撲克牌一樣翻面。
羅薇繼續拍下了男人失落的表情。困惑的表情。疲憊的表情。甚至他還出現了一點苦巴巴求助的味道。
我該出現嗎?羅薇一度不忍。將心比心,她沒有預料到他會等了五十分鐘還不離去。
可是自己這樣邋遢地出現,恐怕只會加劇他的失望。這時候沒有答案可能是最好的答案。但是,如果這時出現的是一位窈窕多姿的美女,他是不是會立刻精神百倍起來?
過程對男人來說不重要,有結果便勝於一切。女人怎麼得來的並不重要,可以用搶,可以用買,可以用騙。等待只是一種手段,並不是一種心情。
女人在等待的時候,繼續愛著對方。男人多數則開始檢討自己的愛。
對街的男人朝地下啐了一口,並擲棄了手中的玫瑰。羅薇發現自己相機裡還剩下最後一張底片,於是準備捕捉他重新坐入車內前最後一個表情。
男人開車門動作到一半,突然整個人僵住了。
羅薇立刻放下相機,她知道他已經懂得了些什麼。

圖片|Photo by Hester Ras on Unsplash
男人猛地轉過身,直直望進速食店裡。他一個一個臉孔瞄過去,羅薇心跳得好急。
雖然沒有具體證據,但是男人已經強烈意識到這可能是一場設計好的惡作劇。他放棄了速食店的現場,變得慌張起來,在街道上跑來跑去,企圖發現任何形跡可疑的人犯。
羅薇錯失了男人最後的鏡頭。那是一張帶著驚恐,對整座城市都充滿了敵意的表情。
連夜洗出了那對街男子的影像,羅薇將它們用夾子在繩索上吊成一串,面對面坐著注視了一晚。
如此真實,真實到像排練過一樣準確,男人的每個表情都充滿了戲劇性,彷彿從開始他就知道鏡頭的存在,於是賣力地表演。
原來等待中的我們,有著這樣豐富的表情。羅薇這樣沉吟思索著。那是一個我們永遠見不到的自己。
羅薇將洗好的照片裝進一只大牛皮紙袋,等待第二天一早那輛白色轎車停在同樣位子,她便可將這組攝影原樣夾在雨刷上送給當事人。
羅薇沒有想到,白色轎車再也沒有出現過。
男人將車停到了一個她再也找不到的地方。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接受等待的結局。也許那個男人這一輩子都要活在那天傍晚帶來的夢魘裡。
作愛之後,男子拾起地上的白蔴紗襯衫重新穿上,發現了不小心被他踢到床腳下的那組黑白照片。
他暫時忘了繫釦,晾著胸膛,就著窗口的路燈燈光一張張瀏覽起來。然後他轉過身對著在床上裹著床單的羅薇笑了起來。
笑什麼?
妳是不是也幫我拍了一組?
羅薇把那天的經過向男子簡單重述了一遍。
為什麼要這樣作弄一個無辜的傢伙?
沒有作弄的意思—我本來想把洗出來的照片送給他。很多人並不曉得,他們本身也可以成為一件藝術。
不是每個人都希望暴露在鏡頭前呀。
你是說,我有暴露狂囉?
不是啦。色情狂可能有一點,暴露狂倒未必。
他們當夜又溫存了一次。男子背上那陷落溝脊的部分,羅薇吻了又吻。當她繼續沿了腰椎一路親吻,快達到男子臀部的時候,對方一個翻身制止了她。
不可以。
男子歉意地笑了笑,又道:我好奇,妳好像不知道世界上很多事有一道最後的界線,不可以越過去的——
傷風敗俗嗎?
太原始的東西會讓人害怕的。
為什麼要怕呢?羅薇心想:當他在看我展出的那些照片時,並沒有一點不自在,不是嗎?難道女人在等待狀態中,才讓男人覺得是馴服安全的?
還有,妳那些讓人不安的作品—算了,我不說你也明白。這樣子妳會活得很辛苦的!
可是男子並不打算停留。當他終於又把白蔴紗襯衫穿好,臨走時想起了什麼,鄭重地要羅薇保證,他不會收到類似的被偷拍的照片。
你會期待我嗎?會想起我嗎?如果不會,那你有什麼值得拍的? !
男子有些動容了:妳要什麼?
我要你——羅薇儘量不讓自己情緒波動,卻發現吐出的這三個字讓她無端感到心虛:——成為我下一次攝影展的主題,來當我的模特兒。我會等你的答案。
等待一點也不美麗—男子嘆了一口氣:我怎樣才能讓妳明白?
停工的樓層如廢墟,出入沒有管制,只雇了一位女工讀生坐鎮展場。事情發生的當下,羅薇記得那女孩尖叫的音量在空間中激盪出巨大迴音。身材矮小的陌生男子丟下還滴著紅漆的保特瓶,逃逸前對羅薇不忘猥瑣地齜牙,
羅薇很鎮定,會有這樣的變態被她的作品挑起厭女惡意,並非完全出乎意料。只是不該在那時腦裡又閃過了那句:這樣子你會很辛苦的⋯⋯
遭破壞的作品中的那個她,包著浴巾,還在對著自己嘟嘴。紅漆正好噴在她大腿部位,染紅的浴巾讓原本諧擬的幽默登時便成了社會版的真實。
羅薇忍住被羞辱的椎心,撿起地上的空瓶,用剩下的漆料朝自己的作品再補上一筆。
接下來的兩個月,羅薇又跟另位三個不同的男子上了床,每一個都讓白蔴紗衫的男子在記憶中又遙遠了一點。
她突然對自己的生活厭倦極了,暫停了下一個系列的計劃,不再旅遊,不再跟陌生男子聊天。某家合作多年的雜誌社請她去上班,不用再跟那些模特兒一起工作,她的名片現在寫的是視覺效果主任。沒多久她便成為了一個標準的、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直到有一天,她忽然接到一包沒有署名的照片。
照片中的人是她自己。
她在等車。
她在過馬路。
她在點香菸。
她在——
還沒看到最後一張,她便將這包東西丟進了垃圾桶裡。主任有愛慕者喲!一旁的年輕女助理邊說邊偷瞄她的反應,最後只得自討沒趣轉身退下。
為什麼會用那樣大驚小怪的語調?難道連什麼是惡意、什麼是愛慕、都無法分辨嗎?
羅薇壓抑著慍怒,正準備拿起紅筆在助理送來的圖樣上做記號,不料那幅被潑漆的作品又浮現在她眼前。
沉思了片刻,羅薇突然被某個令人不安的想法擊中,急急從工作檯前起身。
重拾回那一包照片,回到位子上,她開始一張張抽出,端詳。終於從其中一張的背景玻璃窗反影裡,找到了模糊的一抹線索,舉著相機的男子不知是有意還是無心,也讓自己入了鏡。
原以為,她已不復記得他的長相。沒想到即使是一團霧影,羅薇仍能心痛地指認。

圖片|Photo by Edgar Hernández on Unsplash
為何之前她從沒有懷疑過,男子數次來看她的展出,並非由於業餘的喜好?這是在模仿,還是在嘲弄,她原本計劃中的下一個主題?難道他會將她的系列據為己有?除了對她隱瞞了從事的職業,他還有其他什麼沒說的?
竟然到這一刻她才發現,自己失去的,不只是等待的資格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