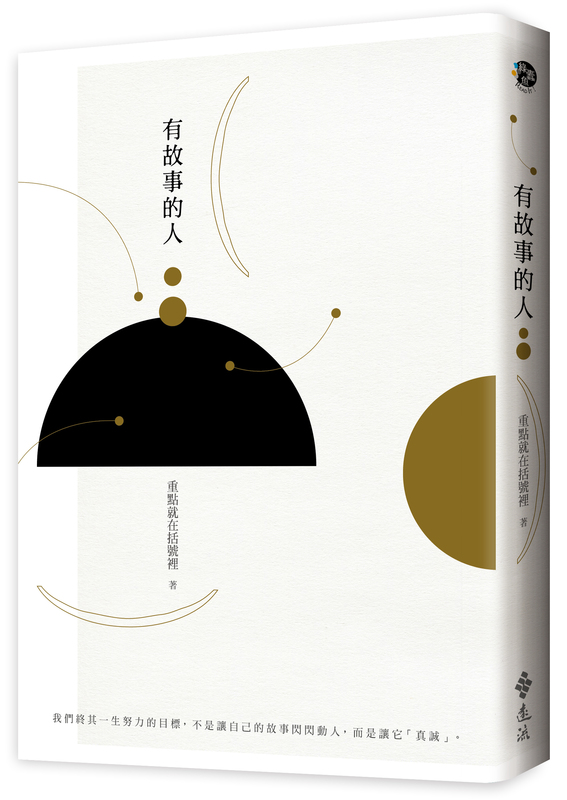用心過日子,每個人都是有故事的人。吳念真導演總能用淺白字句說出市井小民心聲,原因沒別的,因為他說的就是自己的生活、我們共有的日常。
真實的故事
台灣新電影留給現代觀眾最深的印象,是他用自己,深刻了侯孝賢的「鄉村」、楊德昌的「都市」,最後觀眾都能在這些電影裡,透過他,看到自己。
每當他開始回顧著瑞芳礦坑的童年時,他總是會念念不忘一位名為「 條春伯」的工人。
條春伯是村裡少數識字的人,所以,村裡的人如果有需要寫信或是需要讀信的時候, 總是會請條春伯來幫忙寫信或是解釋翻譯( 國語翻成台語)信。條春伯會以自己的方式與話語,轉化村民有時夾雜髒話、有時夾雜毫無重點的日常對話的文字敘述,他會寫成書信上規規矩矩的文字,讓收到信的人很快就能理解,他有時也用自己的方式將信上充滿怨言與憤怒的文字(多半是討錢討生活費),轉化成婉轉但不失原意的口頭敘述講給村民聽。
他覺得條春伯最了不起的地方,就在於用這些淺白的文字,找到真實與虛構之間的平衡,思考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之後,用這種方式真正幫助了不識字的村民。
在他年幼時,條春伯是他心目中的知識份子,這個人深深影響了他,一直到成年後的數十年,已經用「 說故事」 這項天分賴以為生、聲名大噪時,他還是念念不忘著條春伯當年告訴他的這段話: 「你有能力的話, 應該替旁邊的人做些什麼。」
推薦閱讀:吳念真寫給台灣的一封信:世界上偉大的事,都是年輕人弄出來的

圖片|來源
所以,他用「故事」,一直不停地替台灣人發聲。
他做工出身,學商畢業,最後選擇的人生道路卻是文學,就是因為擁有各種不同的經歷,看過太多在身旁發生過的奇特故事,所以,想像出的故事,寫出的故事,形形色色。在他的電影編劇黃金期八○年代,他寫了講述歌舞圈姐妹花的心酸故事《台上台下》,寫了講述退伍老兵的愛情故事《老莫的第二個春天》,也寫下取材於他的母親講述過的鄉里故事《八番坑口的新娘》。
直到現在,故事還是他的生財工具,那是他翻轉人生階級的鑰匙,是他拿在手上準備反擊這世界不公的銳利寶劍,也是他的信仰。編出的每個故事,都是從虛構中反映出真實,把現實生活的社會問題寫在劇本裡,弱勢的、底層的、醜陋的真實,用最淺白的方式,虛實交錯,透過電影放映機的光照射在黑暗銀幕上的同時,傳達給觀眾似簡卻深的道理,因為他用故事包裝著,他想說出口的真相。
而他的本事在於,不論什麼樣的環境與時代裡,總能說出貼近人心的故事。
我們都知道,故事的基本元素是空間、時間、角色、情節這些可變可動的因素,但是,喬治.盧卡斯曾經說過,從古至今,所有的故事類型其實一共只有二十五種,再怎樣厲害的花稍變化,都只是在前人原有的基礎上做出細微進步。千年前的「 希臘悲劇」 與莎士比亞的「 四大悲劇」,到了二十一世紀風行的漫威《復仇者聯盟》 電影系列與飆車電影《玩命關頭》 系列,都是在用類似的方式說著相似的故事,而每一位說故事的人的差別就在於,如何在虛構的故事裡頭,放進自己觀察到真實的「細節」,讓你感動讓你哭。
推薦閱讀:吳念真、阮光民的創作哲學:生活不用筆記,會忘記的事就是不重要
所以,他將自己真實的細節,放進「台灣新電影」裡。
身為上個時代台灣新電影的推手之一,他在全台灣最不可能創新與改革的國營電影公司,與當時的總經理明驥明老總,與總是會互相鬥嘴的作家小野,一起在全台灣電影院戰場的西門町,矗立在人潮最多的廣場那幢「 中影股份有限公司」 的辦公室八樓,每天絞盡腦汁,不停地構思企劃與故事,努力與當時台灣的風氣連結,試圖以電影反映當代人的真實。
事到如今,台灣新電影留給現代觀眾最深的印象,是他用自己,深刻了侯孝賢的「鄉村」、楊德昌的「都市」,影響了後輩的電影人。
侯孝賢說,他的筆名來自於他的初戀情人, 告訴自己「 不要再掛念阿真」 , 雖然像是要告訴自己「 已經錯過的事物就不要再留戀了」 。但是這也像是太過留戀, 所以要把她的名字放在最醒目的地方, 跟自己永遠相連在一起,變成這個被譽為「全台灣最會說故事的人」的象徵。
這個筆名的意義是前者還是後者, 他曾經公開說明過幾次( 妹妹投稿時幫他改名「 念真」 , 後來想改筆名報社告訴他「 前面加個『 吳』 就行了啦」),這個故事發展至此,也被侯孝賢拍成電影《戀戀風塵》。
但是他說,當他第一次看完電影成品卻有些困惑,因為這樣的故事對他的「真實」來說非常「 不真實」,看著被虛構過後的事實,產生一種意識錯開的既視感,但是這樣的故事卻一直不停地在兩人之間的合作出現。

圖片|來源
他跟侯孝賢合作多次,從一開始的《兒子的大玩偶》到最後的合作用他真實的虛構,回顧父親人生的自傳電影《多桑》,將他的「鄉村故事」 化成一種「寓言」,觀眾總能在其中找到,我們曾經發生過但已經被遺忘的細節(不擅言語的父親之愛, 從來不曾說出口的「 我愛妳」),因他的過去而感傷,因他的細節而懷念。
在楊德昌不長的電影生涯,他替他的第一部長篇電影《 海灘的一天》編劇( 也演出了一個客串性質的角色「 公司職員」),一直到他最後一部電影《一一》,他擔當了這部電影的主角,這個一開始就以他為本的角色「NJ」(連英文縮寫都一模一樣)。
他說,當楊德昌找他來演這個角色時,原先想推掉,他沒有辦法擔當電影主角的大任。但當他知道,楊德昌是觀察到他疲累的一面( 當時在忙台灣電視圈開始風行「 台灣鄉村行腳節目」 的濫觴《台灣念真情》 ),看到他對世事萬物那種無可奈何的態度,所以決定找他來演這個社會常見的普通人,聽完理由之後,他點頭。
在電影《 一一》的開頭,NJ 在婚禮中回家拿東西,但卻忘了自己要拿什麼,下樓之後再上樓,苦思著「 我到底要幹嘛啊」,最後,什麼東西也沒拿就回去了。這個總是忙到忘東忘西的中年人樣貌,是楊德昌對他最真實的細節描寫,也是楊德昌想要在他的真實裡,放上當代忙碌都市人的共同象徵:我們總是不停地錯過,錯過了家庭,錯過了愛情,最後,錯過了人生。
他的這些真實,激發了台灣新電影,激發了侯孝賢與楊德昌的思考,最後都留在他們的電影裡面,最後觀眾都能在這些電影裡,透過他,看到自己。
關於自己,他寫小說,寫電影劇本,當中影公司的編審,當電影導演,當節目主持人,拍膾炙人口的廣告,想出簡單好記的廣告對白,他忙的事情太多太多,事業有成功也有失敗( 第二次執導的電影《 太平・天國》 票房與評價不比第一次執導的電影好),而自己的人生,有高峰也有低潮,有時,他會用故事記錄這些過往。父親的人生,他拍成電影《多桑》,弟弟的離世,他寫在散文集《 這些人,那些事》裡,用故事的方式,記錄這些真實,記錄自己的情感。
十幾年前,在他第一次執導舞台劇《人間條件》時,在出版發行的劇本書前言寫著,他認為自己不是知識份子,只是一個說故事的人,在「 商業跟藝術」之間, 他覺得自己是偏向商業,就像日本每年都會拍出一兩部《男人真命苦》來維持松竹電影公司收入的導演山田洋次一樣,他們都會在這些簡單直白的劇情裡,用喜劇,用悲劇,寫下對人性的觀察,最後,描寫出最真實的「人」。
二十一世紀初, 他從電影跨足舞台劇, 他寫出一連串關於「 台灣家庭」 的舞台劇本《人間條件》 在台灣一連上演十幾年,從第一部寫到第六部,舞台劇的名稱取自於日本名導小林正樹的反戰人道主義電影《人間の條件》,這個五十年前的電影系列,當年拍到故事的第六部就完結,然而,五十年後,這個台灣的「國民戲劇」,卻不甘只停留在第六部。
推薦閱讀:不確定是一件好事!哈佛校長福斯特的畢業演說:「用你的人生,說一場新鮮的故事」
可能就像他的筆名一樣吧,雖然告訴自己已經錯過的事物就不要再留戀了,但是,它放在記憶裡,總有一天就能透過虛構的文字,把它轉化成真實的感情,表達出來,散播出來,就像當年條春伯告訴年幼的他,這是他的天分,也是他的責任。
他的筆不止歇,故事還會繼續說著。
吳念真
一九五二年出生,本名吳文欽,畢業於輔仁大學會計系夜間部,曾連續三年獲得聯合報小說獎,並獲得第十屆吳濁流文學獎。一九七八年開始創作電影劇本,一九八○年進入中央電影公司擔任編審,「台灣新電影浪潮」的推手之一。
近年事業重心轉向廣告拍攝、執導舞台劇,及紀錄片配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