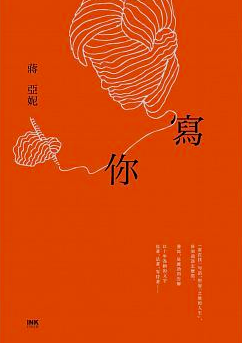迷人書摘,《寫你》裡頭的花季末了,原來我們都在消逝的青春裡,學會了遺憾的技能。
年輕與不再年輕,是猝然的,就是一早醒來你發現與年輕時的自己隔著海也隔著島,那樣一場睡眠的時間。
說穿了都是時間,讓年輕變得秒秒金貴。年輕時間裡的朋友,有個酷似年少周慧敏般靈動光鮮的女孩,她張著接植睫毛後水光洶湧的眼,水煮蛋般亮潔的臉龐,不擦唇彩也粉潤的雙唇說著她在 28 歲生日清晨醒來,發現了兩撇法令紋的悲傷。像是這樣的感慨,在仍然年輕的時間裡還是經常出現,我明白青春的不再永遠都是感傷的,連只是可能不再都能令我們如此傷感。但誠實面對長長的青春,我們揮霍的也該足夠了,預支完一生能熬的夜晚後,該學著面對揮霍和做些放下書本和鏡子後的事。
比如面對遺憾。
即使在年輕的時間中生長,仍然沒有人無法不帶著遺憾往前,像是遺憾沒有活在舊的想像之中、遺憾沒有和平、遺憾沒有趕上搖滾樂出生的時代,遺憾嬰兒肥才剛剛褪去就想念了。我們在時間中學會遺憾這個技能,但直到現在我才明白它的不好與它的好。
推薦閱讀:燃燒的搖滾魂!專訪張鐵志:「成功不必在我,我能做的是持續走在路上」

圖片|來源
故事是這樣的。
我出生在 1987 年,民國 76 年,很多這一年出生的朋友都會說上一句,也是解嚴那一年。但其實我們全都沒趕上解嚴,我在一月出生,那年的七月十五日宣布解嚴,在之後長長的歷史解鎖時程中,我還是一個嬰兒、一個女娃、然後一個半大的孩童,才變成了我。變成了擁有閱讀與辨識能力的我,也已離解嚴年代翻過至少十年。對於歷史課本裡的幾組名詞,多半無感它們與我的距離太近,再也沒有老師對於學運、二二八、解嚴、精省這些名詞感到陌生,也不會感到不自在。
時間再推。20 歲前後的我,開始感到一種迷惘和巨大的不安,那年我還沒轉讀文學,在一座山頂大學裡追逐一種惶惶不安的新聞夢,從美國、日本的新聞史,我終於看到了屬於自己國家的新聞史和新聞危機。鄭貞銘教授、高信疆先生,多少臺灣新聞史中的名字,隨我在大成館後的系館成長,但卻沒有滋長至心底,我終究並不適合成為無冕王,放了自己與青春一馬,走向文學。但因此對於所有錯身的歷史感到遺憾,像是對馬世芳書中解嚴年代的激情青年、搖滾樂傳說的年代更是如此。更早的大江大海、眷村尾巴,更是見面不相識了。面對76年的解嚴我無法書寫屬於自己的記憶,但對於時間的遺憾,並不只從這裡而來。
在我童稚的眼睛裡,其實也攝下了許多重要的場景和年份,只是總以年幼的斑駁眼光和父母們過於溫溺的聲線訴說著。
1996 年,民國 85 年的 3 月我第一次出國,去香港。對於飛機的形狀和除了父母外同行的人無一印象,但記得父親開車往桃園的路程裡,幾個大人對談著因為出國而將錯過的第一次總統民選,聲線拔得很高,我在後座趴著往後方的公路望去,灰沉沉的公路和鴉青色的天光,車飛般的往北開著,我回望家的方向終至看不見台中城的邊緣,那時的我以為我們被什麼追趕著一路向前,小小的心臟扑通的跳著,在還纖薄的胸膛裡鼓一般的響。因此好長的一段時間裡,第一次的民選總統成為了一個巨大的有鴉青色翅膀的幻獸,我也一直記得,大人們高聲交談中,一直重複著一句:「回來後,就都不一樣了。」我的父母絕不是《女朋友‧男朋友》裡的林美寶與王心仁,但這句話雷擊似的在我第一次看這部電影時的耳旁共鳴隆隆,因此我可以忽略電影裡那些比我還彆腳的台語、中文台詞。我想藏在影片與追在我車後的必定是同一匹幻獸,只是它在不同時空中迴身關注。
而我回來後、看完電影後,卻沒發現有什麼變得不同,我想是因為我從不曾真正知曉「從前」是怎麼樣的從前。
推薦閱讀:從花樣年華到春光乍洩,香港後青春攝影
那一次的旅行充滿魔幻,除了臺灣島上追逐著我們的幻獸,香港島上亦有成群成隊的各式人群,集合成了舞台上歌隊似的華麗出場。絕對記不得的一個大型十字路口邊,我被父親抱著等其他人會合,在過街的人潮間看見了好多臺攝影機圍住一個黑色西裝的人,那時的我知道他就是劉青雲阿,長大後,父親說他不記得這段往事,但我知道不記得不代表它不是真的。在很小年紀看過的《香港也瘋狂》電影裡,我喜歡歷蘇、也喜歡上劉青雲,劉青雲一定是我第一個識得的香港明星,連名帶姓的那種。所以當我在香港街頭看見他,也直覺的認為劉青雲本來就是香港人,出現在香港再自然不過了,就好像他是我一個很熟的香港友人,本來就該在街邊遇見他,不管香港是座住著幾百萬人大城。這樣的認知,直直的留在我當時與之後的記憶裡,卻到現在才開始浮出魔幻般的邊框與色彩。大型街頭的歌隊、攝影機與穿著皮丁字褲的歷蘇、熱黏的大樓下女人街攤販裡成堆的無用商品,如此迷幻如此香港。多少年後我們眼中的香港,一直都還是如此,年幼的我從未錯看過什麼。

圖片|來源
現在看來魔幻浪漫的還有那次旅行我得到的一堆英女皇頭港幣,它們都還在我特地留著的牛皮小零錢袋裡,5元厚實的、不規則的邊角,是我當時拿過最重的一枚硬幣,沉而紮實,我以為那才是零錢應該有的手感。後來,我再去了許多次的香港,也曾有過幾次魔幻迷眩的片段,搭的士穿越過港隧道只為到西貢吃一餐海鮮,跳錶上的價錢一直翻出令人暈眩的新數字,還好付錢的不是自己。西貢海鮮街的招牌在夜裡霓光四射,像極了好萊塢電影《萬惡城市》全是灰黑世界中偶爾出現一些極濃、極鮮的鏡頭。這一抹顏色留在回憶裡大半是山水畫背景色之中,閃閃躲躲,那樣的夜晚後來幾乎不再出現了。隨著找給我的零錢不再冒出英女皇頭,隨著街邊的周生生、sasa 藥妝、優之良品這類的伴手禮店開滿整街、隨著時間變成該死的時間後,我們開始活在遺憾裡。遺憾的關鍵字如下:解嚴、劉青雲、歷蘇、女皇頭硬幣,以及莒光新城。
莒光新城是我童年未崩塌的、關於幸福這個字眼,最初的一筆註解。民國 86 年,1997 成為界線,有地方成為了一處國家,有地方承認自己失去了一個國家。祖父從中興新村撤出,我不再需要跟著父母在假日熬過長長塞車彎進中興新村陪他吃飯。他回來台中,與我吃遍童年的大吃與小吃,經常一起散步到莒光新城下的小米粥店,點一份抓餅,灑兩匙糖,那年的粥店裡人常有像祖父一樣的其他伯伯,祖父總會輕輕和他們點頭,各自坐在不同的桌子吃著相同的吃食。許多年後,我再進新城,那家店早已拉下鐵門,半點當年不斷從後廚傳來的麵粉香都沒有留下。界線那年之前的我,紮著兩根一左一右的高馬尾,在與肩齊高的桌台間看人群。
推薦閱讀:【如果你想】尋覓城市裡的秘密基地:致台北,我的生活不在他方
那時餡餅的湯汁燙著唇口、舀了糖的小米粥,如此直接而美好,但這些味道都淡了。唯一能慶幸的是,至少在過去中的味道無損無缺。時間跨越民國 86 年,這條界線後是長長的下坡,距離未變但時間加快了,再一晃眼,我自己開著車停在新城旁,卻只是走向它對面新建的購物商圈修剪頭髮。回頭乍看新城,一如當年的米黃色、陳舊著,記憶中它從不曾新穎過,但也許是因為我總習慣只是,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