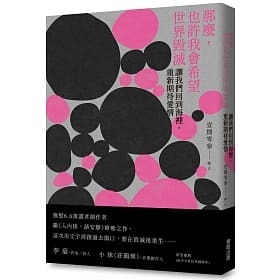分手後,一切如舊,只是身邊的你,不在了。親愛的,最難道別的是,那些與你經歷過的瑣碎日常。
一覺醒來,眼睛還是張開,末日沒來。
一樣喝了一杯等了徹夜的水,白色的帆布鞋,牙刷和馬克杯,晨光在同樣的仰角,刺穿窗簾伸了進來,被窩暖著,一人份的體溫。
早上七點左右,手機習慣的勿擾模式自動解除,開始接收訊號,看著昨晚是否被誰侵擾。
不用特別專心就能進行的簡單盥洗,鑰匙舊的掛飾還在,那些讀過不只一次的書還在,黑色檯燈還在,門上的日曆還在,日常裡的都還在,一一確定了。
只有妳不在了,分開的時間也太久,應該不會回來。

圖片|台灣東販 提供
預言需要時間證明,在很後來的現在,才應驗了妳說過的話。
如果哪天我們分開了,這些被遺忘保留的景物,可以說是遺跡吧,能證明曾經有什麼存在過一段時光,而後消失了,被後來再發現的人們議論或紀念。
記憶中妳信誓旦旦的樣子,說如果哪天妳不在這裡了,妳不在我身邊了,遺跡一定會讓我很傷心很懷念,指著房內的任意角落這樣說過。
我們第一次見面就互道晚安,我正要去一個飯局,而妳準備回家,只是遇見了,隨後兩人走著自己的步伐離開,相視微笑的說下次再見。
我們曾經就見過面,在學校裡,只是不曾說話。
那是十二月的忠孝東路,當時飄著冷冷的雨,折射著銀白的大樓燈光,像雪一樣,還有大大的聖誕樹下擺滿禮物。
那時的我們都不住在台北,幸運的話,有時會搭上同一班車回家。那時的我們才剛步入社會,總是說著要搬來台北住,如果真的搬來了,我們一起養一隻貓吧,取貓的名字叫明天,喚著就是一種期待。
我們喜歡同一種類型的音樂,喜歡同一個歌手,我們都喜歡咖啡廳,只是我們都一樣不懂咖啡,我們都喜歡看電影,也喜歡在看電影時吃爆米花,甜的。
這些是世界的一部分,只是剛好重疊著我們。
之後妳離開了,這些世界的一部分看上去都零零碎碎,它們沒因此消失或去了哪裡我找不到,它們都還留著,而且本來就不屬於我們,在沒有我們之後,它們看似未曾沾染過情愛,一點也未見陳舊昏黃,它們還是支撐也運行著這座城市。
晨光裡,大雨中,咖啡廳,爆米花,歌和歌手,會經過妳家的客運,都照舊運行著,我們不照舊,但我們卻是舊的。
稱不上思念,思念讓人感覺悠長而淒美,我想我只是時常想起妳這個人,也或許
是想起我們,在想起來的時候,會有一陣悶悶的痛呼一聲飛過,心想抓也抓不牢的,就是那樣一下子,症狀卻持續了很久。
不曉得這算不算一種不成熟,但也許我也沒想過要成熟,更多時候,如果還能幼稚一些,我會是慶幸的,雖然妳討厭那樣的我。
到底真正的成長,是絕口不提那些過往的悲傷,還是像我現在這樣,容許自己在該傷心的時候,片刻的沉默,隨自己掉進回憶裡,反正那像風,吹一陣就又走。
相比平淡的生活,有時想念是突兀而刻意的,突兀的出現,刻意的裝演。
那時是兩個原本以不同形式生長的靈魂,在某一隨機的狀態下交錯了,之後重疊而依著對方,重新生長,重新以另一種可以延續生活的模樣生長,生長出了原本不可能發生的軌跡和形狀。

圖片|Photo by Raychan on Unsplash
而我們後來經歷了分開、道別,時間的大雨把兩人越扯越遠,時空間在不斷證明,相遇的機率有多低,那在分開之後,更加明顯了。
原本重疊的部分,相互依偎著生長,在某個瞬間拉扯開來,隨即扯出了一些必然,必然的悲傷,必然的難熬,必然的成長,只是那些成長,是被逼著重新生長。
我們成為了歷史的一小角,有了自己的遺跡,我們望著流年,那不可逆。
不可逆的都忘不了,就像是多次被摳弄的傷痕,長出了癒合作用的痂,結痂最後成了疤,而那些疤,就是我每早醒來,眼睛每次睜開,能見到的世界,能見到那所有我們曾一起經歷過、輕撫過、任憑時光經過滑過的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