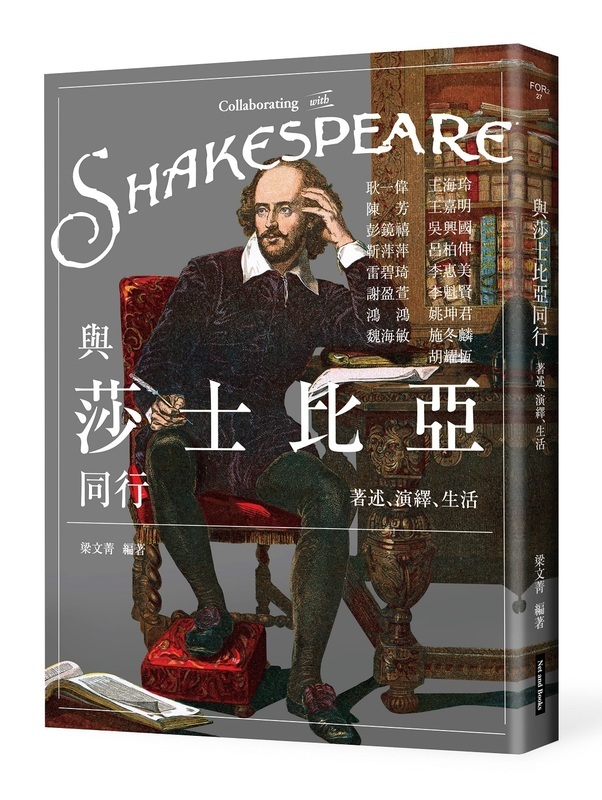莎翁逝世四百年後,飄洋過海化身萬古的靈魂,活在豫劇裡、京劇裡、台語戲劇裡,也在兒童夏令營裡⋯⋯與這裡的人悲喜交融、探論矛盾——他始終與我們同行。 劇場學者梁文菁,訪問了台灣當代十七位舉足輕重的莎劇專家學者以及藝術工作者,暢談莎士比亞迷人之處,並對他們的著述、演繹和人生產生何種影響與領悟;印證了莎士比亞與他的作品不屬於一個時代、一種文化,而是屬於全人類永恆的文化傳承。
國立台灣大學戲劇系副教授,專長表演、肢體、即興,尤以寫實表演為其教學重點。在美國曾多次演出莎劇,回到台灣後,參與屏風表演班、綠光劇團等諸多製作,表演廣受好評,並與台南人劇團合作《馬克白》,詮釋馬克白夫人。
姚坤君在台灣的莎劇演出雖然不多,但在台大戲劇系開設的莎劇表演課程,幫助學生在看似神秘的莎劇表演裡,找到可能的破解方法,亦參與彭鏡禧老師的《與獨白對話:莎士比亞戲劇獨白研究》一書,與蔡柏璋等年輕演員,共同錄製其中的獨白範例。
最近的著作《表演必修課:穿梭於角色與演員之間的探索》,綜合自身的演出經驗,以及上表演課遇到的種種景況,就文本、排練、演員自身狀況等面向,為對表演有興趣者,提出學習的路徑與方法。

◎ 您在美國的時候,演了幾個莎士比亞製作,您自己現在也教莎士比亞表演,請問莎士比亞演出的難度何在?
▲ 所有的演員—— 不管是以英文為母語的美國人,或者是來到這邊要講翻譯成中文的台灣人,無論是國內或國外—— 在莎士比亞的表演上,常常會被它的語言卡住。總有一種迷思,覺得莎士比亞的文字很偉大、很了不起等等,或語言文字拗口,然後自己沒辦法消化,最後淪為背誦跟擺擺樣子,看起來就讓人很不舒服;或者說,因為認為莎劇是至高無上經典中的經典,以至於在表演時,詩詞上的韻腳,會拘泥到變得非常死板。
就有點像我們在朗誦《唐詩三百首》,每一句都非常的中規中矩。事實上,莎士比亞的語言固然是非常優美,但任何觀眾聽了兩個多小時版鐵定是會睡死。莎士比亞的迷人之處不是只有語言、文字或聲韻,而是他故事的普遍性和普世性,也就是他探討人性之處,才是大家更關切的。
◎ 那麼您在上課的時候會怎麼教莎劇的演出?
▲ 其實我自己也覺得用中文詮釋莎士比亞台詞很弔詭,雖然它很有趣:因為經過翻譯,文字很可能已經喪失很多意義,而原來的韻腳,更是早就蕩然無存。縱然很多譯者,例如彭老師,他們非常認真地試圖想把它的韻腳再找回來,可是無法否認的,那已經不是原來的音樂了。
如果我們把莎士比亞的文字,想成是一首歌的話,那個曲子早就變調了,只有歌詞的意義上是類似的。你說我怎麼去教?我最大的重點是想辦法使我們的學生、演員可以把這些你聽不懂、難以消化的文字,消化成一般人聽得懂。怎麼做呢?在語句的處理上,你必須要劃分到你的結構要怎麼走,會讓人家比較聽得懂那個內容。
就拿我比較熟的、做過的製作這段舉例好了:
馬克白:我眼前看到的,是匕首嗎?刀柄向著我的手。來,讓我抓住你。
馬克白說,我眼前看到的「逗號」,是匕首嗎「問號」,第一行是這樣。第二行是,刀柄向著我的手「句號」,來「逗號」讓我抓住你「句號」。所以通常聽到的是照著標點符號念出來:「我眼前看到的(休息)是匕首嗎(休息)刀柄向著我的手(休息)來(休息)讓我抓住你(休息)。對不對?其實是聽不懂的,如果照著標點符號,你想想看這樣聽兩個小時會不會想死?一般正常的耳朵,聽得懂的是:「我眼前看到的那個是匕首嗎(休息)刀柄向著我的手(休息)來(休息)讓我抓住你(休息)。節奏上,雖然變化沒有很大,但聽覺上不會斷掉,並不能永遠乖乖地照念,那樣的斷句和意象無關。
其實文字是給眼睛看的,不是給耳朵聽的。視覺需要分字詞、分重點的幫忙。如果把它變成是聲音之後,人的聽覺又有另外一個邏輯了。這是很多人不會去注意到,更沒有發現過的事。就像我現在說的這一整句話,到底中間有幾個逗點,有幾個句點,或者哪幾個是驚嘆號?你是聽不出來的。
好,我現在再把剛剛說的那句話再講一遍,變成是文字的邏輯:「就像我現在說的這一整句話(休息)到底中間有幾個逗點(休息)有幾個句點(休息)或者哪幾個是驚嘆號(休息)你是聽不出來的(休息)」。就會變成是這樣,如果你照這樣背,死定。
文字不是給耳朵聽的
◎ 我想您最後示範的這個,很像廣播,或者模擬廣播會有的聲韻,就是太照著標準走,沒有去消化這個東西。
▲ 對。所以我教課的時候,我的重點就是放在怎麼把那一整段的意象先整理清楚,變成是一種意圖。當你這個角色的意圖演繹清楚,那個段落就不可能會是原來的標點符號,或者是分行所做出來的斷句了,這樣就比較有趣了。
◎ 那這樣子學生會有抗拒性嗎?
▲ 沒有。原因是因為我不是一句一句教他們講,我是讓他們用遊戲的方式,玩出「啊,原來我的斷句在這裡」。那個細節內容,太多遊戲了,很難一時說清楚。
◎ 所以要上姚老師的課才知道。
▲ 可能,而我一年半只收八個人。
◎ 真的嗎?
▲ 對,而且要甄選,我好壞喔。不然這麼多人會講莎士比亞的獨白,到底是要幹嘛?(笑)

◎ 作為一個技巧啊。莎士比亞其實是台灣演出頻率最高的作家。我是做了這個展覽才恍然大悟。那麼,我們來談談您跟台南人劇團合作的作品?
▲ 我和台南人合作的只有馬克白夫人,我應該講《女巫奏鳴曲》,不對!那個版本叫作《馬克白》,不插電系列。
◎ 嗯,是兩個不同的作品。
▲ 之前我演過《馬克白》,是在美國的時候。在美國當然是用英文,回到台灣本來想,當然是用中文吧,但,不是,是用台語演出!台詞要重背不打緊,古台語的語句又深奧,雖然我是台灣人,我還是得花很多時間去背。我們沒辦法看著有意義的文字背。因為周定邦老師把它譯寫成羅馬拼音,我們一邊看著羅馬拼音,一邊聽老師的錄音,一句一句牙牙學語地背。頗像古時候的演員,或是歌仔戲班也是這樣教唱的。對我來講真的覺得好難啊,比背英文原文還難,而做功課也一定得要有錄音器材在身邊,否則很容易講錯那些語音,你沒有辦法自己來。
◎ 所以那並不是照著劇本直接轉換成台語,而是有人先幫你們轉換,你們再去做功課?
▲ 對,然後因為那個作品是由五個演員把整齣戲演完,所以文本是被拆解的。我要演女巫,同時又演馬克白夫人。這樣有一個雙重意義,也就是女巫其實存在於自己家裡。(笑)是滿好玩、挺有趣的,對演員來講,演員當然一定是喜歡挑戰、玩,有不一樣的觸角。我自己在詮釋這個角色時,就很不想要和很多製作一樣,把這個太太詮釋成權力慾望很強大,慾望全部寫在臉上的那種壞女人。因為大家詮釋馬克白夫人的時候,很多製作都會把她做得刻板,讓她看起來就是很……
◎ 恨鐵不成鋼?
▲ 對。當然她外在的服裝、造型也會讓她看起來很強悍、兇悍。不過,我有故意收掉一點,詮釋成如果能夠當皇后的話會很開心,就是有點小女人的天真,因為我希望她的形象可以更平易近人些。我希望我的觀眾會覺得,這樣子的人,就在我們周圍。你並不知道她原來是這樣的、將來會做出這麼恐怖的決定。
也就是說,一個很普通的人、一個很普通的太太,當她有了過度的慾望之後,就一步錯、步步錯;有了一點甜頭,就還想要再多一點,慢慢釀成可怕的後果。而這並不是說長相、身材,或者是有壞女人面相的人才可能變成這樣,普通人如你我都很可能誤入歧部C所以我在詮釋她的時候,有故意做這樣的選擇。
◎ 那您之前演過的不同的莎士比亞角色呢?
▲ 我想想看我在台灣還有演其他的莎士比亞嗎?
◎ 好像⋯⋯
▲ 沒有欸。其實他們應該要找我……
◎ 這是一個跟全台灣導演的告白嗎?「趕快來找我演莎士比亞」嗎?
▲ 可以可以,趕快來找我演莎士比亞,我可以的,我超可以的。(笑)
反轉「李爾」
◎ 我們剛剛閒聊時您提到《辛柏林》,那是在國外演的。但是這個劇本本身就是一個比較少演的劇本。
▲ 對,但《辛柏林》沒什麼好提的,我演一個小小的宮女。每個人都當過小演員,那個沒什麼。演《辛柏林》那個時候,是我進了研究所之後,我還是個研究所一年級的菜鳥就被相中,參與他們當地的職業劇團,心裡覺得已經很偷笑了,而且還是跟自己的教授們同台。教授們,一個演辛柏林,一個就演他的太太,國王皇后,那兩個老師實在太厲害了。其實第一次讀本的時候,我被他們兩人的能量給嚇傻了。暗自想著,我以後一定可以跟你們一樣。雖然是嚇傻,但中間休息時間,我看到我們老師在廁所旁邊洗手,我跟個迷妹一樣地跟她說:老師你好厲害,我好喜歡皇后剛剛的讀劇這樣。
後來我在美國演過比較大的角色,一個是馬克白夫人,還有《終成眷屬》的海蓮娜(Helena),以及,挺意外的是,他們把《李爾王》直接改成《李爾》,因為是要讓我去演那個李爾,那次的收穫當然很大,而且我也沒有想到導演會做這樣子的決定。因為那一次製作,其實有年紀比我還大的男演員來甄選,男士們大概想說李爾王這個角色應該是他們幾個競爭吧,結果沒有想到是找一個小隻的東方女生來演李爾,我覺得那些人大概都傻眼,後來他們都變成我的公爵。(笑)
◎ 那本來您是去甄選小女兒考迪利亞(Cordelia)的嗎?
▲ 我心裡想就隨便試試看,我是黃種人,覺得這很難,因為三個女兒怎樣應該都是白人吧。當然我也沒有想太多,結果不但甄選上,還把我變成李爾,結果整個劇搬到日本中世紀,全部人頭髮染黑。(大笑)這個決定我真的是受寵若驚,導演還很沾沾自喜的說:「你看吧,這樣全部都通了。」不是應該三個女兒嗎?他怎麼選擇?結果老大、老二是女兒,老么是兒子。導演說,這就是你們東方人會做的事,就是疼兒子,但是兒子不聽話。你覺得兒子跟你唱反調,但你最寵兒子。
◎ 我們剛剛聊到李爾王這個角色很難演,因為他的心理歷程很大,因此對演員是很大的挑戰。身為一個演員,莎士比亞的演出,對您有什麼收穫?
▲ 我告訴你一個非常直接的:如果你能把莎士比亞的語言文字,能夠演得好,讓人家聽得懂,哇,你大概沒有什麼其他的台詞是人家會聽不懂。因為莎劇句子的結構已經太難處理了,其他的獨白,應該都不會有太困難的挑戰。我想,這個是對演員最大的收穫。當然,也不是第一個獨白就能夠處理得很好,所以剛開始,觀眾還是得忍受你那些聽不懂的文字。
而觀眾們如果聽不懂演員在講什麼,千萬不要自責,並且千萬不要覺得是因為自己的程度不好,所以聽不懂、看不懂。
不應該是這樣子的,因為演員還有導演本來就有責任,將這些艱難的語言結構,讓觀眾能夠岩掑F解,而不是說:「啊,我聽不懂耶,我聽到了一段好像很有學問的一段話,可是我都聽不懂,可能是我程度太差,所以我們鼓掌吧。」為了表示自己跟得上莎劇的程度,或是讚許台上的背書功力而鼓掌?不必!很有可能是因為他們演得太爛,或者太自以為是,所以你聽不懂、看不懂。千萬不要有莎士比亞迷思。

◎ 那您演過最喜歡的莎士比亞的角色?或是您想要挑戰的莎士比亞的角色?因為您竟然連李爾王都演過了,那是很多人的高峰角色。
▲ 其實,說實在的,莎士比亞很多好的角色都是落在男生身上,幾個女生的經典角色,其中一個重要的是馬克白夫人,讓我演到非常的幸運。然後,我不可能再演茱麗葉了,(大笑)或者是我九十歲的時候故意去挑戰茱麗葉。
◎ 我前一陣子在寫一篇關於茱蒂·丹契的文章,回顧她的作品,她演了兩次《仲夏夜之夢》,都是演仙后,一次是很年輕時,一次是二○一○年。
▲ 欸,我演過《仲夏夜》的仙后,我怎麼會忘記講這個。《仲夏夜》的仙后我也覺得很幸運,也是在美國演的,也一樣是在Summer Festival。那個導演還是對我很好,讓我的扮相就是一個東方人,反正我是仙后,所以不一定要是白人的世界。你本來想到這個仙后要說什麼?
◎ 我本來是要說她已經七十幾歲了,所以是一個七十幾歲的仙后,但是七十幾歲的茱麗葉是不一樣的事情。
▲ 我演那個仙后,又同時演西波利塔(Hippolyta),那個王后也剛新婚,跟那些新人一樣。
◎ 聽起來滿好玩的啊。
▲ 很好玩啊,讓我可以有很多亂搞的空間。
◎ 您怎麼跟驢頭談戀愛?
▲ 演驢頭的那個人很可愛,真的很可愛。他是一個紅髮白人,長相很呆。可是他非常靈巧,其實是伶牙俐齒的人,就跟驢頭的角色真的非常符合。我覺得要愛上他並不難,因為他就是很靈活很體貼的一個演員。其實說到表演,演員與演員之間的默契是佔很大的部分,所以很幸運可以遇到這樣的驢頭。是真的很可愛,然後我就愛他就好了。
◎ 那個驢的頭是怎麼表現?
▲ 道具是一個寫實的驢頭,並不是用意象表現。有的製作會只是戴一個髮箍或耳朵就表示是變成驢子了,我們的製作選擇套上一個有毛的驢頭。希望讓觀眾覺得,哦,你怎麼會愛上這個東西。對了,我也演過《亨利四世》的波西夫人(Lady Percy)。《亨利四世》裡面基本上沒有女人,波西夫人可能已經是最大的角色了,那個是學校製作,一樣是要甄選的,沒有想到導演找一個東方臉孔、英文又講得怪怪的人演波西夫人。
另外一個女生角色是毛提摩夫人(Lady Mortimer),台詞不多,而且這個角色本來就是外國人,我以為我會是那個角色,結果沒想到我是波西夫人,所以很高興。結果我們在看榜單(演員名單)的時候,我看了我就超爽,但另外一個來競爭的女演員,漂漂亮亮的金髮美女大哭,看到她在我旁邊哭的時候,我覺得很尷尬,然後就趕快開車回家。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況且我又是一個外國學生。其實我覺得我的美國同學都還滿好的,他們安慰我說,導演選你一定是相中你什麼樣的優點。然後我就開著我的小車跑走,途中我越開越興奮,然後我就開始唱起《中國一定強》,不知道哪來的 idea。(大笑)
◎ 這是您學生時期、還滿早的莎士比亞製作?
▲ 應該是我第一個或第二個有台詞、比較稱頭的角色。角色是個花瓶,但是有一個精彩的獨白。當初我真的沒有想到我可以講那個獨白。因為我還是一個大學部的外國學生。所以很妙,我到現在還記得前幾句。
把劇本當床頭故事
◎ 您會給想成為莎士比亞演員的人什麼樣的建議?
▲ 除了上課之外,會有很多學生來跟我求救,要我看他們莎士比亞的表演片段,都是因為他們要去國外念書,需要準備古典和當代兩個不一樣的獨白,古典的話我們都會建議找莎士比亞,因為希臘悲劇可能不是那麼討好,也都會很明白的希望你避開那些非常有名的片段,原因是,有太多人做過了。一來,如果大家都選那些有名、熟悉的,那些老師可能會聽八十遍的「生存,還是毀滅……」,他們會瘋掉。
二來,那些經典片段之所以成為經典,可能不是只有文字,而是以前曾經有很經典的演出,要比他好,很難;你要比他好,老師才會驚喜。如果只是因為自己有興趣,想要研究,你要看什麼樣子的角色當作入門呢?那當然,你剛開始會對歷史劇比較沒有興趣,反正,大家都聽過的《羅密歐與茱麗葉》、《仲夏夜之夢》,以常被搬演的當作入門。
其實,我也要說實話,我自己在讀劇本的時候,也常常看一次劇本,中間要睡三四遍,這真的是很難避免的,因為文字確實是非常的不平常,雖然都已經是中文了,但你要花很多腦筋才能看得懂他在說什麼。所以想入門的朋友,不要害怕、不要嚇到,因為其實我也還是會睡好幾遍,(笑)反正就把它當床頭故事,今天看幾景,明天再看幾景,你可能看一次會玩味不出那個趣味,反正多看幾次。
很有趣的是,不管是我自己在演、學習莎士比亞的,還是剛開始要開莎士比亞的獨白這門課的時候,我自己也會一直反問我自己,意義在哪裡?尤其是譯成中文後,除了故事情節內容還是莎士比亞以外,歌詞全部不一樣、音樂全部不一樣,台詞已經沒有聲韻了,只是比較文謅謅、拗口的字句結構而已,要說美感有點困難。
雖然有一些莎士比亞工作者已經非常努力把它寫出韻腳,但是確實不是已經原來的聲音樣貌了。雖然我也曾自我懷疑,但是既然台灣開始有一點這樣的流行,與其大家一起亂弄,倒不如我將自己的經驗與所學跟同學討論、分享。如何把這些難以理解的文字,透過演員的詮釋,能夠讓觀眾看得懂、聽得懂,這對我來說是最大的意義。

◎ 我們上次訪問呂柏伸,他說,他在您變成同事之後,他覺得他導莎劇有不同的體悟 ⋯⋯
▲ 那他是有什麼樣的體悟?
◎ 他覺得這是姚坤君式的寫實主義表演。所以他應該是說怎麼樣用一個寫實主義的表演來演莎劇吧。
▲ 他所謂「姚坤君式的寫實主義的莎士比亞」,可能就是我希望讓大家都聽得懂、看得懂的莎士比亞,不是一個高高在上的東西。莎劇當時也是個大眾娛樂,像我們平常聽到的語言一樣容易接受,如同我們的行為舉止一般平常,或許他所說的寫實就是這個意思吧。
◎ 我們訪問盈萱時,也提到大眾娛樂,她覺得這是很重要的,要讓大家可以享受這個表演。
▲ 莎士比亞很多劇本,真的很多社會新聞跟《娘家》或《世間情》都很像的,完全就很八點檔。那些販夫走卒都可以在那邊看,你期望他們有多高的學養才能聽得懂嗎?不可能啊,所以很顯然是一種很普及的娛樂。
◎ 所以我們不應該把莎士比亞當作供起來的東西,應該跟生活有關。
▲ 我常常在講 Play a Play 為什麼這兩個字都是 Play,「演一齣戲」就是「玩一齣戲」,也就是「玩一玩」啊,那 See a Play 就是「看人家玩」咯。但,不知道是華人,還是東方世界都如此,還是只有台灣,就會把這些已經被稱為藝術的東西供在上面。我很羨慕很多國外的小孩,在學鋼琴的過程,跟我的經驗實在差太遠。我痛恨彈鋼琴。我小時候被家裡規定要學鋼琴,我學得很差,因為沒有人發現我是看不懂譜的,我都是用耳朵聽,硬把它彈出來,老師聽完一次交差我就要下課,我真的很害怕。老師也很妙都沒有發現我讀譜太慢,慢到有點像閱讀障礙那種慢。
小時候學琴壓力很大,可是我在國外念書的時候,看到同學把彈鋼琴當成是在玩玩具一樣,要彈什麼就亂彈什麼,在這樣的狀況下慢慢學會的,而不是那個譜彈什麼我就跟著彈。當然那個也很重要,就像我要說的,學表演不是每一次表演都要跟著台詞走的才叫表演,不是。現在我正在跟你講話,我在表演,你也在表演,表演就在生活裡。所以我很羨慕人家學樂器就是真的在玩樂器,為了好玩就學會了。所以學莎士比亞應該 Play,我們應該 Play a Play,不要去供起來拜。
延伸閱讀:你不是書讀得少,你是經典讀得不夠
◎ 我在英國的時候,發現他們很重視小朋友的莎士比亞。所以有各式各樣小朋友版的莎士比亞,像是繪本,還有浮空投影版的立體書,所以就像您說的,潛移默化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可是在台灣因為不是我們的文化,被我們當作經典。那您覺得我們在課堂上,應該要怎麼認識莎士比亞?
▲ 我覺得很多角度可以做,當然他是一個經典,所以也需要一個很認真的角度去學習他,還有一個方面,就是能不能用玩樂把它玩出來呢?像我剛剛說的鋼琴,如果你真的對音樂非常有興趣,樂理你需要去學。就像我們需要去理解莎士比亞在寫這些台詞時,它的規則是什麼?這是什麼道理?但當我們在彈琴抒發的時候,那個道理為什麼要存在呢?那在我們心裡啊,那就是一個令人振奮、愉悅、悲傷的曲調,它就是一個可以震撼人心的作品,它就是一個玩具。
◎ 所以我們要把莎士比亞當成玩具,拿來玩弄一下。
▲ 把它當閒書、課外讀物。這是其中一個角度。
訪談時間/二〇一五年七月二日
校閱整理/林立雄
圖片來源:電影《李爾王》劇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