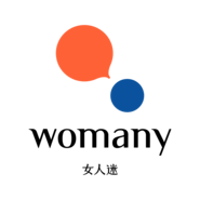執導《美國女孩》入圍金馬獎,阮鳳儀獲得第 58 屆金馬獎最佳新導演獎,她在台上哽咽,「這三年,我們沒有一天不想《美國女孩》,沒有一天不是奉獻給電影。」將生命中難熬的日子化作電影,回想反移民的經歷,她以泰戈爾詩集中的一句話回應:「最遠的路,就是最近的路」,曾讓她陣痛的日子,最終也使她貼近自己。
《美國女孩》以 2003 年的台灣為時空背景,講述女主角芳儀因母親罹癌,無預警地必須拔起從小在美國生長的根,回到文化、環境、身份認同都帶給她巨大衝擊的台灣,無法適應的憤怒與無助,生出火苗,在芳儀與母親間悶燒。
彼時台灣不是芳儀的家,她心中有塊象徵自由的奧勒岡原野,馳騁白馬於曠野奔跑,那瞬間世界彷彿靜止,除了當下,其他不再重要。《美國女孩》中以白馬作為芳儀對家鄉的念想,對自由的渴望,當芳儀最終抵達馬場,找到那匹白馬,套不上的韁繩與她眼中的淚水揭示——那是再也回不去的故鄉。
《美國女孩》故事原型來自導演阮鳳儀的生命經歷,她直言,拍下這個故事某種程度像在記憶中改寫過去,目的是為了前進。

你知道媽媽很愛你嗎?
思索第一部長片主題時,阮鳳儀嘗試過很多題材,但總是寫著、放著又覺得沒意思,直到她開始寫自己的家庭故事,發現可以一直寫下去。
「和解是很多人用的字,但我會覺得,真正的和解是與自己和解。」
以為已經放下的過去,在阮鳳儀結束美國求學,搬回新店重新與媽媽同住時,看似死透的灰燼又燃起火苗,「一起吵起來,就覺得,哇!根本還沒有和解吧!心裡的怒火湧上來,覺得我還沒有真正放下。頭腦說要放下,但我們的心能不能真的走到那裡?有沒有欺騙自己?」
如何放下了?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麼?母親在想什麼?我的憤怒從何而來?帶著疑問,阮鳳儀踏上創作《美國女孩》的路,「作為編劇去回顧當時,為了把每個角色都寫得立體,需要很多的換位思考,不能為任何角色找藉口。如果我是寫自傳體的小說,可能就沒有人挑戰我,放在電影裡,演員要去做這件事,他就會打破砂鍋問到底,他要得到他要的答案。那我也必須問自己:為什麼這樣寫?」

於是阮鳳儀開始與父母聊起那段移民回台的故事,訪談父母的家人、朋友,甚至拉著母親一起心理諮商。真空在 2003 年的情緒與困惑,因對話開始流動,「你如果了解一個人的原生家庭,就會比較能接受他為什麼會這樣子。我媽媽的血親都不在台灣,我外公外婆在我出生前就過世,我對母親的原生家庭很陌生,她像個真空的角色,就覺得她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有這些習慣?這很不合理。直到遇到媽媽的姊姊,他們做了一樣的事,你就會覺得,原來如此!」
「我學到很重要的事,保持一種中性,就是不要去評斷。有些觀眾會說,這一家人感覺好尖銳,但我在寫這些東西不是帶著尖銳去寫,我希望保持一種中性,就是,他曾經對我說過這句話,我也曾做過這件事,我不會去想,這是好還是壞。如果在劇本階段就評價這個角色的話,我就剝奪了觀眾去感受角色的機會。」
時間給了阮鳳儀一個遠觀的視角,讓她能以創作者、第三者的角度去思索角色說這句話、做這件事的背後動機,試圖理解角色的過程,也讓她更貼近彼時的自己與家人。
真正的和解是與自己和解。
回望而得的心疼與同理,阮鳳儀藉角色說出。劇中一幕,妹妹芳安對日日與母親爭吵的姊姊芳儀說:「你知道媽媽很愛你嗎?」對阮鳳儀而言,芳安這個角色投射了芳儀經歷挫折、憤怒前,最原本的樣子——那些柔軟、溫暖的部分。
說到底,針鋒相對的爭吵背後,底蘊還是對家人無盡綿長的愛。
最遠的路,就是最近的路
經歷過移民與反移民,阮鳳儀的生命歷程中有需多必須重新扎根、回到原點的狀態,現在去看那樣的人生處境,她以泰戈爾詩集中的一句話回應:「最遠的路,就是最近的路」。
「從頭開始,會帶來很多挫敗,當習慣或是接受人生就是會面臨許多要重新開始的情境時,你就不會對重新開始那麼害怕。或是不會對失敗感到那麼害怕,因為大不了就這樣,沒有去試,反而更惋惜。因歸零感到挫敗時,長遠來看,到頭來會有一個原因,我很相信緣分。」
如同拍下《美國女孩》,那些看似繞了遠路、感到陣痛的人生過程,其實都是讓自己更貼近生命、更靠近自己中心的唯一近路。

她笑說,創作就是很弔詭的一件事,「很多創作者被驅使創作很多原因是,你有很巨大的痛苦,你希望把它抒發出來,這東西與自我表達有很大關係。我自己感覺到,如果我要邁向成熟,我需要『無我』,越無我,我可以看事情看得更透徹。可以更專注在這場戲的精神,而不是他的形式。」
片中有一幕,飾演爸爸的莊凱勛獨自一人在樓梯間痛哭,讓觀眾看見父親的眼淚裡有對家人的不捨與承擔。阮鳳儀也在成長與創作的過程,脫離孩童時期的「我」,以觀者的角度去理解父親,明白作為一個男人,父親說得不多,但總以行動表達愛的內斂。
「在我們的文化,說愛你很難,爸媽總是做得太多說得太少,尤其爸爸。我覺得長大成熟就是要去看到他做了什麼。因為小時後會很在意父母說了什麼,其實他的愛在很多行動裡。每個人接收愛的方式是不同的,我們常常表現愛的行為是不對等的,就會兩條線這樣(手在空中比畫),形成一個平行宇宙。需要理解才能慢慢交叉。」
《美國女孩》中,除了講述角色對身份認同的迷惘外,死亡與失去帶來的恐懼也貫穿全片。曾經歷意義上的死亡與失去,也讓阮鳳儀對生命的起伏看得淡然,「我覺得沒有永遠的成功,也沒有永遠的失敗,一切就是過程。我也會變得蠻活在當下,我們有的只有現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不能等到到時候再來說,因為可能沒有那個『到時候』,這是死亡與疾病,很早帶給我的禮物吧!以一個不同的形式,讓我更珍惜擁有的時間。」

同場加映:金馬 7 項提名!專訪《美國女孩》導演阮鳳儀:拍攝母女題材,難在要對自己很誠實
因為它還是少數,所以我站在這裡
《美國女孩》拍下 90 後女孩與母親的女性生命故事,早期阮鳳儀也曾於專訪中提及:「我進入這行最大的動力是想講述更多女性故事、華人故事,華人有很多種身份,而不是只是移民。」
紀錄下女性故事之所以重要,以阮鳳儀的話來說,是因為女性發生的精彩故事,與變成作品的比例太不成正比,所以她寫、她拍,「如果有很多人拍了,它變成主流,我覺得很棒,那我就會去做別的事情。不是有個名言嗎?村上春樹說過:『在高大堅硬的牆和雞蛋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那方。』因為它還是少數,所以我選擇站在這裡,也因為意識到生命本身的力量來自於這種柔弱吧。生命都始於很脆弱的開始,那是很珍貴的。」
電影作為全球的文化媒介,儼然成為大眾生活的一部分,也讓阮鳳儀意識到,讓下一代在電影中看見女性故事的力量,「你會覺得,好像被放進電影的故事很重要,這件事重要到可以被寫成書、拍成電影欸!你一直教育下一代,平等平權,他用看到會最直接的,要先看到才能做到。我覺得電影就是能讓你看到,那是最直接的力量。」
阮鳳儀也直言,在這個時代,很多東西淪為口號,口號隨時都可以喊,但到底做了、看到了什麼於她而言是更重要的事情,「做自己渴望改變的事情,成為改變的一部分。」
她思索了一會兒,提出了耐人尋味的觀點,「中文系老師以前告訴我們,他說,一個時代回去看另個時代的關鍵字,學者在分析就會覺得那件事特別重要,因為它(關鍵字)重複出現。可是老師就跟我們說,其實常常這個關鍵字是沒有的東西。」
「因為我們要的是沒有的東西。因為如果有了,你不會一直講。所以我覺得也可以思考說,那我們這麼積極說要平權,那實際上?平權是否可以有更多更細緻的內容?」
在慢慢靠近平等、平權的當代,阮鳳儀選擇站在少數的一方,拍下女性的生命故事,以她的方式,成為改變的一部分。

喪失之後,我們還是可以愛生命
訪問最後,阮鳳儀也分享了近期影響她很深的一部電影,它是來自丹麥導演湯瑪斯・凡提柏格 Thomas Vinterberg 的作品《醉好的時光》,故事講述四位過著苦悶生活的丹麥中年大叔,為了要驗證「人的體內缺乏 0.05% 的酒精」的說法,開始了一場酒精計畫。
「看了就覺得,這就是生命。這就是一個導演對生命的愛。看到形式與內容這麼疊合的東西覺得很棒,可以看到它的精神。齁,我真的是看到,我平常不會想喝酒,但邊看就覺得,冰箱那瓶酒呢?邊看邊喝醉,覺得好開心!」

阮鳳儀補充,她認為這部片讓她看見一個創作者的極致,「導演的女兒在開拍前因意外過世,然後大家就勸他停拍,裡面有個角色原本是他女兒要演,但他就覺得,女兒應該會希望他把電影完成。我覺得那就是一個創作者的意志,就算我們以為拍電影很難,其實做什麼都很難,但他把喪親的痛放在作品裡,在這個喪失之後,他還是可以愛生命。而且他不是口號浮誇的說:愛生命喔!而是真實帶你走了一趟。」
這次因《美國女孩》,阮鳳儀獲得第 58 屆金馬獎最佳新導演獎,她在台上哽咽地說,「謝謝所有因這部電影帶來的緣分。那些很難熬的日子,因為被拍成了電影,所以有了出口⋯⋯這三年,我們沒有一天不想《美國女孩》,沒有一天不是奉獻給電影。」將生命中最難熬的日子,化作電影,在她身上你或也能看見屬於創作者的柔情骨幹,就算經歷恐懼失去親人的痛、對自我認同的無措,她以自己的方式演繹——喪失之後,我們仍可以找到出口前進,仍然能夠愛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