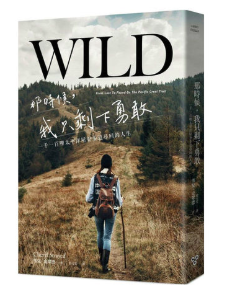女人迷【畢業季選書】,你的人生不要再聽別人說!挑選不同職業經歷、生活方式、人生選擇,開拓你對未來的想像與可能性,勇敢替自己做出選擇。《那時候,我只剩下勇敢》一書,描寫一趟千里荒野跋涉,在太平洋屋脊步道上,這才明白,真正巨大的勇敢是——正對著恐懼,瞪視它。
我知道,現在已然太遲了。只能怪罪我那個不在人世、孤立、過度樂觀、不曾替我念大學做準備、偶爾拋棄小孩、吸大麻、揮舞木湯匙、歡迎我們直呼她的名字的母親。她不及格。她是那麼徹底讓我失望。
去她的。我心想,心中升起了一股狂怒,停下了腳步。
然後,我放聲哭嚎。一滴眼淚也流不出來,我只發出一陣陣撕心裂肺的嘶吼,用盡全身的力氣,讓我甚至連站都站不穩。我彎下腰痛哭失聲,雙手環抱著膝蓋,背包沉重地壓在我的背上,雪杖「噹」的一聲落在我身後的泥土地上。我就這樣悲泣著我那該死的愚蠢人生。
它完全錯了。它殘酷無情地將媽從我身邊奪走。我甚至無法好好恨她。沒辦法擁有正常的人生經歷:從嬰孩長成青少年、開始疏遠她、跟朋友一起說她的壞話、為了那些我認為做錯了的事情質問她。隨著年歲漸長,我開始了解到她已盡了最大的努力,發現她已經做得很不錯了,然後,終於再度張開雙手親近她。她的死毀了這一切。毀了我。在我最年少無知、滿懷傲慢的時刻,它將我的成長之路一刀截斷,逼得我必須立即跳到大人階段,原諒她作為母親所犯下的所有過失,同時又迫使我永遠都像個孩子一樣長不大。那個太不成熟的時機,既是我人生的終結,也是我人生的起點。她是我的母親,但我已沒有母親。我獨自一個人被她困在原地,然而困住我的她甚至不在身邊。她將永遠是那空蕩蕩的碗,沒有人能填補。我得自己一遍、一遍、又一遍地填滿它。
去她的。我一邊低吟著,一邊繼續向前走了幾英里,步伐因憤怒而加快。但過了不久,我就慢下腳步,然後在一塊大岩石上坐了下來。一叢低矮的花朵生長在我腳邊,它們淺淡粉紅色的花瓣圍繞在石頭的邊緣。番紅花。我心想。這個名字立刻浮現在腦海中,因為媽曾經告訴過我。在我鋪灑她的骨灰的泥土上,就長滿了這種花。我伸出手,輕輕碰了碰其中一朵花的花瓣,感覺我的憤怒逐漸從我體內流洩而出。
這一次,當我又站起來往前走時,我不再吝於承認:無論如何,我媽都是個非常、非常、非常棒的母親。從小到大,我一直都很清楚這一點。她快死的時候我知道,現在我還是知道。我有一些朋友的母親─不論多麼長壽─永遠都不能夠給他們像媽給我的那樣毫無保留的愛。媽把她對我們的這種愛視為她一生最大的成就。當她終於知道死亡已是不可避免的結果,而且還會來得很快的時候,她付出在我們身上的愛,成為她唯一能夠寄予的指望,愛勉強讓她承受即將拋下我、凱倫、雷夫的事實。
推薦閱讀:為你選書|那時候我只剩下勇敢:當罹癌母親在我耳邊輕聲吟唱

圖片|來源
「我把我的一切都給了你們。」在她最後的那些日子裡,她一遍又一遍地堅持著。
「對。」我同意。她真的有,這是無可辯駁的事實。她真的有。她真的有。她真的有。她總是用最快的速度、帶著排山倒海般強大的母性朝我們奔過來。她從不吝惜給我們任何東西,連一絲半點的愛也沒有少給過。
「無論如何,我永遠會在你們身邊。」她說。
「嗯。」我回答,輕輕撫摸著她柔軟的手臂。
當她的病逐漸惡化,我們也開始明白她真的已不久於人世;當我們已來到了通往地獄前的最後一段路;當我們已經放棄希望喝掉那一大堆養生小麥草汁可能會救她一命的時候,我問她想要怎麼處理她的遺體。火葬,還是土葬?但她只是盯著我看,好像我是用德文在跟她說話一樣。
「我想要把所有能捐贈的都捐出去。」過了一會兒以後,她說:「我的意思是我身上的器官。讓他們拿走所有他們用得著的部分。」
「好。」我說。這是全世界最怪異的感覺,考慮思索著這件事、知道自己並不是在為遙遙無期的看不見的未來作規畫,並且想像媽身上的一部分,將會在其他人的體內活著。「可是然後呢?」我堅持繼續追問,因痛苦而喘著氣。我一定要知道。這個責任會落到我的頭上。「妳想要把剩下的⋯⋯剩下的身體怎麼辦?妳想要火葬還是土葬?」
「我不在乎。」她說。
「妳當然在乎!」我回答。
「我真的不介意。妳覺得怎麼做最好,就怎麼做吧。選最便宜的那種好了。」
「不要。」我堅持:「妳非得告訴我不可。我想知道妳想要怎麼處理。」我可能會是那個必須作出決定的人,這個念頭讓我充滿恐慌。
「噢,雪兒。」她說,被我纏得筋疲力盡。我們目光交會,像是在悲傷之中達成了和解。我總是受不了她的過度樂天,但同時她也難以忍受我執拗的頑固個性。「燒掉我。」她終於開口:「把我化成灰。」
我們照辦了。但她的骨灰跟我想像中的不太一樣。它不像木頭燃燒的灰燼那樣,如沙般絲滑微細;倒更像是白色的石頭混雜在灰色沙礫裡。其中甚至有一些碎塊,體積大到讓我一看就能辨認出:那曾經是骨頭。殯儀館的工作人員交給我的那個箱子上,寫的收件人是我媽──很奇怪吧。我把它帶回家,放在收藏展示架下方的一個櫥櫃裡,我媽把她最好的東西都放在裡頭。那時候是六月,我們為她訂做的墓碑也在同一週送達。我將骨灰留在屋子裡,和墓碑一起,一直放到八月十八日。這段時間裡,她的墓碑就靜靜地待在客廳的一角;這幅景象或許讓來訪的客人覺得不自在,卻給我莫大的安慰。那是塊深灰色的石頭,刻著白色的字。上面寫著她的名字、生卒年月日,還有她病重臨終前不斷重複對我們說的一句話:「我永遠會在你們身邊。」
她希望我們記住這一點,而我牢記在心。我總覺得她真的陪在我身邊──至少,從象徵意義來看是這樣,在某種程度甚至是實質上。當我們終於立好了墓碑,將她的骨灰灑在泥土上時,我並沒有把所有的骨灰都放進去。我留下幾塊在我的掌心。良久,我站在原地,無法做好心理準備讓自己放手,任它們落入塵土。我沒有放手。我永遠不放手。
我將她那幾粒燒毀的骨頭放入口中,吞了下去。
到了媽五十歲生日的那天晚上,我又重新愛她了,儘管我仍舊無法忍受茱蒂.柯林斯的歌曲在我腦中播放。天氣還是很冷,但已不如前一天夜裡那麼嚴寒刺骨了。我戴著手套,包得緊緊地坐在帳棚裡,從頭開始翻閱我最新的一本書:《一九九一年美國最佳散文集》(The Best American Essays 1991)。我通常會在早上燒掉前夜看過的部分,但這一次,讀完後爬出帳棚,我在讀過的書頁上點火,看著它們起火燃燒,大聲說出媽媽的名字,好像這是一場為她舉行的儀式。她的名字是芭芭拉,但大家通常稱呼她芭比,所以,我選擇使用「芭比」這個名字。
對我而言,從口中說出「芭比」而非「媽」感覺有如一種啟示,第一次讓我真正明白她不僅僅是我的母親,同時扮演其他的角色。而在她過世後,我連那些都失去了―失去了「芭比」,那個擁有跟「我媽」截然不同面貌的女人。此刻,她似乎帶著她所有的完美與不完美來到我面前,她的生命像是一幅繁複難解的壁畫,直到此時,才終於得以一窺畫的全貌,看見她是誰、她不是誰;明瞭她是多麼深刻地與我緊緊相依,卻又是如此徹底地不屬於我。
芭比想要捐贈器官的遺願並沒有達成,至少,沒有達到她想要的那種程度。她過世時,癌症與嗎啡已將她那四十五歲的身體摧殘成帶毒的肉體。最終,能捐贈的只剩下她的眼角膜而已。我知道,人眼的那個部分只不過是一片透明薄膜罷了,但我就是沒辦法以這種角度去想媽捐出去的東西。腦海中浮現的是雙水藍靈動、藍得令人屏息的眼睛,活在另一個人的臉龐上。
推薦閱讀:學習失去這堂課!專訪五月天石頭:「死亡這麼近,更要用力的活著」
我媽死後幾個月,我們收到一封感謝信,來自協助器官捐贈事宜的基金會。「因為她的慷慨,有個人得以重獲光明」―信上這麼說。想見那個人一面的強烈欲望幾乎令我發狂,我想看看那個人,想狠狠地望進他或她的眼睛裡,他或她一句話也不用說,我只不過是想要那個人看著我而已,只要看著我就好。我照著信上所附的號碼打了通電話,但我的要求很快就被回絕了。「身分保密是最重要的。」他們告訴我:「這是接受器官移植的人的權益。」
「我想對妳說明一下,有關妳母親捐贈器官這件事。」電話那一頭的女人對我說,她的聲音充滿耐性與安撫,令我想起我媽過世前後的日子裡,那些對我說話的悲傷輔導師、安寧病房志工、護士、醫生,還有殯葬業者⋯⋯他們的語氣總是那麼刻意,帶著近乎誇張的同情憐憫,同時卻傳達出另一種義涵:這件事,我只能一個人獨自面對。「移植的不是整顆眼珠,」那個女人接著解釋道:「只是眼角膜而已。眼角膜就是⋯⋯」
「我知道眼角膜是什麼。」我的理智突然斷裂了,厲聲說:「我還是想要知道這個人是誰。可以的話,去見他或她一面。我認為這是你們欠我的。」
我掛上電話,被哀慟的情緒擊倒。但在我心底深處那塊依然保有理性的地方,其實很清楚──那個女人說的對。我媽不在那裡。她那雙藍色的碧眼已經消失了。我永遠無法再凝望著它們了。

圖片|來源
當書頁燒盡後,我站起來,轉身打算回到帳棚裡,卻突然聽見東方一陣尖銳狂暴的吠叫聲。是一群郊狼。這種聲音,我在北明尼蘇達時聽得多了,所以並不會令我害怕。它反而讓我想起了家。我抬起臉望向天空,看著滿天星斗繁密燦爛、耀眼奪目,在黑夜中顯得格外明亮。我微微顫抖,心知自己能夠在這裡真的非常幸運,眼前的景色實在太美,美得令我捨不得那麼快進入帳棚。一個月以後,我會在哪裡呢?一想到屆時我已經不在步道上了,就覺得很不可思議;但事實就是如此。可能會在波特蘭吧,我猜,就算沒有其他理由,大概也會因為我已一文不名而留在那裡。我身上還有一些在愛許蘭剩下的錢,但當我到達眾神之橋時,那一點錢肯定也早已被我花光了。
接下來幾天,我通過天湖曠野區,進入俄勒岡沙漠,任由波特蘭在我腦中盤旋迴盪著。俄勒岡沙漠是一片平坦的高原,塵土漫天遍野,並有美國黑松木生長其中。我的旅遊導覽寫道,這裡曾經遍布著河流與湖泊,但在馬札馬火山噴發後,這些溪流河湖全被埋葬在大量火山灰與火山浮石底下。我在週六早晨抵達火山口湖國家公園,並沒有看見那座湖,而是來到了在湖岸南方七英里(約十一公里)處的一塊露營區。
這塊露營區不僅僅只是個營地。它是個熱鬧無比的綜合觀光區,包含停車場、商店、汽車旅館、小型自助洗衣店,還有目測大概三百人,他們有的正發動車輛的引擎;有的大聲播放著他們音響中的音樂;有的用吸管啜飲著巨大紙杯中的飲料;有的嚼食著從商店裡購買的袋裝洋芋片。面對著這幅景象,我既受到吸引,又感覺有點驚嚇。若非親身體會,我很難相信:在這裡,我只要隨意往任何方向走上短短四分之一英里的距離,就可以踏入另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我在這塊營地紮營過夜,興高采烈地到公共澡堂洗了個澡,然後隔天早上繼續往火山口湖前進。
導覽書沒騙我──當我第一眼看到火山口湖的時候,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站在海拔七千英尺(約二一三四公尺)高的岩石湖岸邊,湖泊的水面卻在我所立之地的下方九百英尺(約二百七十四公尺)處。火山口湖不規則的外圍環圈在我身下展開,湖水閃耀著那種難以形容的純淨海藍色,我這輩子從未見過。那座湖大約六英里寬(約九‧七公里),是一整片美麗無瑕的藍,只有巫師島(Wizard Island)在湖心隆起,它高出水面約七百英尺(約二百一十三公尺),是一座小型火山的頂部構成的,生長著歪曲的狐尾松。環繞湖泊周緣的湖岸大部分荒瘠崎嶇,只有狐尾松間或點綴其間,而在湖泊後方,遠處的山脈連綿起伏,像是它的背景。
「因為這座湖的清澈深邃,所以它可以吸收所有除了藍色以外的可見光,只將最純淨的藍反射到我們眼中。」一個站在我身旁的陌生人對我說,彷彿回應著我未曾說出口的驚詫。
「謝謝。」我對她說。「因為這座湖的清澈深邃,所以它吸收所有除了藍色以外的可見光」這個說法,聽起來是非常合理而科學的解釋;我卻覺得火山口湖還蘊含了某種難解的意義。克拉馬斯族依舊相信這座湖是塊聖地,我完全可以理解他們為什麼會這麼想。即使身邊滿是按著相機快門、駕著車緩緩開過的觀光客,也沒有關係;我仍然可以感受到這座湖的力量。它孤絕地座落在這片廣闊無垠的大地,遺世獨立、神聖而不可侵犯,好像它過去一直在這裡,未來也永遠會在這裡,不會改變,始終吸收著所有除了藍色以外的可見光。
我照了幾張照片,然後沿著湖岸,朝向供觀光客住宿的幾棟聚集建築物走去。因為週日的關係,園區內的郵局沒開;我別無選擇,只能在這裡待上一晚,等到隔天再去領取我的補給箱。那天陽光和煦,天氣終於變得暖和了些。我一邊走,一邊想著:當我決定出發往太平洋屋脊步道徒步旅行前,在蘇族瀑布市汽車旅館房間裡發現自己懷有身孕,若當初我沒有墮掉那個胎兒,現在差不多就是預產期了。我會在媽媽生日的這個星期生下孩子。那時候,當我意識到這兩個日期撞在一起時,感覺就像是有人狠狠揍了我一拳。但這個發現最終並未動搖我墮胎的決定,它只令我更懇切地祈求這個世界再給我一次機會。在我成為一個母親之前,請先讓我成為那個我應該要變成的人,讓我的人生可以不要踏上和媽相同的道路。
我深愛媽。但從很小開始,就下定決心:不要變得跟她一樣。我知道她為什麼在十九歲就大著肚子嫁給我爸,她並不是非常愛他。以前,我老愛纏著她問東問西,她總是搖搖頭說:「妳到底為什麼想知道這些?」但我不放棄,不斷問了又問、問了又問,她最後終於投降,把這個故事告訴了我。當她發現自己懷孕的時候,她有兩條路可以選擇:到丹佛去做非法墮胎手術,或是在懷孕期間躲到遠方城市去,生產後將孩子,也就是我姐姐交給母親,讓母親將孩子視如己出地撫養。然而,媽兩條路都沒選。她想要生下小孩,所以嫁給了我爸,變成凱倫的母親,然後是我的母親,然後是雷夫的母親。
我們的母親。
「我從來沒有真正為我的人生決定過什麼。」當她得知自己時日無多以後,有一次她掉著眼淚對我這麼說:「我總是照著其他人的期望去過日子。我一直都只是某個人的女兒或母親或妻子。從來沒有真正做過自己。」
「噢,媽咪。」我撫摸著她的手,沒別的話可說。
當時我太年輕,只能夠無言以對。
到了中午時分,我走進附近一棟建築底下的自助餐廳吃午餐。之後,穿過停車場,步行至火山口湖旅社。我背著「怪獸」,漫步在它那素雅的大廳之中,停下腳步悄悄窺視著餐廳。餐廳裡一桌桌坐滿了用餐的人,裝扮體面的旅客手中拿著裝滿夏多內白葡萄酒(chardonnay)與灰皮諾葡萄酒的玻璃杯,看起來就像是將淡黃色的寶石握在手中。我向外走到可以眺望火山口湖的長廊上,沿著一整列大型搖椅走,直到找到了並未與其他椅子相鄰的一張搖椅。
我花了整個下午坐在那張搖椅上,望著湖泊。我還剩下三百三十四英里(約五百三十公里)要走,然後我就會來到眾神之橋。可是,此時我竟有種感覺,好像我已然到達目的地。眼前碧藍的湖水已經將我長途跋涉至此的原因告訴我了。
這裡曾經是馬札馬火山―我提醒自己。這裡曾經是一座海拔將近一萬兩千英尺高的山脈,失去了它的心。這裡曾經一片荒蕪、滿目瘡痍,只有遍地的熔岩、火山灰與火山浮石。這裡曾經是個空蕩蕩的碗,花上千百年才被填滿。然而不論我多麼努力去想像,那些畫面依然無法浮現在我腦海之中―沒有火山、沒有荒地、沒有空碗。它們單純就是已經不在這裡了。如今存在此地的,只有那片寂靜無波的水,這片湖水,就是當火山、荒地、空碗踏上療癒之旅後,所轉變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