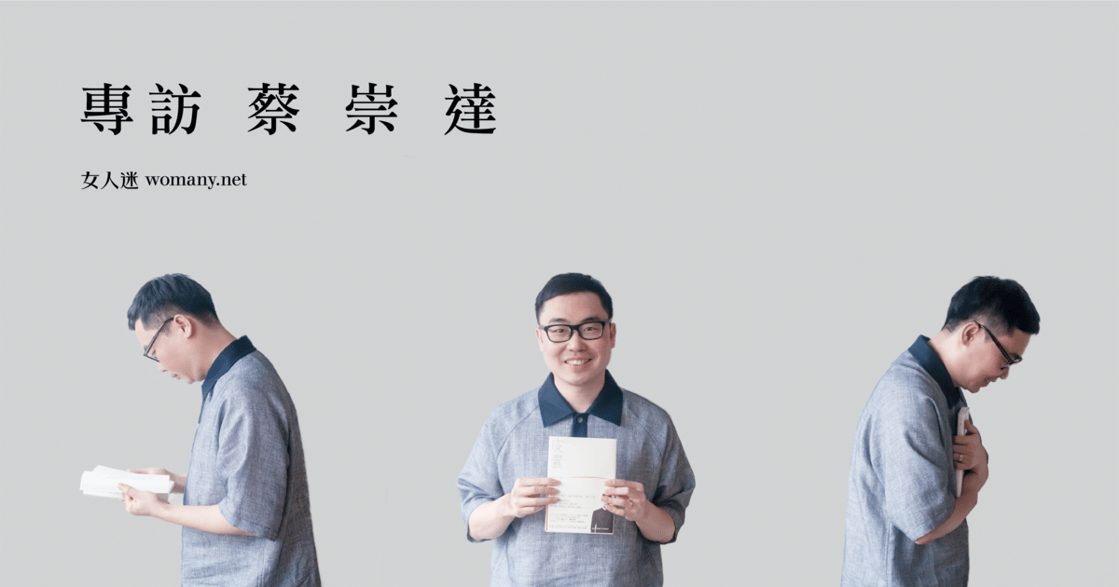專訪蔡崇達,細看他寫下《皮囊》赤裸告白,上篇看他以寫作直面自己,下篇談寫作如何理解他人。

32 歲那年《皮囊》終於上市,讓出版社意外的是,閩南男孩小鎮生活的短篇故事竟上架第二天就售罄,回神已狂銷 200 萬冊,蟬聯中國文學榜多年。他的皮囊裝載什麼勾動中國百萬人?他的膿包怎會碰巧裹住整個時代在中國結成的傷,一刀劃下去,兩百萬人都淚流?
蔡崇達這樣理解、這樣回答。
「當代社會,尤其是大陸,太劇烈了,劇烈到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就像你穿過一條很暗的巷子,走完後發現這裡疼、那裡也疼,都不知道被誰打的、怎麼打法。時代洪流是不會讓你知道自己是怎樣難受的,大家都需要找到傷從哪來,才會釋然。」
他想了想,「皮囊就是追蹤自己每個傷口來源,追蹤傷口跟時代、跟社會、跟自我關係的過程吧。」

生命如疾行列車,我寫字挽留
蔡崇達常說《皮囊》不是自傳,他說自己是沒資格寫自傳的,只是自剖後發現,這些命題並非自己獨有。
「命題都是共通的,比如年輕時總會面臨理想和現實的問題、故鄉與遠方的關係、親人的生老病死。讓人難受的命題,恰恰是作為人共通的部分。」
他以自己作為樣本切入,把人們不敢深掘的部分以文學筆法解說明白。「後來大家遇到故鄉與遠方、理想與現實、家人的離去,常常會說你看看《皮囊》吧。寫作者若為人們難解的命題表達了,表達得愈準確愈有力,就會穿透時間,人們自然會想要挽留他。」
「挽留」兩字是蔡崇達的說法,他寫字力求簡白,特殊用字必有故事。
書裏,他譬喻生命如向前疾駛且不斷各自旁岔的列車,他曾驕傲自己總有能力在捲入後狠心抽離。
「我一直嘗試著旅客的心態,一次次看著列車窗外的人,以及他們的生活迎面而來,然後狂嘯而過,我一次次告訴自己要不為所動,因為你無法阻止這窗外故事的逝去,而且它們注定要逝去。」
可當他經歷懦弱可愛的父親突然死亡、戰天鬥地的報社兄長抱理想猝死、石頭般頑強的阿太被輕易抹除,他深愛的人被時光列車拋下,不見蹤影,才知道自己其實多想打破玻璃去親吻想親吻的、擁抱他不願離開的。
看風景的心態終究太失重,現在他想挽留最珍惜的東西,即使次次無能為力但他次次願意,至少把記憶帶走,是對時間能做的唯一反抗。
如果人事物皆無法挽留,如果回憶亦不足牢靠,至少帶上一本能為你記憶時光的書,搭上這班疾行的生命列車。
「例如一代一代青年藉由〈少年維特〉表達年少煩惱,藉〈在路上〉表達叛逆時期感受。人的命題真是共通的,所以文學的力量很厲害,被挽留是作為寫作者最大的光榮啊!」他講著講著情緒慢慢高漲起來,也有點不好意思,說談得愈來愈嚴肅了。
「本來以為今天要聊點輕鬆話題的!」他說完,我們大夥開心對視而笑,其實對話是沒有輕鬆沈重分別的,只要當下有自在就好。
人生方法論與寫作,受神婆啟發最多
自在的前提,是知道如何「不在」自己之中,不被自己圍困。
蔡崇達的人生態度受神婆啟發最多,那位神婆就是他書裏開篇寫的阿太,蔡崇達笑說「我現在的方法論和生命觀是很像神婆的。」
所謂神婆,經常用浮在半空中眼光俯視人間和自己,「如果靈魂一直在自己軀體,會被自己各種慾望、疼痛、感覺給充滿與抓住,掙脫不出來。」
「我阿太交給我最重要的人生方法論,是把自己當作客體。你適當抽離、俯視自己,看清內心真正構成,才能真正解脫自己。要知道讓你難受的真是這件小事,還是累積了某種東西在這被觸動了。」

內心秩序必須溫柔妥善地安排,不要反被各種瑣碎情感統治。這不容易,但可以練習。特稿寫作就是一種練習方法:從鉅觀角度俯視自己站立位置。社會學、人類學提供超脫個人的結構型視角,對於鉅視能力很有幫助。文學則是微觀的,借蔡崇達說法,文學是人內心紋路的學問。
他自己也說了:「我用社會學、人類學、文學,三重眼光來看待時代、社會、人與人之間、人與人自己之間,是怎麼把自己雕刻出現在的樣子。原先我的工作是報導他人內心的真相,當我覺得有足夠能力了,也試圖藉由這套方式來剖析我內心。」
讓他轟動中國的特稿〈審判〉是這樣的作品,《皮囊》也是。聽起來無敵不敗,可人生像一張問卷,寫了一題還有下一題,不同階段有不同命題待解,說得再瀟灑也沒用。他至今仍有一關過不了,估計還要花他二十餘年,這關就是女兒。
婚不一定要結,但小孩可以有
我還想急著問他女兒的事,他卻幽幽先說了個故事。
台灣 921 大地震時候泉州也震動,他父親急得一路往家裡跑,「他跑到拖鞋都掉了,拿著斧頭把門一個個劈開,終於找到我,一把抱緊一路哭喊:心肝寶貝嚇死我了!」蔡崇達模仿自己父親,把我們逗笑也鼻酸 ,他當時醒了看到父親哭,「覺得特別丟人又失敗,假裝繼續睡!」
《皮囊》其實本來還有篇文章,出書前拿掉了,就叫做〈失敗的父親〉。
「〈失敗的父親〉第一句話就是:父親總是失敗的。其實父母總是容易失敗,他們把所有能給的東西都給你,因此你最容易發現他們的局限,容易拋棄他、嫌棄他。」
父親離開之後,蔡崇達才意識到父親已為他做了所有能做的。「我曾覺得自己一輩子都無法為人付出到這程度。」他說著便安靜下來。

直到女兒出生,他訝異發現自己也有和父親一樣宏大而柔軟的情感。
蔡崇達說,看著女兒坐在地上玩手指、給自己講故事,「我記起自己忘記的事,忘了自己小時候也喜歡玩手指、說故事給自己聽,人的很多密碼會在孩子身上長出來。老婆本以為要去看醫生,我跟她說不必了。」
接著,他發現自己像他父親那樣愛護著女兒、願為她做一切事,他感到父親確實有部分留在他身上。「突然間,某種踏實感是:我父親的血在我身上、我的血在我女兒身上,我感到自己是一個有過去、有未來的人。」
這番言論太催生,本來覺得人生不必小孩的也被撩撥,我試著想像生命延續可以不只在個人身體;想像自己無懼付出;想像另種生存樣態;想像生命逝去後有另種方法與你共在。蔡崇達乘勝追擊:「一定要生、一定要生!我甚至可以很極端的說,你可以不結婚,但是你一定要有小孩!」
在場三個女生全部哈哈哈笑個不停。他像在下午茶被冷落的堂哥,一直補充,「我說真的,真的,你會理解原來這是世界上最好的禮物。」
即使不生小孩,世上仍有踏實相繫的情份。
蔡崇達在書裏沒談及他的愛情觀,我趁機追問。他以對比法說明,「現在都市說的愛情,是愛,不是情。是賀爾蒙,但不是情感。」
「福州聚春園(註一)的老闆跟我講過一個事,他說辣不是味覺、是刺激。愛是刺激,來得快去得也快。」蔡崇達總結是,情比愛重要,香比辣的刺激重要。
「真正的情感是,人生很多部分相通相容、互為彼此的那種感覺吧。人終極內心有很多部分表達不出來,所以需要跟與你相通的人靠近,你們兩個在一起就覺得,不孤獨。」
可是都市現代性液態流動,時間與生活容易是破碎的,所有堅固的都已煙消雲散,怎有足夠時空將愛戀踏實成情感?這題只能靠各人摸索出答案。
不過蔡崇達也提供了對比參照,「如果兩人老覺得需要相互解釋,就肯定是出問題了,因為你沒有那個能力解釋清楚自己,對方也沒有。」
他說完這些,我們都安靜了一會。窗外信義區站著幢幢高樓,天光在樓間漸暗,霓虹燈點點繁亮,入夜後感受城市欲望正伏流湧動。
邏輯框不住的慾望,讓人成為渾然一體藝術品
書中〈海是藏不住的〉文章裡,他以海譬喻慾望,我問他這麼多年之後,找到處理或欣賞各種慾望的方法了嗎?
他誠懇點頭,眼神像孩子一樣清澈光亮起來,看著我說,「找到了。」
「首先就是承認它,每人身上都有光明面和陰暗面,都有,所以不用把它當回事。彼此的陰暗面不是敵人,是我們要共同面對的;光明面則是可以共同享有的。」因為亮面和暗面都值得接受,進而能夠審美它。
「我老說理解是對自我和他人最大的善舉,宣判一個人是容易的,宣判就是把他身上某個剖面拎出來、釘在邏輯概念的框架裡處死,這是粗暴不負責任的,而且沒什麼了不起。在我看來,理解力比宣判力重要太多。」
他因此不喜歡時事評論家,做媒體期間看著太多人藏著己身暗面、拉著自己的明面去批評別人的暗。「宣判他人,本身是罪惡的。理解他人才是真正的力量。」
理解他人,才是真正的力量。
「要有理解力就必須謙卑,謙卑才看得見更多人。」
說到這裡,他忍不住說,「其實這世界上最美的風景啊,是一個個人。你看人心有很多相互矛盾、衝突著的地方,最終又渾然一體,你不覺得這是最棒的藝術品嗎?」
蔡崇達說自己現在可誠實了,真不開心他都會直接講的,問對方怎麼做那些事情呢?「理解了,ok 啊,跟對方說下次我不一定處理得好,但會努力讓自己這塊不那麼敏感的,我講話都是這樣子。」
現在蔡崇達周邊人都把他當小孩,沒人把他當老闆,都是「欸!那個達達,來來來」他就回一句「幹嘛」。
他愈活愈沒把自己當回事,「我期待自己到老都是周伯通,愈通透就愈無我。中國傳統哲學中常有,什麼物我兩忘、逍遙遊、天人合一,都是沒把自己當回事,把自己當作一片葉子,也把一片葉子當作自己。其實就是這樣子啊!唯一處理得不夠好的是,我還很擔心自己的女兒嫁出去。」
我們又笑,笑聲通透迴盪在專訪房間,空氣中我感受這不斷迴響、值得挽留的片刻,二十年後若有機會再見,再來問問蔡崇達嫁女兒的命題解決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