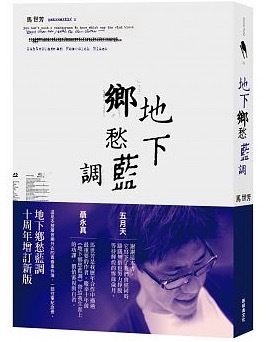在風雨縹緲的那個時代,台灣像是飄盪於動盪年代的孤島,四周濃霧看不清未來的輪廓,卻在死寂的年代裡有一群人不甘沉默,用搖滾鼓譟的聲音敲響自由民主的鑼鼓;用堅定卻溫柔的步伐獨步於這時代,走出一條開創未來的啟蒙道路。「美麗島」是我們美麗的台灣島,從〈美麗島〉到反服貿,那些前輩走過的社運如今成為我們的書本上的扉頁,而親愛的,這個時代的我們,也正創造著歷史,皆以一顆期望更好的心,去喧嘩青春憧憬未來。
「美麗島」的前世今生
1973 年,「笠」詩社的前輩女詩人陳秀喜寫了一首題為〈台灣〉的詩,反映了那個風雨飄搖的時代,同時也把對未來的寄託,重新放回了腳下這片土地:
形如搖籃的華麗島/是 母親的另一個/永恆的懷抱
傲骨的祖先們/正視著我們的腳步/搖籃曲的歌詞是
他們再三的叮嚀/稻 米/榕 樹/香 蕉/玉蘭花
飄逸著吸不盡的奶香/海峽的波浪衝來多高/颱風旋來多強烈
切勿忘記誠懇的叮嚀/只要我們的腳步整齊
搖籃是堅固的/搖籃是永恆的/誰不愛戀母親留給我們的搖籃?
七○年代初,台灣被迫退出聯合國,短短三年不到,就有二十多個邦交國陸續和台灣斷交。彼時我們對這片島嶼最常用的稱呼是「自由中國」,警察滿街追捕長髮「嬉痞」然後抓進警局剃光頭,年輕人最時髦的去處是「野人」、「艾迪亞」、「稻草人」這些播放、演唱著搖滾樂的咖啡室。披頭的翻版唱片一張八塊五毛,牯嶺街的書攤除了可以挖到三○年代「陷匪」和「附匪」作家的禁書,還有美軍帶來的《生活》畫刊,裡面登載著越戰實況、校園示威和年輕男女抽大麻的照片。
保釣運動從台灣校園延燒到北美,而收音機裡震天價響、反覆播送的口號,是「莊敬自強/處變不驚」。
就在這樣一個既壓抑又激昂的時代,一群青年人從存在主義的蒼白和搖滾樂的喧囂中抬起頭來,發現了洪通的素人畫、朱銘的木雕、陳達的恆春民謠,還有黃春明和王禎和的小說。那是許多人的「啟蒙時刻」,他們不安地蠢動起來—那是一種糅雜著素樸的正義理想(以彼時的政治氣氛,沒有人敢公然提起「左」這個形容詞)與純真的國族情感,在壓抑中漸漸累積的一股衝動。
那股衝動,或許可以翻譯成「在這樣一個悶到不行的時代,我們非得幹出些什麼事情不可」。
推薦閱讀:告別被歷史弄髒的經血:《Lady's 尖頭們》上空革命
於是段氏兄弟創辦了《滾石》雜誌,成為「滾石唱片」的前身。向子龍把陳達老人請到台北,從大學校園一路唱到「稻草人西餐廳」。張照堂把電視台的「新聞集錦」玩成實驗性的影音拼貼,再過幾年就要和雷驤、杜可風、阮義忠一起改寫台灣紀錄片史。林懷民的「雲門舞集」則把八家將和宋江陣都搬上了國父紀念館的舞台……。
1974 年,胡德夫在國際學舍辦了第一場創作發表會。1975 年,楊弦在中山堂辦演唱會,為余光中詩作譜曲,後來出了唱片,轟動全國,成為點燃「民歌運動」的燎原之火。1976 年,淡江畢業的菲律賓僑生李雙澤在一場演唱會上拿著可口可樂跳上台,說自己從國外回來,喝的卻還是可口可樂,接著憤然質問台上的歌手:你一個中國人唱洋歌是什麼滋味?請問我們自己的歌在哪裡?然後他在滿堂倒彩中,唱起了〈補破網〉。
「唱自己的歌」漸漸成為共識,結合了當時同仇敵愾的民族情緒、青年世代的自覺、初初萌芽的鄉土意識和不假他求的原創精神,它們都是「民歌運動」早期最重要的思想基礎。
李雙澤在 1977 年夏天一口氣寫了 9 首歌,包括後來成為傳奇的〈美麗島〉。它的歌詞脫胎自陳秀喜的詩,由淡江的年輕老師梁景峰改寫而成:
我們搖籃的美麗島 是母親溫暖的懷抱
驕傲的祖先們正視著 正視著我們的腳步
他們一再重複地叮嚀 不要忘記 不要忘記
他們一再重複地叮嚀 篳路藍縷 以啟山林
婆娑無邊的太平洋 懷抱著自由的土地
溫暖的陽光照耀著 照耀著高山和田園
我們這裡有勇敢的人民 篳路藍縷 以啟山林
我們這裡有無窮的生命 水牛 稻米 香蕉 玉蘭花
李雙澤為什麼能夠寫下這樣完美的旋律,是一樁無解的謎。唯獨〈美麗島〉這首歌,詞曲咬合之無懈可擊,旋律之美麗懾人,在在超越了時空環境的局限。假如李雙澤繼續寫歌,他還會留下什麼樣的精彩作品?我們永遠得不到答案了— 1977 年 9 月,李雙澤為了救人而淹死在淡水海邊,時年 28 歲。他自己還來不及替〈美麗島〉留下錄音,葬禮現場播放的歌,是老友胡德夫和楊祖珺合唱—前一天晚上,他們連夜整理李雙澤的手稿,在「稻草人」西餐廳錄下了這首歌傳世最早的錄音版本。
因為好聽易學,〈美麗島〉很快就傳唱開來,之後的兩三年,幾乎每一場民歌演唱會,都會以全體歌手和觀眾合唱〈美麗島〉作結。1977 年,胡德夫在陶曉清籌畫的民歌合輯《我們的歌》裡演唱了〈牛背上的小孩〉、〈匆匆〉、〈楓葉〉幾首作品,這是他第一次錄唱片。1979 年 4 月,楊祖珺首張專輯收錄了〈美麗島〉,是這首歌第一個公開發表的版本。
然而唱片公司風聞楊祖珺投入社運工作,四處到工廠、農村和學校演唱,是個「問題人物」,發行才 2 個月,就把專輯回收銷毀了。她和戰友胡德夫,從此被貼上「偏激分子」的標籤,不僅作品被全面封殺,也無法再參與演唱會(否則警備總部會找主辦單位的麻煩,同台的歌手還會被迫寫悔過書)。誰也不會想到,胡德夫再度為唱片獻聲,竟要再等二十多年,而楊祖珺後來投身反對運動,更是徹底和音樂圈斷絕了往來⋯⋯
推薦閱讀:從香港旺角「魚蛋革命」反思暴力的存在意義
專輯被銷毀後兩個月,黨外雜誌《美麗島》創刊,刊名是周清玉從唱片得到的靈感。4 個月後,高雄「美麗島事件」爆發,這首歌也自此萬劫不復,從所有公開場合消失,轉入地下,等到八○年代晚期禁忌鬆綁的時候,除了極少數「運動圈」分子,大多數人都忘了它怎麼唱,甚至壓根兒不知道「美麗島」曾經是一首歌了。

離開音樂圈,胡德夫和楊祖珺雙雙投身反對運動最前線,他們曾經在競選的卡車上合唱〈美麗島〉、在政見發表會現場義賣的錄音帶裡灌唱〈美麗島〉、在群眾運動的場合教唱〈美麗島〉。二十幾年過去,他們一路經歷了我輩難以想像的磨難與挫折。即使在戒嚴體制崩潰之後,仍然有很長一段時間,他們不太願意提及昔日歌唱的那段歲月,彷彿一旦憶起那些洶湧澎湃的歌,好不容易癒合的傷口又要被撕開。
直到 1996 年,王明輝力邀胡德夫參與黑名單工作室《搖籃曲》專輯錄音,我們才再度聽到他久違的聲嗓。長年的顛沛流離,在他的肉身和心靈都留下了難以想像的傷痕。Kimbo(胡德夫的別名)已經滿頭白髮,而他的歌聲,和 1977 年意氣風發的錄音相比,愈發顯得深邃、黝黑,像是剛剛踏出死蔭的幽谷。
當年和胡德夫一起清談歌唱的老友、和他一起衝州撞府的戰友,如今有許多都變成了台灣最有錢、最有權的人。敏督利颱風來襲時,他用幾通電話就調到了賑災物資、弄到了直升機,然後立刻拋下專輯工作,往災區飛去。然而,無論過眼的錢財權位是多麼令人咋舌, Kimbo 自己從來沒有過上幾天好日子。他當過油漆工,在工地扛過水泥、釘過板模、綁過鋼筋……,別人替他不平,他卻說了一個小故事:
有一次在阿里山達邦部落的河裡,看到一群小孩子在游泳,小朋友很快樂地分享那個河水,又說著「我們原住民」怎樣怎樣⋯⋯,很自信很驕傲。那時我心裡想,如果我曾努力做過什麼事,所求也不過如此吧!自己要有信心,能夠站起來,像個浪人也沒有關係⋯⋯。
這些年,日子再怎麼難過,胡德夫始終沒有忘記音樂。生命中殘酷的磨難,卻讓他的歌聲與琴藝真正「熟成」了。近年,他的現場演出在年輕世代之中找到了許多知音,這些年輕人多半在李雙澤逝世的時候都還沒出生,卻在 Kimbo 的歌聲裡找回了熊熊燃燒的青春之火。
近幾年,胡德夫演唱〈美麗島〉的時候,會在最後加上一段新詞。他說,這是回應故友李雙澤的答唱,想要告訴他,我們生長的地方,的確是美麗的:
我們的名字叫做美麗/在汪洋中最瑰麗的珍珠
福爾摩沙/美麗/福爾摩沙⋯⋯
2005 年,胡德夫 55 歲,終於出版了第一張個人專輯《匆匆》,他行走江湖、吞吐著大山大海的聲嗓和鋼琴,直抒胸臆、渾然天成。文化圈的顯赫人物用盡最高級形容詞讚美 Kimbo ,然而他只尷尬地說,面對這些褒獎與稱讚,他「極不對位、極不自在」。他說:
我唱歌無所求,我所歌頌的山川和人們,早已給我所需的⋯⋯雲海、山脈和清流,和波濤。
2006

(圖片來源)
2016 附記:
這篇文字是林懷民先生邀我為雲門作品《美麗島》節目冊所寫。《美麗島》由布拉瑞揚編舞,胡德夫現場彈唱並為舞者伴奏。那是陳水扁連任的時代,藍綠對立劍拔弩張,〈美麗島〉誰都不討好。儘管演出陣容如此厲害,門票並沒有賣完。
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我每聽〈美麗島〉必落淚。直到 2006 年聽到一群泰武國小原住民孩子合唱〈美麗島〉,清澈而無心機,極是動人,乃覺悟這首歌原本就該是這樣:溫暖、大氣、明亮。之後再聽,便能漸漸將歷史沈澱的悲情洗去。
我輩人對〈美麗島〉的種種情結,現在的青年大概是完全不在意了,願意傳唱的人,似乎也不若以前那麼多了。這倒也不見得是壞事,至少它還不至於被當權者教條化、儀典化,變成有體無魂的軀殼。
2014 年反服貿群眾佔領立法院,聲援的人潮很快擴散到附近的街區。有人在佔領現場唱起〈美麗島〉,大家漸次加入,都唱得很慢很溫柔。這首歌總是不會被遺忘的,這樣也就可以了。
推薦閱讀:一夜不眠的台灣憤慨:反服貿黑箱的現場直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