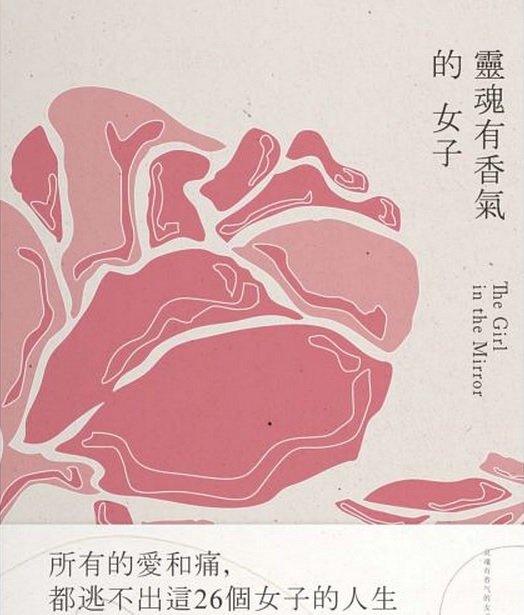你會看見一個任性女子的桀驁不遜,聽愛的慘慘戚戚也濃烈瘋狂。接著,讓我們一同閱讀這個為愛而生的女子。
打著「依賴」旗號的死纏爛打,都很難逃脫憔悴失落的結局。情感世界裡最終的贏家,無不是泰然處之、順其自然、全情享受的高人,不管他們是贏得了愛情、贏得了完滿,還是贏得了超逸灑脫的人生。
在白話文初起的年月,即使是現代詩的鼻祖,也顯出簡單與粗糲。
胡適那首拉開了中國現代詩大幕的《蝴蝶》,今天讀來頗為稚拙:「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不知為什麼,一個忽飛還。剩下那一個,孤單怪可憐。也無心上天,天上太孤單。」用當下的標準回望民國的經典,大多史料價值超過文學價值。但是,也有例外,比如魯迅、徐志摩、張愛玲,閃耀著光輝的天才文字穿透了百年的塵埃,如陳年普洱般醇釅。
當然,也少不了蕭紅。

第一次讀蕭紅的《生死場》便被奇妙的比喻驚艷到,她寫「菜田裡一個小孩慢慢地踱走,在草帽的蓋伏下,像是一棵大型的菌類」;她眼中的林蔭道「像是動蕩遮天的大傘」;她看「菜田的邊道,小小的地盤,繡著野菜」。別緻、具象、靈動,好似透過孩子明澈的眼打量世界。只是,電影與傳記最津津樂道的,除了她的文字,便是她兩次懷著別的男人的孩子,嫁給另外一個男人。
1911年出生、雙子座的蕭紅深得祖父張維禎寵愛,祖父蔭庇下短暫的童年是她人生最美好的回憶,甚至,《生死場》中的場景大多來自記憶中祖父的東北夢幻花園。
父親張廷舉堅持將她許配給小官僚之子汪恩甲,她拒絕,便以抽煙、喝酒對抗,與有家室的表哥陸哲舜一起出走,在北京求學、同居,被家族不容,斷絕經濟支持。表哥退卻後,她便去找汪恩甲,與他同居,同抽鴉片。
汪恩甲工資入不敷出,她卻懷孕了。汪回家求援,被家人扣住,她去理論,被汪家怒斥。於是,她去法院告汪兄代弟休妻。法庭上,汪恩甲竟臨陣倒戈,表示自願離婚,法庭當場判決兩人離婚。
同場加映:愛走了,情還在:離婚是幸福的另一種延續
她怒不可遏地衝上街頭,汪恩甲追來道歉,兩人匪夷所思地和好。這對離異夫妻在旅館賒欠食宿費六百多塊錢之後,汪恩甲藉口回家取錢,從此杳無音訊。此時,她已懷孕五個月。
蕭紅遇到蕭軍之前的情事,這已經是最精簡的版本。

蕭軍與蕭紅
從前看《蕭紅全傳》,我不厚道地想,這些行為怎麼看都像一個任性女子的瞎折騰,和反封建沒有半毛錢關係。可見生逢其時很重要,生對了時代,私奔便是一場反封建的抗爭,不然,便是一樁顏面掃地的緋聞。如今,被蕭紅的文字打動後再看這段經歷,也生出幾分體諒,或許,她是真有苦衷吧。
母親早逝,父親疏淡,繼母薄情,蕭紅如大多數親情缺失的女子一般,有強烈的情感依賴症,她們把愛情當做救命稻草般緊緊抓住不放,雙子座天生的率性,以及天馬行空的行為模式,也讓她吃了不少苦頭。在與家庭鬧翻後,追愛和抗婚並不是她二十歲時離家出走最重要的目的,她這次逃離,更多是為了讀書。
而失卻了家族的支持,便只好倚靠陸哲舜、汪恩甲。但這些男人看重的,僅僅是一個女人的身體。身無長技出走的「娜拉」,除了輾轉在不同懷抱討生存,似乎也沒有更好的出路。
1938年,她在重慶塔斯社分社接受 B.H. 羅果夫的訪談時遺憾地說:「我很想上大學,但是無法實現。」
這算是道出了心頭的無奈與苦楚。最終,她踩著這些淒惶往事搭建的橋梁,遇見了蕭軍。負債累累的蕭紅聽說旅店老闆要把她賣去妓院抵債,情急之下寫信給《國際協報》求助,副刊編輯裴馨園便委託蕭軍去探望。兩人相遇,言語投機,彼此傾心。
蕭紅在短詩《春曲》中陶醉:「那邊清溪唱著,這邊樹葉綠了,姑娘啊,春天到了!」

雖然蕭軍籌不到解救她的巨款,一場肆虐哈爾濱的洪水卻給她帶來福音,旅館一樓被淹,她趁亂逃走。然後,一個猛子扎進蕭軍的懷抱,終生都抬不起頭。熱戀時,她眉梢眼角都是歡喜,詩裡的愛情濃得化不開:
你美好的處子詩人,來坐在我的身邊。你的腰任意我怎樣擁抱,你的唇任意我怎樣吻,你不敢來我的身邊嗎?情人啊! 遲早你是逃避不了女人!熾烈時,即使窮困潦倒,依然有情飲水飽。
「只要他在我身邊,餓也不難忍了,肚痛也輕了。」
兩個人黑麵包加鹽,你咬一口,我咬一口,鹽抹多了還開玩笑:這樣度蜜月,把人鹹死了。偶爾去小飯館改善一下,把饅頭、小菜、丸子湯吃到足,再買兩顆糖,一人一顆,何止嘴裡是甜的,心裡更是蜜一般。情意相投時,兩個人合拍極了。
蕭軍曾說,他倆都是「流浪漢」式的性格,從不悲觀愁苦,有時候,蕭軍拿著三角琴,蕭紅紮著短辮,兩人在街頭旁若無人地邊彈邊唱,滿是肆意的瀟灑。偶爾吵架,兩個人搶著喝酒,他醉極、氣極在地上打滾,她悔極、痛極自責不已。
推薦閱讀:【不是影評】永遠失落的《黃金時代》,柔軟而鏗鏘的蕭紅
1935年,她在魯迅的幫助下發表《生死場》,他出版《八月的鄉村》。一對文學伴侶聲名鵲起,上海文壇向他們敞開大門,約稿紛至沓來,各類刊物拉他們做台柱子。苦撐四年,兩人終於從飢寒交迫的隆冬,走向名利加身的暖春。
可是,愛情卻向著反方向漸行漸遠。

湯唯在《黃金時代》飾演蕭紅
蕭紅曾說:「我就向這『溫暖』和『愛』的方面,懷著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的確,尋愛求溫暖似乎是她人生最大的寄託。遺憾的是,想法天真、拒絕長大的蘿莉們大多結局不妙,猶如現世的冰寒總是留存不住情感的微溫,男人的肩膀總是靠不住女人的爛漫。
主張「愛便愛,不愛便丟開」的蕭軍四處留情,對著美艷的新人抒情:「有誰不愛個鳥兒似的姑娘! 有誰忍拒絕少女紅唇的苦!」蕭紅黯然神傷:「我不是少女,我沒有紅唇了。我穿的是廚房帶來油污的衣裳。」
蕭紅欣賞史沫特萊《大地的女兒》,蕭軍卻以取笑女作家為樂,強詞奪理,她氣哭了,他卻說:「再罵我揍妳。」苦悶的蕭紅形容憔悴,臉都像拉長了,臉色也蒼白得發青,對人冷淡而心不在焉,她常常往魯迅家跑,一坐就是大半天。
好涵養的許廣平也忍不住對胡風的妻子梅志訴苦:「蕭紅又在前廳,我哪來時間陪她,只好叫海嬰去陪她,我知道,她也苦惱得很。她痛苦,她寂寞,沒地方去就跑這兒來,我能向她表示不高興、不歡迎嗎? 唉! 真沒辦法。」
通常,女作家的情緒敏感而纖細,些微的慢待便足以讓她們驚惶。究竟是蕭紅神經粗壯得足以在許廣平的不滿中御風前行,還是,失卻了蕭軍的依靠,她太想找到另一個支撐?
於是,端木蕻良出現了。
1938年,蕭紅懷著蕭軍的孩子,與小她一歲的端木在武漢舉行了婚禮。很多人疑惑,懷著別的男人的孩子和另一個男人戀愛,她得有多讓人愛呢? 這究竟是衝動還是真愛? 抑或是其他難以啟齒的原因?他們幸福嗎? 細節透不出深愛的跡象。
他的家人對他娶一個情感經歷複雜的孕婦既驚訝又惋惜。似乎從來沒有人看過他們有說有笑地並肩走在一起。他當著她朋友的面,讀她寫的懷念魯迅的文章,鄙夷地笑個不停,說:這也值得寫,這有什麼好寫?
他打了人,讓她去跑鎮公所。而她,挺著懷孕八個月的大肚子在宜昌碼頭絆倒,是陌生人把她扶起來。她對聶紺弩說,端木就是「膽小鬼、勢利鬼、馬屁精,一天到晚在那裡裝腔作勢」。這並不是婚後的抱怨,而是婚前的指責。
她得有多麼寂寞空虛冷,才能死死抓住一個讓自己如此鄙夷的人不放?依賴型人格的女子,總是習慣性地倚靠別人,卻不可思議地充滿自我懷疑,懷疑自己不夠美好、堅忍、獨立、強大,不足以支撐搖搖欲墜的人生。
推薦閱讀:「至少,他對我很誠實?」放下情緒勒索換來的假性親密
可是,自己不足信,他人豈足信? 那些被她視作情感支柱的男子深知吃定了她,他們不屑、慢待、輕賤她,因為知道她捨不得走,她下不了狠手對自己,就輪到別人下狠手對待她。

這對相互不屑的夫妻共同生活了三年,在抗戰的炮火中一同逃到香港。蕭紅肺結核越來越嚴重,端木每次出門,她便擔心自己被遺棄,非常絕望,待他返回,才會平靜。她總是情緒反覆,一會兒覺得自己會健康起來,還要寫《呼蘭河傳》第二部,一會兒又怨恨端木,覺得早該與他分開。惶恐焦慮中她又開始亂抓救命稻草。
這次,被抓的是她弟弟的朋友、小她六歲的東北作家駱賓基。駱賓基受了端木的幫助,答應留下照顧病中的蕭紅。據說,蕭紅在端木離開時,曾經答應如果她的病情好轉,一定嫁給駱賓基。
病床前的愛情和承諾,真是讓人匪夷所思。炮火紛飛的戰亂時期,人人把活下去當成首要任務,一個病入膏肓、驚惶而神經質的女作家,就算她願意以身相許,對於一個只見過兩次面、在香港人生地疏的二十五歲男青年來說,只怕更像一個沈重的負擔吧。
於是,駱賓基忿忿寫道:「從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開始爆發的次日夜晚,由作者護送蕭紅先生進入香港思豪大酒店五樓以後,原屬蕭紅的同居者對我來說是不告而別。從此以後,直到逝世為止,蕭紅再也沒有什麼所謂可稱﹃終身伴侶﹄的人在身邊了。而與病者同生同死共患難的護理責任,就轉移到作為友人的作者的肩上再也不得脫身了。」
這哪裡有什麼愛情,分明是遭遇違規卸貨的憤怒。三十一歲,她終於在日軍的轟炸中缺醫少藥地死去。死前,親筆寫下自己的心情:「半生盡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
每每讀到那兩個夢囈似的「不甘、不甘」,我便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地想:既然看出了別人的嫌棄,就不能有些骨氣? 一定要用混亂的步法,把人生下成一盤死棋?
果真,一個女子的任性,對文字是大幸,對人生卻是大諱。她死後,與她交好過的男人互為情敵,爭吃陳年老醋。駱賓基與端木蕻良因《呼蘭河傳》的版權歸屬反目成仇,從香港返回內地後分道揚鑣,從此形同陌路。她其餘著作的版權,解放後端木蕻良倒是全都捐給了國家。為了《呼蘭河傳》的版權,她的兩個妹妹又和駱賓基打過一場官司。這些生前折騰出的是非,身後都不肯放過她。
那個被她稱為暴虐的父親張廷舉,在她離經叛道的私奔之後,因教子無方被解除「省教育廳」秘書的職務,調任巴彥縣督學兼清鄉局助理員。在呼蘭上學的張家子弟不堪輿論壓力,紛紛轉校離開家鄉,她的弟弟張秀珂孤獨地隨父親由北滿特別區第一中學轉學到巴彥縣立中學,途中,她的父親看著幼子,無奈而感傷。
她肆意追尋自由、學業與愛情的時候,可能根本沒有想到,自己的不管不顧給家人留下了一個爛攤子。
當然,她是反封建的鬥士。她還曾經有過兩個孩子。第一個是女孩,生下來沒幾天就送給了公園臨時看門的老人,老人搬家之後,便失去聯繫。第二個是男孩,她堅決不肯到隔壁育兒房餵奶,任憑孩子的哭聲傳來,任憑周圍人苦勸,看也不肯看孩子一眼,直到第六天孩子被別人抱走,她始終未看孩子一眼,也沒讓孩子看她一眼。
有些時候,她也著實狠得起來。或許她知道,她這樣一個永遠長不大的女孩,似乎沒有能力再去承擔另一個女孩或者男孩的人生。和她濃烈的愛情相比,她的母愛有點稀薄。
她折騰了三十一年,不知是否明白:遇到一個好男人,從此過上幸福的日子,很好。遇不到,一個人,善待自己,也很好。
心 靈 療 養
在愛情中,有多少如蕭紅一般的女子,丟失了自己,急急忙忙地控制,振振有詞地用依賴去損耗兩個人關係裡的浪漫和輕柔,最終得不償失地迷失自己,丟失了原先的愛。所有活得不自信、特別焦慮的人都試圖牢牢掌控兩個人、三個人,或者多個人的關係,這種打著「依賴」旗號的死纏爛打,都很難逃脫憔悴失落的結局。
情感世界裡最終的贏家,無不是泰然處之、順其自然、全情享受的高人,不管他們是贏得了愛情、贏得了完滿,還是贏得了超逸灑脫的人生。愛是享受,而非依賴。永遠做自己,而不是妳以為別人會喜歡的那個人。最終,不管是一個人、兩個人、三個人,或者其他方式的人生路,都能走得愉悅和通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