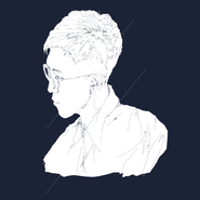對於「成為母親」感到恐懼、無力嗎?《平行母親》透過拆解母女創傷,帶妳重新找回母性力量。
不少女性都喜歡跟小孩子玩耍,看到新生的嬰兒更是兩眼發亮,不過她們未必想自己生養小孩。
在諮商工作裡,我蠻常聽見的是:「我不想重蹈我媽的覆轍!」。
簡單的一句話,道出了女性在成為母親的路上其實深受自身的母女關係所影響,使她們在某種恐懼、不自信、無力感的籠罩之下,質疑自身的「母性」力量,且對「母職」缺乏勝任感。
今天順著西班牙導演阿莫多瓦(Pedro Almodovar)的電影《平行母親》(Madres Paralelas,2021),把主角當作個案般去聚焦感受女性「成為母親」的悲歡苦樂,和思考如何重捨母力!
《平行母親》:母性本能非必然!
女性在成為母親前有著不同的心態:喜悅而期待、期待但有點焦慮、幾乎陷在憂慮之中、對生命巨變的恐懼、未能消化的困惑⋯⋯。
《平行母親》呈現的是一組對比:嘉妮(Janis)是專業的攝影師,她跟有妻之夫阿杜羅(Arturo)上床後懷孕,但她並沒有要阿杜羅離婚好為她負責,反而她相信自己能獨自撫養,並樂觀地期待孩子賽希莉亞(Cecilia)的到來。
在隔壁床待產的是還未成年的學生安娜(Ana),在她的想像中小嬰兒安妮塔(Anita)是要來毀掉自己的未來,因為她是被二人強暴懷孕的,她甚至不確定當中誰才是父親。
人生總是被許多實際、無奈、痛苦的事推著走,懷孕過程可能被好好照料、或只感到孤獨哀愁,但十個月後孩子總會出生,生命得翻至新的一頁。
這新的一頁有時候又會顛覆想像,曾有一位不想生小孩的女性,在生產之後成為朋友間公認的幸福媽媽,天天在社群上曬寶寶。
推薦閱讀:「懷孕,讓我成為更強大的自己」有一種勇敢,叫成為母親

圖片|《平行母親》劇照
電影中安娜的母親泰瑞莎以為女兒跟自己一樣缺少母性本能(maternal instinct),卻意外「孩子出生後,安娜忽然就變成成熟的女人(a grown woman),有責任心!」安娜認為安妮塔是上天的禮物,產前憂鬱都一洗而去。
即便母親們再盡心盡力地照顧孩子,她們仍需要家人、親友、丈夫等的支持。嘉妮需要老闆讓她重返職場以維持開銷,又需要褓姆照顧小孩來換取休息時間。安娜雖然有褓姆,但她失望於自己最需要母親的時候,母親卻為了一圓演員夢而到外地演出好幾個月。
過去母親與孩子的關係並不如今天社會要求的緊密,今天各種心理學理論都強調母親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有著無可比擬的重要性,代表她背負無可推卸的「責任」;不過社會家庭組成的變遷,讓女人和家族其他有經驗的媽媽們親戚關係疏遠。
在這樣的條件下擔任「母職」,對任何女性來說都變得困難 [1]。
換言之,當一個全職(甚至是單親)母親在缺乏支持的環境下照顧小孩,心理學家除了關心小孩長大後有怎樣的童年影響之外,我們也應該多關心這群母親生活中的創傷隱憂。
母女創傷的象徵式重返
用精神分析的角度思考這些母親的創傷,即去看她們跟母親(自己作為女兒)的關係是如何影響其母性的表達、母職的品質。那些未被處理或從未揭開的創傷,往往以某種方式回返至自己孩子身上。《平行母親》的發展可謂以象徵的方式表達了這種創傷。
一天晚上,嬰兒安妮塔在睡夢中猝死了。這死亡有文學的象徵意義,對照著安娜出生不久便經歷父母的離婚,當年母親泰瑞莎為了追求演員夢,只好把安娜交給先生照顧十多年,直到這次懷孕安娜才搬回來跟她同住。
因此,當母親在安娜生產後不久便離家工作,在潛意識上就重演了安娜幼年時期被母親拋棄的心碎與憂鬱,在安妮塔身上則以嬰兒猝死症來表達。
我也希望只是危言聳聽,但類似的案例在心理諮商工作裡還真的聽過!女性與母親之間的創傷,會在日後自己懷孕或生產的類似時間、方式、地點、關係模式上,以具有象徵性的方式重現。
猜你想看:「即便成人,都有難以言喻的傷痛」心理師:別輕忽童年創傷陰影

圖片|《平行母親》劇照
現在談談嘉妮,她照顧孩子初期從未思考過孩子像不像自己的問題。直到孩子的爸阿杜羅到訪,指出賽希莉亞跟二人都不像,嘉妮才開始起疑心而做基因檢定,發現自己的確非孩子的生母(抱錯嬰兒,醫院出錯把她的嬰兒跟別人的調包了)。
嘉妮的創傷又是什麼呢?父親在她出生幾個月後便去世,幾乎所有關於父親的記憶都是由外婆講述的:「他有雙杏仁眼」。嘉妮其實完全不知道父親(以及母親)長相是怎樣。
換言之,「妳的鼻子、眼睛、笑容像爸爸或媽媽」相關的家庭互動在她心中是不存在的。如此,她無法擁有一般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母性直覺,及早發現孩子其實跟自己或阿杜羅都毫不相似。
由此可見,除了不可迴避的生物因素之外,「母性/母職」的品質其實亦是社會性的,即深受女性自身作為其母親的女兒的(早期)關係、她和家族各人之間建立的關係感、由這些關係凝聚的心理結構等的歷史所共同形塑。
母性力量的重新起步:看過去,望未來
《平行母親》不只是講兩位女性當母親的故事,它也平行地講述西班牙的《歷史記憶法》背後所掩埋的民族創傷(可類比至台灣的白色恐怖歷史),這部份不是我本篇文章的重點,便只好交給較擅長歷史的影評人再作分析 [2]。
從家族創傷到家庭創傷,這兩條平行線都在回應「人必須向前看,否則只是在挖舊傷口?」這問題。
嘉妮的回應是:歷史的傷口若果不先挖開與認清,前人的遺骸若是未好好安葬、在世之人的心願若然遲遲未了⋯⋯「除非我們完成這些事,否則戰爭永遠不會結束」。唯有直面過去,人才能在真正意義上決定自己的未來。
同場加映:為什麼母愛一定要犧牲奉獻?林靜儀醫師:承認「母職」充滿挫折也沒關係

圖片|《平行母親》劇照
當今天每一位母親都被要求對孩子有更多的母愛與責任,且被過度強調為「絕對」的方向──在某種平行的轉型正義下,我認為「母性/母職」隱含的歷史,即女性成為母親前後所經歷的創傷,也需要先被揭開、談論、安頓。
自我犧牲、完全奉獻的母愛其實不是歷史的必然 [3],在母職之外平行線:「女人」本身、其歷史、社會的形塑等,都需要被更細膩地挖掘,我們才可以在過去的傷口上修補些什麼,再於未來的世界面前,構想母性力量的理想樣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