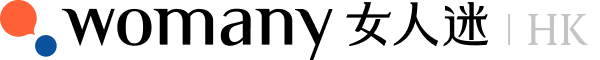女人迷專訪帶你看香港女人形象,她是「左手 Vogue,右手 Foucault」的黃鈺螢 Sonia Wong,同時也是香港女影創辦人、女人節創辦人、大學講師、作家。
文|香港特派 Kayla
「左手 Vogue,右手 Foucault⋯⋯」這是一句寫在黃鈺螢 Sonia Wong 專欄的介紹,也是我對這位女性的第一個印象。第二印象,是同屆畢業禮中碰面,她是那個頭髮極短但眼線極長,唇色豔紅的博士畢業生,看起來氣勢凌厲,與身旁教授和畢業生截然不同的學姊。三步之遙,卻讓我感到望塵莫及。有一天,我們在女人節香港(Women's Festival HK)的工作場合中,正式認識。
年紀輕輕已經身兼博士學位畢業生、香港女影創辦人、女人節創辦人、大學講師、作家等名銜。別人眼中不受常規的惡女,私底下,她形容自己是一個「任性的小孩」。 這個相約在大學的晚上,剛下課的她依然精神滿滿,而學院的氣味卻絲毫沒有嚴肅的味道·,與她的訪談之中,她的幽默和熱情讓空氣變得自由,也令我想起女性主義和理論,是如何在年輕的大學生身上漸漸萌芽,成為大家日後生活的一部分。

女孩子不用只成為「漂亮」
從小到大,我在別人眼中都是一個漂亮的女生,聽得最多的說話就是:「你很漂亮。」
「這其實是異性戀話語系統,或者陽具中心主義對一個女性的認可,告訴你,你最大的資本就是你的美色。」Sonia 在成長過程都被不安全感包圍,一直用一把「漂不漂亮」的標準尺來評價自己、配合別人的期望 —— 不夠瘦、不夠美⋯⋯直到一個地步,她的自我形象開始崩塌,也開始抑鬱和焦慮。

我現在打扮是為了自己,是我所定義的美麗。
「出問題的原因,是那種存在的方式,不是我自己由衷選擇的。」為了脫離別人的凝視(gaze),她改變髮型,例如留長髮的時候,把部分頭髮剷青。維持五年左右的時間,「三尖八角的、五顏六色的、長長短短的都有。」這對她而言是一種解放、一種充權,因為終於,「人們以我想要的方式去凝視我。」化一個與潮流不相關的妝、穿一套不被允許的古怪服裝、不出口成文當淑女⋯⋯ 女生除了「漂漂亮亮」還有很多可能性。
口頭禪為「我對女孩子的要求很高!」的她,「漂亮」絕對不是她欣賞女性的唯一法則,就如她自己亦希望大家口裡那句「你很漂亮」少講為妙,「如果有人讚我做事能幹、很厲害很強,我會很開心。」
推薦閱讀:亞莉安娜的女力宣言:曲線也好,扁平也罷,我們與眾不同

時尚的靈魂,傅柯的思考
「左手 Vogue,右手 Foucault 這句話是形容得我很貼切。」Sonia 笑言自己的打扮的確不像一個教書的人,亦曾經想過修讀時裝科目,「我當時覺得時裝界的人缺乏了某種視角,所以打消了念頭。」她說時裝對於將人們的想法外化、表達出來是很有力的,例如陽剛性曾經被放置在女性身上,推動一個時期的女性思潮,例如 1980 年代流行的 ”Power-dressing”。
她心裡面的 Vogue 靈魂,並沒有因為自己是個「讀書人」而隱藏。後來 Sonia 選擇了哲學科,亦開始了她的學習之路。 現在她是大學講師,專門講性別。 「一開始我對從事學術研究的人都有一種沉悶、跟時代脫節的印象,當我慢慢進入學術圈子後,我自己的定位是一個愛美的、愛穿漂亮衣服的學者。 」
每一次跟她見面,她雙眼上面定必有黑色的貓眼線,看到喜愛的唇膏會心動,會埋怨自己在照片裡臉泛油光和沒有補妝。幾十年前被指虛榮的「愛美的女學者」形象,她都放在自己身上。

有權者究竟是如何根深蒂固地控制一個人,去讓她覺得自己是錯的?
而 Foucault(傅柯)則像是她的大腦。傅柯的「治理術」是文化研究課堂必修的一環,以解構社會權力從何而來為開端。傅柯指出不論是政府機關、教育機構還是醫療系統都由上而下地控制人們的思考,而控制無孔不入,存在於宗教訓條,也存在於我們社會的所謂風俗和道德觀。女性面對性侵時不敢發聲、不同性取向的人需要自我隱藏等等現代情況,都可以見到 Sonia 一度非常著迷的議題的體現—— 反省的文化( Culture of Confession )。
一直以來,性(Sexuality)與別(Gender)對我來說是切身的議題。
「我對於權力、基督教思想、反省文化很著迷,這些關乎於控制(Manipulation)。例如,有權者究竟是如何根深蒂固地控制一個人,去讓她覺得自己是錯的?權力者和整個社會如何傳遞一些信仰,去形成個體的行為和經驗? 這些問題,慢慢就演變成我對性(Sexuality)與別(Gender)的關注。」
女影香港 Reel Women HK 的源起
為什麼大部分電影裡面的女人都很快死,或者百無聊賴、等人來救?女人在電影中為什麼都很「廢」?
2013 年,女影香港正式運作,是香港首個女性電影節。向當時的大學僱主提出了「女影」的想法,對方為 Sonia 介紹一個獨立電影的策劃人,再認識了國際電影節的友人,聚在一起,談了一輪,決定發起香港首個女性電影節。
推薦閱讀:專訪女影策展人羅珮嘉:女性是一個開放詮釋的 Hashtag
除了放映由女性執導、剪接或的電影、有女性視角的作品之外,亦會舉辦與電影和社會脈搏相關的座談會。女影的理想,其實是希望電影中有不一樣的女性再現(representation),而女性不再淪為花瓶,而是有講故事的話語權,「女性在社會上遇到的問題、經歷的事情,和男性是不同的。我們希望可以通過作品,來審視現有的女性議題。」
「拍攝非愛情片、非家庭片的女性電影製作人,亦能通過女影接觸更多觀眾,得到更多的支持。」女影讓女性紀錄片工作者或者拍攝嚴肅社會議題如階級、種族的劇情片工作者,也能大放異彩,不用擔心被商業電影世界「靜音」。女性電影提供的,是另一種觀看世界的方法。
「陳小娟那套《淪落人》,還有 2017 年的《不思議女人》等等都很好看。近年,獨立電影人拍攝不同題材的作品亦多了散播的渠道,也多了工作的機會。」我們的社會似乎在改變,在電影工業,我們看到荷里活經過一輪 #metoo 的洗禮後,女性電影人有更多工作的機會,因為社會已經察覺行業被單一性別壟斷的後果。加入女性視角,不單只讓女性受益,其實男性也有展現更多面貌的機會,「黃秋生在《淪落人》中,終於不再演黑社會或警察。」男性在女導演的視角中,原來可以是「雄壯的警察」或「兇狠的黑社會」以外的定型、角色。

性別定型主導媒體,其實代表著我們有很多事情要做
在香港的便利店,當眼位置擺放的除了是報紙、八卦雜誌,還有一些「女性向」的雜誌,內容大多圍繞「時尚」、「吸引異性」、「瘦身」等。而網上的女性向媒體,亦主要由這些元素主導,但有些所鼓吹的審美觀則較傳統雜誌多元,會涉獵「不同體型的自我接受」、「多元性取向」、「性別氣質」,或許反映著女性讀者在「新」與「舊」之間徘徊。
「這不代表讀者很保守,或者抗拒某些思想。既然她們看女性中心的媒體,代表其實她們真的想接受跟自己有關的資訊。關鍵在於有沒有把空隙填充,放置更多元、不一樣的視角進去。」
Sonia 笑言上年舉辦的女人節,「隱藏的目的是讓 Beauty Exchange 和 Baby Kingdom 的女性讀者接觸女性主義,哈哈,上次在電台接受訪問的時候,他們都不讓我這樣講。」以瑜珈工作坊、舞蹈工作坊等活動,吸引不同年齡的女性參與。新舊思想、上一代與下一代,未必對立和水火不容,就如每一個女兒和母親的關係在青春期定必緊張,可是大家都知道,只是造就自己的環境和時代有點不同。
後記:女人,每一個都不一樣
「我會不會因為自己是女人而感到自豪呢?這是一個好問題。」思慮一番,她說:「我很自豪,因為我是我。」在女人節籌備當中的 Sonia,與拍檔們在會議上討論自己是個怎樣的女人,「我們的口號大概是 我是一個__的女性。如果我要填,我會說自己是個 “nasty“ (下流的)、 “sexual” (有性慾的) 和 “loud”(招搖的)女人。」
社會中的女人有不同年齡、性格和體型,世界上的女性有不同膚色、國籍和文化,各面對著不同的挑戰。當我們在談女性主義,其實是在談「看見不只一種的女性」,而且是「讓女性們的不一樣聚集起來,激起浪花」。而女影香港的存在,是因為女性拒絕被歸一,渴望真實而多元的再現。
也許這一秒,這個她在嘗試改寫電影中女性的命運,那個她在身體力行告訴大眾審美觀不只一種,還有無數在傳媒、影視和學術界中努力的她們。「我很幸運,因為身邊的人看見我的熱情,會願意一直協助和支持我走下去。」只要保持熱情,哪怕看起來格格不入和充滿稜角呢?就讓我們都熱情地做一個自己想成為的女人、推動想看見的改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