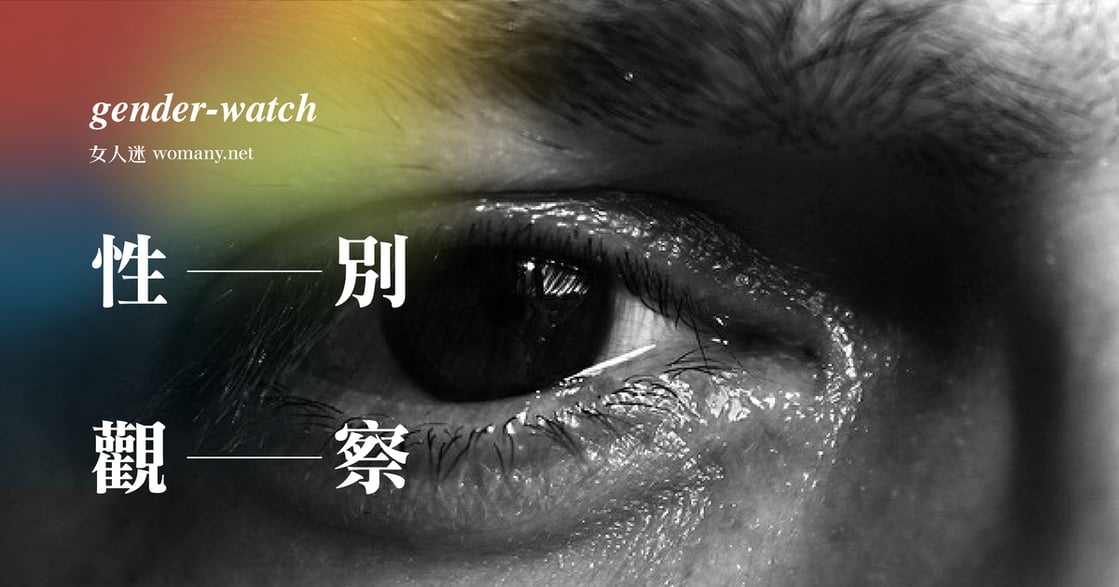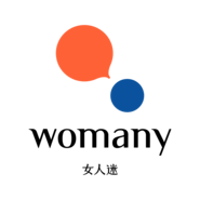三月南投一間少年安置機構因少年得性病爆發出四件性侵案。在台灣,安置機構的性侵案件並不少見,媒體獵奇捕捉,政府推卸責任,一間間孤立無援的安置機構面臨師長不足經費不足無力管教的困境,少年們自力更生出權力階級。
文|Womany Abby
你認為集體性侵案會發生在什麼樣的場所?
實踐陽剛社交禮儀的男子監獄?將女子擄為性奴的 ISIS 戰地?
三月,一名15歲少年被學校老師發現罹患性病,牽涉出南投少年安置機構四件性侵案。事發於二○一四年到二○一五年之間,搜查與詢問確定有四名少年受害,遭性侵次數約十次,案發處多在機構內的寢室或浴室,被害少年被要求進行口交與肛交。據聞,許多離院的少年,可能都遭受過這樣的性侵害。

(圖片來源:來源)
安置機構:沈默的性侵文化
三月傳出新聞,《報導者》進行追蹤調查以《遮掩的傷口:安置機構裡被性侵的少年們》一文列舉受害者困境與體制難處。在台灣關注權勢性侵議題當刻,上下從屬支配、優勢弱勢之關係被大量複製進有團隊生活的領域。從司法體系到安置機構,為何孩子被消音、或是不知何謂錯誤?我們進一步認識安置機構的組織結構。
安置機構由社工、生活輔導員、同儕少年組成,少年安置所的名字又是家園、中途之家。在台灣,安置輔導與安置機構為依《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等相關規定辦理的兒童或少年福利機構。以常理來說一名生活輔導員約要照顧四個孩子,孩子在這裡跟著形形色色的少年一同成家,賦予家庭意涵發展出一套物競天擇的後家庭法則。
在安置機構裡,有觸法少年也有因家庭因素來到這裡的非行少年。來到這裡的小孩都有一個共同特質——家庭功能薄弱。於是他們在這裡發展新的秩序,孩子們在裡頭學習什麼是階級,什麼是權力,運轉出新的小社會。
「講了會更慘」的性侵事實
南投少年安置機構性侵案不是個案,電訪在安置機構 11 年的台東海山扶兒家園主任林劭宇說明:「安置機構發生性侵事件已經不是新聞,這是一直有的社會事件。」
2011 年高雄中途之家性侵案 16 歲的受害者說:「他們將牙膏擠在我的肛門上,用木棍插入性侵我、強迫我自慰,最後恐嚇嗆聲:『你敢講會更慘』。2015 年桃園一間安置機構一名 12 歲男孩被同寢室另兩名男童性侵,但他也對其他人做出類似行為。孩子們噤聲,以性控制儼然成為團體秩序的管教途徑。
林劭宇主任從社工到主管,見證了安置機構十年間的轉變有許多嘆息:「安置機構這個事情不會是偶發,但是多數機構不會承認,因為形象一定會受到影響。」我問主任若是通報性侵事件,機構受影響可能承受什麼後果?
他認為視機構與當地縣市政府的「關係」而定:「有些縣市政府就會給你資源去處理,有些縣市政府會覺得是你管理方面有問題。真正對機構而言最大的顧慮是形象,通報後如果縣市政府不支持,他就會把你貼上一個『管理輔導能力不好的標籤』,定期督導你,檢核你,對一般機構而言就會有很大的壓力。」
中央與地方政府與機構的不健全關係不僅如此。一般觸法孩子透過司法體系來到安置機後,不會接受司法與中央的實質追蹤,司法體制亦不會通知社政單位,得到專業的情感與心理健全資源,孩子在情感的生長上持續受傷或孤單,慣性選擇沈默與複製團體內的行為模式、間接推演安置機構循環性的性侵案件。其中,「授權」給少年利用「權力」維持團提秩序,可以說是霸凌與性侵文化的起點。
延伸閱讀:從《戀我癖》事件看霸凌現況:權力結構下,我們是共犯也是受害者
一個老大的養成:我能代替老師來管教你們
多數來到這裏的少年童年時期可能都沒有得到良好的家庭照護、缺乏對家的情感認同,必須從小團體裡找到歸屬感。
物以類聚的生存法則讓在機構裡屬性相同的人自然集合在一起,在相同勢力的團體裡又有位階,位階高的觸法少年往往要求位階低的觸法少年、非行少年處理生活內務,如洗衣、打掃、洗碗。待過不少安置機構的林劭宇主任說明:
「安置機構裡有大孩子跟小孩子,年紀是一個問題,孩子年紀比較大就會有更多權勢。另一個是資源,儘管來到這裡的小孩都是家境較差的,還是會有相對稍微好一點的,常見的資源譬如說:菸。或是比較會討好老師的人,便宜行事的老師就會授與他權力。」
安置機構禁菸,教養方式不是全控,孩子會去工作與上課,生輔員與社工畢竟不是家長,無法全然介入孩子在學校或是打工地方的行為。在機構內呼風喚雨的少年握有「生輔員沒有加以矯正」的權力,展現在他們生活的細節,例如少年老大規訓孩子們列隊、整理房務,發號司令與控制團隊對生輔員來說也能分擔壓力,自然不插手團體之間的權力關係。

(圖片來源:來源)
一個性侵者的養成:無能為力的老師們
一旦有一個大孩子起頭,這就是一個可以不斷被複製增生的結構網:「假使大孩子看了色情媒材,讓小孩去做口交性交,這個發生一次就有可能是一連串的。」
是誰賦予孩子這樣的權力?機構猶如少年們的再生父母,生輔員有很大的權力去限制少年的自由。不聽話的少年可以留園觀察、限制零用金,逃跑或違規還可能被送進法院裁定、進入感化院。有鑒人力不足,即便生輔員與社工懷抱關懷之心,也可能在日復一日承擔太多孩子教養責任的壓力下殆盡。比起關懷式教養,軍事化的管理系統方便許多。
生輔員與社工人力不足,需要第二層管理去維持團體秩序。「我們第一線的老師,一個人要帶十個孩子,有些老師就會不自覺得授權,他自己叫不動某幾個孩子,他就會叫大的孩子去叫。」林劭宇主任自己深知結構的萬惡,他主動三申五令警戒老師,但仍有老師會便宜行事。
一直以來安置機構不斷發出人力不足的呼聲,我們聯絡長期關注兒少議題的李麗芬立委,她於今年三月亦參與事件的記者會,為少年權益發聲,李麗芬委員認為機構服務品質下降與缺乏人力有關:「安置機構 24 小時 365 天都不休息,生輔員必需輪三班,人力最缺乏。我們要符合勞基法與生輔員規範,普遍不足。」
去性化空間?性控制與性壓抑共生共謀
另外一個必須被正視的議題就是看見孩子有情慾。
青少年正值性探索時期,在密閉而高壓的同儕環境裡,他們如何發洩情慾?多數安置機構如民間普羅教育單位相同,沒有一套鼓勵孩子理解性別認同情慾的方法,在制度與階層嚴謹的秩序下,性亦成為一種權力與施壓手段。
性控制與性壓抑共生共謀,這樣的循環導致了機構內沈默的性犯罪,今年三月的案件並非由機構自主通報,而是學校發現學生異樣並通知警方與社會勞動處介入調查。李麗芬委員說明國內外其實有許多安置機構性侵案件,我們應該擬出機構內部的應對方式,除了通報流程,更該將「性討論」普遍化:
「我們不能把孩子當成無性人、沒有慾望的人。青春期的孩子有衝動是可以被理解的,重點是成人要怎麼跟孩子討論。這部分我覺得在各機構可以更坦承佈公、透明地去談這些事,孩子感覺談性是很羞恥的,也阻止在黑暗隱晦的地方發生我們不希望的事。」

(圖片來源:來源)
李麗芬委員強調機構內要加強輔導員與社工的專業訓練,讓工作人員都有對性別的敏感度去覺察孩子間權力不平等的關係。事實上,這十年間台灣社福體制在漸趨成熟的路上,很多安置機構的法規都在這十年中修訂,安置機構發生性別議題,性侵或猥褻都要做法規的責任通報,沒有通報會有法律責任,從《關懷e一起來》做線上通報,另外做初步隔離,主管機關會做事實的釐清跟確認。
法規也強制納入安置機構評鑑規則,林劭宇主任表示:「這兩年評鑑會更強制我們對孩子要有性別平等的教育。課程內容我們自己安排,但是不一定每個機構都有做,要看縣市政府是不是支持機構去做,因為也會需要額外的撥款申請。」不是每個機構都有能力像林劭宇主任有勇氣去與孩子談性,他會與孩子透過生活經驗聊各種性議題:自慰、婚姻平權、性別認同、身體界線。
每個孩子可以談論的範圍有限,可以使用實際聊天或是給予孩子書籍教材、網路資源。這也反映政府在施政上要求機構談性教育,但並沒有一致可以爬梳脈絡,要靠機構內的老師非常主動地去找素材找資源。
社會與政府漠然:用20分資源帶出100分小孩?
「孩子在青春期比較苦悶,比較浮躁,沒有事情去做。男生看A片性慾難耐,就很容易發生這件事。」林劭宇主任希望整個社會可以一起正式事實,幫助機構去改變,而非獵奇評斷。多數時候政府知道機構內有性侵案並不會加以協助,只會給機構貼上管教不當的標籤:「社會跟政府都應該知道,孩子在成長階段可能會有這樣的需求,我們要做的是教育。我希望媒體資源可以發聲,大眾不是看八卦與譴責,了解結構性問題、安置機構人力狀況需求,現在整個公部門對這一塊的補助杯水車薪,這就像給我們二十分的資源,要做一百分的事。」
機構人員在惡劣的勞動條件下,必須犧牲更多自己的休息時間去照料孩子。另外是政府委託機構費用一個月每個孩子約是一萬八到兩萬,只運算了孩子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但是機構有不同問題的小孩,李麗芬委員說明自己在南投少年安置機構性侵案的公聽會上眾人討論:
「應該針對安置孩子的困難度去做分級,如果照顧某類型孩子狀況比要複雜,需要更多輔導人力或社工,我們可以在安置費用提高,一個困難型服務的個案應該要提高委託費。一萬八的價格沒有計算到安置機構或硬體的費用。所以多數機構又要對外募款。」
大眾「看起來」對事件很關注氣憤,但事實上,無法協助機構改善狀況的批判在他們眼裡更像漠然。
林劭宇主任該事件機構發聲:「我覺得不需要把他們批評的體無完膚,我在這個領域很久,我知道那有多辛苦。」這間已經歇業的南投少年安置機構過度超收小孩,但他們也是全台灣唯一不挑案,願意接受司法保護官送來的任何觸法少年的機構。正是因為每個機構都不希望自己照顧「麻煩小孩」,所以該歇業機構幾乎群聚了台灣最不好帶的問題少年。
推薦閱讀:在《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後,正視性侵,你需要知道的十件事

(圖片來源:來源)
犯錯的人不值得被愛嗎?一個加害者的淪陷
離開原機構的加害者與受害者,走上不同的復原之路。法規明定,有性犯罪的孩子要強制接受加害人心理諮商。然而這樣的孩子要接受更多的其實是情感關懷。原先來到機構的孩子就是生命有創傷的孩子,可能來自失和的家庭、或是帶著犯罪的陰影。許多人聽聞南投性侵案,謾罵犯下性侵案件的小孩,這群孩子一直處於社會遺棄的邊緣,更多人搖搖頭說這樣的小孩沒救了,李麗芬委員期待的卻是:「我們要看見孩子來到機構是需要協助的,而不只是覺得他必須對他的行為付出代價,不要讓孩子又帶著傷出去。」
在香港的某間安置機構曾經傳出被蒙蔽許久的性侵案件,一名觸法少年在機構裡遭受性侵,知情的成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樣的潛意識可能是很多人對犯罪小孩的眼光,進一步思考:
我們會不會覺得有做錯事的孩子,受了懲罰是可以的?站在兒少權益的立場,團體堅持不管孩子有沒有犯錯,都不該受到暴力。
無論是第一線的服務人員,或是遠觀事件的我們,都希望讓更多孩子成為一個有能力自力更生且被社會接受的成人,不是嗎?
南投性侵案件事發機構歇業後,孩子們被送往全台灣不同的安置中心,他們必須為小孩盡最後一份責任。其中有兩個孩子,來到了林劭宇主任這邊,他亦猶豫許久,害怕自己要承擔小孩變壞的風險:
「我以前在當社工時一定會覺得要落實社工精神不能挑案,現在當主管必須想很多,我要擔心性侵加害者會不會影響到我們的孩子,也要花更多時間去跟老師溝通。當然也擔心「那邊的孩子」會不會帶壞我們家的孩子,我必須要說,心裡會有天人交戰,不會像以前這麼熱血,孩子出狀況就是我要承擔。但最後掙扎很久,我還是選擇收了。」
我問為什麼呢?電訪中他愣了下:「哪有為什麼,他們就是需要幫忙。這些孩子沒來,就沒地方去。」真的沒地方去會到哪裡?主任說,孩子就會到感化院,即是少年監獄。
少年監獄,剃頭,手銬腳鐐,禁閉室,高聳的水泥牆,一個 15 歲少年的青春。

(圖片來源: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