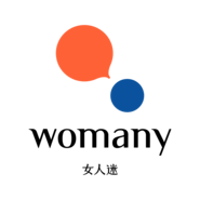專訪蘇品文,她舉辦給女性的性自主工作坊、裸體實踐工作坊。讓我們和女性主義藝術工作者,一起聊性別與身體吧!
文|Womany Irene Lei
微雨午後,我與蘇品文相約在大稻埕的思劇場。它位於三樓,天花板挑高而不顯壓迫,小小的魔幻空間,不卑不亢,在城市裡長出自己的模樣,有一整櫃的書牆、旋轉樓梯和閣樓廊道。
獨立藝術家、舞蹈、自由意志、三十七歲單身、女人、嚴格素食、熱愛騎擋車、超驗主義者、Skoliosexual(超性戀)⋯⋯這些都是蘇品文貼給自己的標籤,她說標籤愈多,就愈不容易定義她是誰。
超性戀
Skoliosexual
這類型的人會被非二元性別所能分類或定義的人所吸引,是一個具包容性的詞。
不被什麼也不為什麼定義,這樣挺好。到這之前,我想像過一個女性主義藝術工作者,會是什麼模樣?但或許在這樣試圖勾勒裡,已犯下刻板的謬誤。

《少女須知》劇照|攝影:羅慕昕
蘇品文走來。她留著一頭白金色長髮,身著黑色外套,脂粉未施,熱情地和我打了招呼。
「好冷喔,你會不會冷?」蘇品文偎緊外套,將身體縮在一起,然後坐下。2018 到 2020 接連三年,蘇品文有過《少女須知》演出、舉辦女性性自主工作坊,她自認是實踐型的女性主義者,床頭擺著的書,全是女性主義或酷兒理論相關,再練習把這些東西帶入生活、帶進社會。「理論要上身」,訪談過程中,我一直想到這句話。
害羞卻真實!裸體實踐工作坊
2018 年,蘇品文從國外回臺灣,開始做裸體相關的藝術實踐,她稱之為蘇品文女性主義三年計畫。「那時候,我覺得,哇,這個東西如果真的要做出些什麼 ,差不多要三年。」她的聲音很輕很細,但很堅定,「我是一個執行力滿好的人,我沒有很多機會,我只能往上或往前。」很多事情,得先過自己那關,自我滿足了,才有力氣持續去闖。
蘇品文說,畢竟從事 nudity (裸露)形式,無論你在什麼位置,一直都不太容易,「我會為自己打分數,而且比外面任何人都還更嚴格。」
2019 年,蘇品文舉行「殺龍 Female Only Salon 女性性自主工作坊」。整個活動分成五週進行,最後一堂課邀請所有參與者進行一場裸體早茶時光。並不是大家都做到狹義上的全裸,畢竟人們尺度有別,但參與者的狀態都很一致地自在。
「作為工作坊 leader ,我覺得滿有趣的是,他們並不用到全裸,就已經覺得自己很挑戰。」蘇品文回憶起那個場面,「餘光瞄到有些女性試著把內褲脫掉,但過了一下就穿起來。我覺得很棒,我都沒有管他們,讓他們自己回到自己去實踐。」

《少女須知》劇照|攝影:羅慕昕
2020 年末,蘇品文將在思劇場舉辦「殺龍 salon -當代表演工作坊/裸體實踐工作坊」。放下艱深抽象的學術談論,轉而直接去感受、去察覺,那些實際作用在身上的觸覺經驗。
蘇品文是舞蹈背景出身,回想觀看舞蹈表演的經驗,其實很視覺取向,「當我們人類有五種感官能力,卻只強化一種的時候,就會帶領藝術往那個方向一直去。」這想法,可說是促成 2020 「裸體實踐工作坊」誕生的原因之一。
「我發現我跟我身體的狀況愈來愈好了,我覺得我好像可以來『分享』這些,不是『教學』。」女性主義今年在劇場界變得很紅,她覺得氛圍有了,想做更不一樣的東西,「我們更缺少的是身體的實踐課。」
其實早在 2013 年,蘇品文就開始做觸覺練習,也在嘗試將之衍伸到藝術治療的層面。「所有向我提出想要做 touch treatment 的人都是女性,因為她們過往有太多不愉快的觸覺經驗。」這些參與者,大多花很長的時間考慮後,才來連繫蘇品文,「我可以感覺得出來,她們把這些事看得很嚴肅。」
這類藝術治療目前還是小眾,有人信也有人不信。「只能實體做練習。」蘇品文聳聳肩,信不信由人嘛,「有些東西必須靠身體去做,每個人的能量展現也非常不一樣。」

2018 殺龍工作坊|攝影:Thinkers' Studio
性別是公共議題,身體也是
我遇過的女生,大多曾經或正在不喜歡、不滿意自己的身體。
「討厭過自己的身體嗎,坦白說沒有。」蘇品文分享很久以前一次莫名其妙的經驗。她常有白頭髮,有次表哥在跟她說話時,突然冒出一句:「品文,你頭髮要不要染黑?這樣我沒辦法跟你說話。」意思是,那些混亂的白頭髮讓他無法專心。
「我第一次意識到『原來我的身體有這麼討厭啊!』」蘇品文重演一次當時神情,活靈活現,「比起被冒犯,我更覺得很 surprising 。」
那股驚訝,來自於外人對自己身體的規訓,竟然可以如此理直氣壯。這故事聽來荒謬,但好像有點既視感,我們在成長過程多少也會遇到那些不知該不該說是關心的勸告。
「我一直不覺得別人可以這麼輕易冒犯我,因為我沒有在服務誰。雖然我喜歡服務也喜歡跟人的連結,但我不是把自己當成被動的服務者。我被冒犯之後,我會冒犯回去喔!」蘇品文笑著說。
相信你的身體,關於對與錯,它的直覺反應更勝大腦。
「我的身體,很需要、很需要速度感。」例如騎檔車的時候,換檔的聲音。我懂那是對精神自由的追求,一旦心靈放鬆,身體才有力量。
不只自己騎擋車,其他交通工具也是一樣。通勤時刻對許多人來說無聊難耐,但卻是蘇品文最愉快的自處時刻,她總藉坐飛機或搭客運的空檔閱讀紙本,「身體和自己的連結,是很自由的。」
我問是不是因為獨處的緣故,她點點頭。
創作者不只要敘述一件事,而要創造一件事。當你成為一個不停產製輸出的人,學習反而成了放鬆的事。藝術家是個人也是主體,但常掙扎著尋找與社會的連結。每次吞吐吸納,都是對世界的提問。觀眾看見的短瞬幾秒,或許是創作者幾月幾年的醞釀。
「一直都很痛苦,最痛苦的就是⋯⋯」蘇品文停頓幾秒,「謝天謝地,我沒有製作人,我很感謝為自己保留很全然的自由空間。」她沒將那個痛苦講明,但我想那個痛苦是,無法在自己舒適的時候,用自己想要的方法,做自己想要的事。
蘇品文談到,自己是 radical (基進)的女性主義者。我好奇,她怎麼在身體的藝術治療裡,探問性別課題?
基進女性主義
Radical Feminism
女人所受的壓迫是最根本、最深刻的剝削形式,且是一切壓迫的基礎。歷史上所有的權力結構都是由男性支配,以暴力為後盾,雖然男性間也有權益差異,少數男人統治其他男人,但所有男性皆受惠於男性至上和女性受剝削的果食。由於婦女受壓迫是其他種族、經濟、政治等壓迫的根源,必須加以根除,否則它將繼續生長出各種壓迫的枝枒。消弭婦女所受之壓迫,將創造一個新形式的革命性變化,其規模遠勝先前所知任何變革。
「哇,這個很複雜。作為一個女性主義者,不可能只是『我想要怎麼樣』或『他想要怎麼樣』。」她說那是演練——演練一個平權關係。「平權不是沒有彈性,一來一往的覺察,並調度出合理範圍,彼此都可以 floating 的狀態,平權不是一個點或一個線,平權本身就是流動的。」
「我在工作過程中,超級 outsider 。」儘管蘇品文很容易被引導進入共感狀態,但大致上還是一個觀察者,「透過皮膚摸著,我要去讀在對方身上,前進多少或沒有前進,確認現在到哪、接下來可以到哪。」

《少女須知》劇照|攝影:羅慕昕
接著她說,身體常被避而不談。
身體最自在的時候,可能是在浴室洗澡的那十幾分鐘,「但我們忽略一件事,就是我們 sharing a space (共享一個空間),我們跟太多人有物理上的接觸。」蘇品文一直想著,要把身體當作公共議題去解。
蘇品文分享她在捷運上遭到性騷擾的經驗。她很氣自己,儘管她已經當面教訓那個人。「最荒謬的是我沒有去按那個鈴,我氣死了好不好!我應該要讓全世界知道這個人正在性騷擾我。」說起這件事,蘇品文仍然忿忿不平,明明比一般人更具性別敏感度,但當遇到性騷擾時,還是無法百分百反應,「我這樣處理,我多差勁啊!」
我們在成長過程裡的性別探索,是讓自己回頭看看,對照過去走的路、跌的步,映照未來可能的形狀。
性別和身體的關係,不只有生理上的區分,還有那些我們該理解卻不明說的課題,那是個人的也是群體的——你認識自己的性別和身體嗎?你怎麼看待別人的性別和身體?別人又是怎麼看待你?
給你的身體課:探索,然後留點呼吸
她提到對今日性別運動的想法。坊間常說要愛自己,但什麼是愛自己,如何愛呢,「愛自己是基本盤,但下一步要去哪?」蘇品文拉緊外套,「你也要懂得愛別人吧,你要提供別人舒服、可以自愛的空間,我們要學那個。」
進行性別討論時,要有多元視角。蘇品文為自己貼的標籤裡,其中有個是 Skoliosexual (超性戀),「我特別被 inbetween 的人吸引,他不太確定自己認同在哪。」
「我完全可以接受一個人的性向是變來變去的,所以對我來說,跟雙性戀的人在一起根本超自然,看著我的雙性戀夥伴個人在轉變的時候會覺得安心。」這個感悟,也體現在蘇品文面對其他事情的方式,「我對於已經被決定好的東西都覺得父權,我會刻意不把東西做完美。」
當一個東西完美的時候,好像就不需要被討論了;但當一個東西不太確定的時候,還能發揮的潛力似乎就很大。
這件事和身體經驗很像。當你不再預期你的身體該怎樣的時候,它就有了空間去呼吸。
「我真的很偏人文,提供的方式和空間很慢,但是很必要。」蘇品文說,這也是為什麼裸體工作坊需要幾個小時,也需要專業團隊從旁協助,他們不會強制規定參與者該如何如何,而是請大家慢一點,別急別慌,「我們這一代是有能力慢慢來的。」
「性別跟身體,是同件事。」訪問尾聲,蘇品文下了這個註解。「不管我的靈魂是男是女,我就是有陰道嘛!我要學習跟我的身體共處。」

2018 殺龍工作坊|攝影:Thinkers' Studio
想起她為自己貼上的許多標籤,那些字彙反映的還真是,什麼也無法完全定義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