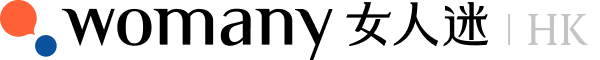在《胭脂扣》後,時隔三十年,關錦鵬導演帶著新戲《八個女人一台戲》來到台灣,「唯有香港,是我閉上眼,也不會迷路的城市」,導演這樣說,這戲,是為香港拍的。
「十二少,3811,老地方等你。如花。」
三零年代的塘西紅牌如花,隔了五十三年重返人世,尋她失約的生前愛人,也昭顯香港今昔的變化。在滄海桑田、世事變遷的香港,如花執著地在報上刊登和情人相認的密碼,「老地方等你」,那一方尋人啟事像封情書,穿越時空,百死不怨。
時隔三十年,關錦鵬導演帶著新戲《八個女人一台戲》來到台灣,「唯有香港,是我閉上眼,也不會迷路的城市」,導演這樣說,這戲,是為香港拍的。

圖片|歐文
新戲,是為了香港大會堂而拍
2005 年《長恨歌》之後,關導多半擔任監製工作,13 年後才選了《八個女人一台戲》重執導演筒。他說,這戲是為了香港大會堂而拍的。
「2015 年的時候為了中環的交通安排,香港政府曾經考慮過拆掉大會堂。當時有很多反對的聲音,因為自從 1962 年大會堂建成以後,它就是香港的、特別我們這代、我的上一代、我的下一代的文化中心。連香港國際電影節都在它的劇場播映。不光是看電影、看話劇、聽音樂會、看展覽,都在大會堂。然後大會堂門口,那時候還沒改建、後來才拆掉那個皇后碼頭,每一任港督到香港、離開香港,都從皇后碼頭,就變成一個儀式。」這樣的情懷保留在電影裡,成為梁詠琪飾演的何玉紋在片末的一段台詞,關導說,那一番話濃縮了香港人一整代的記憶。「所以我就跟編劇說,我們拍拍大會堂吧。」
新戲的發想,除了香港大會堂,還有鄭秀文。「我們很早鎖定鄭秀文來演袁秀靈,因為《長恨歌》帶給她的壓力啊等等,讓她得了抑鬱症。她能走得出來身邊肯定有很多朋友,不管鼓勵她的、勸她的,帶她到教會的,讓她有了宗教信仰。她現在變成另外一個人,在這些層面上她和袁秀靈這個角色蠻契合的。」
《八個女人一台戲》講兩個有宿怨的女明星多年後合作舞台劇,電影從兩人之間的針鋒相對,衍生到周圍被她們影響、也影響她們的其他人。關導曾說過,如果拍的是原創劇本,他通常都從人物開始構想、串起整個故事,《八個女人一台戲》的核心,自然是鄭秀文。但故事發生的所在地,香港大會堂,也是他拍攝這部影片的動力。

圖片|甲上娛樂
「改編劇本它有一定的範疇讓我跟著,比如《胭脂扣》、《紅玫瑰與白玫瑰》到《長恨歌》,都已經有小說的基礎在,但原創劇本我磨得更厲害,譬如說我碰到妳,我聽到妳一些故事,妳啟發了一點點東西,但還是應該有原創的、想像的空間在裡面。」《八個女人一台戲》是個有點例外的電影。因為啟發他的創作意圖的不只人物,還有了大會堂。然而,他仔細想了一想,這種對於場景的關注更早以前就開始。
「比如說《愈快樂愈墮落》,那個時候 1996 年,我搞劇本的時候,香港變成世界的焦點,因為九七就回歸了。當時青馬大橋開通了,但是機場還沒建好。那,我就浮現了青馬大橋的印象,落到最後,電影最後的段落裡面。所以,當然人物是先走的,但有些影像、地方的影像、特別空間的那個感覺,會跟著我的人物走,這個很有趣的。」
地方感在關導的戲裡,總有深刻的意義。1987 年拍《胭脂扣》,他跑遍港澳,好不容易在澳門找到符合三零年代氣韻的古舊樓房,用作戲中最重要場景倚紅樓的拍攝地;1991 年為了拍《阮玲玉》,他身先士卒地費了好大功夫,把整個拍攝場景拉到上海。
「我覺得對我來說,最重要的兩個地方就是香港跟上海。對吧?」關導說到這裡,微微偏頭一笑。上海和香港這兩座城市對於電影的意義,他過去已經談過多次,但這次我們希望他談自己和地方之間的關係。關導慢慢爬梳,從年輕時候的閱讀經驗談起:「我覺得,我對上海的印象很大程度來自張愛玲的文字,我中學時候非常喜歡張愛玲。哪怕在閱讀的當下根本沒去過上海,但後來我印證了,在張愛玲筆下那個有洋味的地方。」
第一次踏上上海的土地,彷彿一腳踏上,張愛玲華美又蕭瑟的文字,梧桐樹、小弄堂,一一從白紙黑字化為真實。那感覺,太美,太震撼。「上海讓我感覺不太像在中國大陸,可能因為上海曾經有過許多租界,不同的文化影響到它的建築、狀態。這跟香港很像,以前是英國殖民地嘛!包括大會堂,整個建築完全是英國風的。到現在,它還是很有氣質,只有十一二層。旁邊都是高樓啦,玻璃帷幕那些。但我覺得氣質還在。」
香港大會堂保留了時代的氣韻,香港這座城市卻不斷的變化中,在變化的同時不斷流失掉某些讓人沈迷的風情和氛圍。如同關導在上海接連拍了《阮玲玉》、《紅玫瑰與白玫瑰》,還有電視劇《畫魂》再到《長恨歌》,上海的故韻也不斷消散。時間的緊張感讓他特別想用鏡頭捕捉一些、重現一些,屬於記憶中的香港。即使許多年輕導演聚焦於現在、現實、當下的題材,但他卻想做特別念舊的那種創作者。
「我覺得有很多眷戀的感覺是逃不掉的,或者我願意,在我的電影裡呈現這個城市曾經的樣子,對那個城市的感覺,我身處這個城市的感覺,對這個城市的一些緬懷。」

圖片|甲上娛樂
港風,就是面向市場、擁抱觀眾
這樣緬懷的情緒,不只創作者有,觀眾也有。我這一代的台灣人大多是看 TVBS 配過音的港劇、看電影台時不時輪播的經典港片長大,而中國的觀眾則時不時在網路上回顧香港電影的盛世。每逢新的香港電影上映,網友總爭相詢問:「這部電影有港味嗎?」我問關導,覺得觀眾心中念念不忘的港風是什麼?
「香港電影優勝在什麼地方,就是它的多元。很多元,不同題材,鬼片、情色電影、喜劇、警匪片、愛情故事,各式各樣。而且還有一點很重要是,類型電影。香港電影最風光的時候,把類型電影推到一個極致。」類型電影在香港電影最繁榮的時候奼紫嫣紅、百花齊放,警匪片、江湖片、三級片、愛情片、武打片,每一種電影都能讓人立刻回想起一種風格、一種畫面的質感、幾個代表性的演員。類型電影關心市場,願意擁抱最最普通的觀眾,像潛藏在一幀幀畫面裡的密碼,觀眾迅速領會、感同身受。這種對市場的敏銳和謙卑,是香港電影與生俱來的基因,也是能打動閱聽人、歷久彌新的關鍵。
「認真製作的香港電影,其實蠻抓眼球的。攝影、美術、聲音、色彩的專業分工,造就了出色的影片。因為我覺得長期以來香港電影的傳統啊,是商業取向,哪怕在八九十年代有些導演像王家衛啊、許鞍華啊、張婉婷啊,羅卓瑤啊,我啊,都拍一些自己喜歡的題材,比較風格化,故事沒那麼商業。但他包裝上很商業啊。」商業化的一個特色是「用大明星」,關導舉了王家衛的《旺角卡門》、《阿飛正傳》、自己的《女人心》、《地下情》到《胭脂扣》,都以大明星作為號召。
「這個概念都是香港電影人很清楚的。電影就是需要明星,除非你的題材明星來反倒不合適,要用素人那是另外一回事。像劉國昌導演《童黨》就是一堆新演員,是不是?陳果導演的《香港製造》也是新演員嘛。但那是基於題材上的考慮。」

圖片|甲上娛樂
有些人看了《八個女人一台戲》,說好像又看到了八九十年代的香港電影。那是來自於一個成熟工業的底蘊和氣勢,有足夠的體量、有充足的預算、有引人矚目的大明星、還有精緻的製作。為了拍出香港大會堂的真實感,劇組甚至複製出 1:1 的前台和後台。「因為《八個女人》有足夠的資源支持,去製作、去包裝,讓觀眾感覺這是一個專業化的作品。」
香港電影面向市場、擁抱觀眾的特質,近幾年也逐漸影響了大陸的投資方和導演,他們逐漸認知到「針對市場需要有類型電影」,技術、人才、題材的開放,讓大陸的類型電影也在慢慢成形。不論烏爾善《畫皮》、文牧野《我不是藥神》或徐崢的電影,大陸的創作者也正在往類型電影、專業分工的路上邁進。關導樂見這樣的發展,「叫香港電影人去拍一個大陸題材,難度很高。而且,也不見得拍出味道。」令人著迷的港風其實源於電影工業的厚實基底,那麼對於關導來說,「香港電影」的核心是什麼?
「我基本上覺得《八個女人》是一個香港電影,哪拍它是合拍的。投資方有意願跟我合作,但我說,我大膽一點,可不可以這個戲讓我在香港拍。他們答應了,所以就拍了。」
成熟的專業分工、面向觀眾的市場考量成就了「港風」電影的盛況,從八九十年代的香港電影裡汲取、生長出的關導,至今仍想反哺。新的電影裡有他對於香港的眷戀和緬懷,在整個工業北上移動的當代,他如同鮭魚洄游,引領觀眾看見他所深深追念的年代和城市。那些時光拋卻了的,他雙手捧住。
他以同樣的柔軟,談女人、談性別、談那些新舊價值的差異和疼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