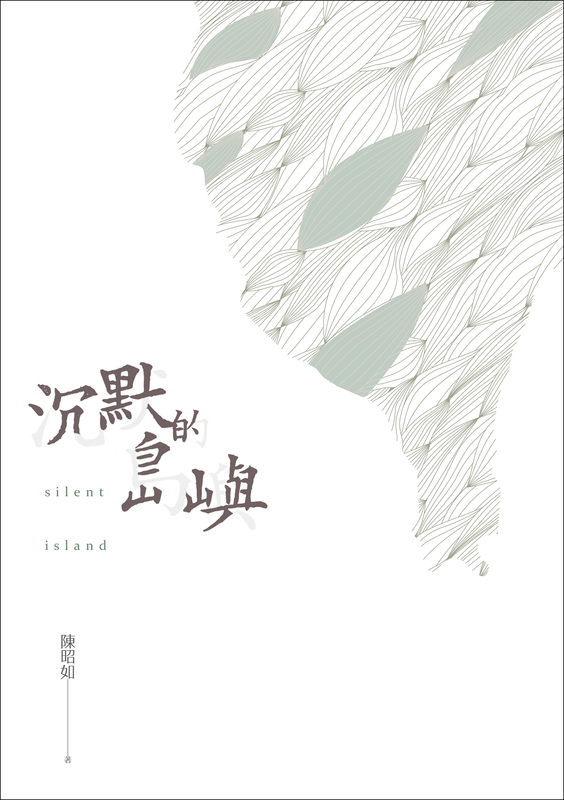除了同學指指點點,老師更私下議論:「男生被親一下,摸一下,會怎麼樣?」「明明看起來好好的,哪裡需要輔導?」「看起來都沒事啊,怎麼可能被性侵?」那樣的冷言冷語,就像利刃一般,刀刀刺在他們的心。當謠言耳語充斥,集體情緒凌駕一切,真相常被每個人的預設立場、刻板印象所遮蔽。

圖片|電影《熔爐》劇照
確定了處理方向與策略,張碧華主動與 H 校長連絡,表示人本願意舉辦全校性說明會,藉機詢找其他可能的受害者,請學校代為發布消息。H校長不怎麼情願,還是答應了。過了一陣子,眼見說明會召開在即,校方遲遲沒有動靜。這下子張碧華可急了,她連忙打電話給H校長卻遍尋不著,改找教務主任亦不見人影,但她的意志根深蔓長,要她放棄,沒那麼容易,最後她找到總務主任,對方卻說,校長沒交代,幫不上忙。
「沒關係,我可以把說明會通知單拿去學校影印,再請你們發給家長。」張碧華客氣說道。
「我們沒辦法幫忙發。」總務主任直接了當地說。
「為什麼?」
「學校沒有那麼多信封。」
這麼爛的理由,虧他也說得出口!她將人本辦公室所有信封找出來,又帶了兩名同事,揹著五百個信封直奔學校。這會兒總務主任又有話說了:「我們沒有人力幫忙裝信。」
她來不及生氣,逕自與同事開始動手,幾個人手忙腳亂地趕在下課前全數裝封完畢,再委由校方發放給各班老師。但仍有老師或許是懷疑,或者是恐懼,未將通知單發出去。
可以想見的,第一場說明會人來得很少,只有三位家長、四位老師,連同靜悄悄坐在其中的以凡、立文及克強爸爸,總共十個人。蕭逸民先從法令角度說明性騷擾、猥褻、性侵害的差異,再由張碧華解釋案情發展,包括謝老師已坦承犯行,正被檢方收押中。
每個人面面相覤。他們說,謝老師不是膽結石開刀才請假嗎?
「謝老師去開刀?是誰說的?」張碧華問道。
「是 H 校長到班上告訴孩子的,」某家長解釋,「她說謝老師生病了,需要靜養,還說同學如果不滿意新的班導,她可以馬上換掉。 」
有老師臉色鐵青地說,謝老師常以「音樂教室需要有人打掃」為由,向她借調男同學去掃地,她感覺孩子不大樂意,總是推推托托,答應了幾次便拒絕了。如今想來,那些孩子可能都是受害者!現場嘩然。
「現在,我們能做什麼?」某家長脫口而出。她的眼淚在眼眶打轉,顯然她不知道情況有這麼嚴重。
「我們懷疑受害的不只是這三個小孩,目前最重要的是讓大家瞭解事實真相,努力尋找其它受害者 」張碧華建議。
說明會結束時已經十點多了。張碧華剛把車停在家門口,便接到H校長的來電,她批評人本的指控不是事實,她一定會控告人本。
「我們沒有洩露個資,也沒有涉及毀謗,你要告什麼?」張碧華冷靜回應。
「案子都還沒三審定讞,你們憑什麼認為謝老師有罪?還曝露受害者的隱私?」H校長怒氣沖沖地說。
「謝老師有沒有罪,這是法院才能決定的事,我們沒有資格說什麼;至於有沒有洩露受害者個資,家長都在現場,他們一清二楚,我問心無愧!」
「我⋯⋯我要告你們!」
「妳來告,我等妳!」
掛上電話,張碧華猛力關上車門,簡直是怒火中燒。但想到年邁的公婆、丈夫及孩子,她不想、更不願把工作的紛擾帶回家。她站在門口讓自己冷靜下來,再次感到自己像是一條寬闊平靜的大河,可以接納人間一切的美與醜,善與惡,才拿出鑰匙,打開家門,以笑臉迎接家人。
接下來兩場說明會,參與人數仍舊不多,但氛圍明顯酣熱起來。教師會理事長率先表示,他問過被找去打掃的孩子,孩子說,謝老師會跟他聊聊童年,談談內心感觸,然後摟他的肩,摸他的身體。音樂老師說,有天警衛提醒她音樂教室窗戶沒關,她匆匆走到音樂教室伸手要關窗,謝老師一個箭步衝出來斥道:「 妳要做什麼?」事後才歉然表示正在輔導學生,不希望被外人打擾。某老師紅著眼說,有學生坦承謝老師喜歡「動手動腳」,問他為什麼不說,學生的反應是:「反正說了,你們也不會相信!」
眾人沉默不語。房間裡安靜下來 ,只剩下高高的窗戶在夜風中輕輕嘎嘎作響的聲音。
說明會進行到尾聲時,H 校長在某民代陪同下也來了,並把蕭逸民拉到一邊,語重心長地說:「年輕人,這種事我們看多了,事情不是這樣處理的......你們這樣做,沒有好處,重要的是要能拿得到錢,不是嗎?」蕭逸民當下沒有反駁,次日向台北辦公室回報此事,人本董事長史英提到友人孩子有過類似遭遇,他代為出面要求學校處置,最後仍不了了之。他鼓勵蕭逸民:「你現在做的事很重要!繼續做下去,我們全力支持! 」
原來深信「謝老師只是摸摸小手」的家長會長也參加了這場說明會。在她聽完張碧華的說明與其它老師的回應之後,態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並發了一封公開信給全校家長:
「⋯⋯我必須以沈痛的心情讓各位知道,本校謝○○老師因對學生犯下性侵害罪,日前已被檢察官聲請羈押,並提起公訴。身為家長會長,我對於這件事既震驚又遺憾,在深入瞭解案情之後,發現有跡象顯示這可能不是偶發事件。我不禁擔心是否還有其他的孩子受害?而這些孩子說不定還生活在恐懼之中,需要早點得到值得信賴的大人的幫助。
聽到這樣的訊息,您心中必然有焦慮或恐慌,但我要請各位家長先保持鎮定,同時絕對不要急著去盤問小孩,以避免先造成孩子的恐懼及不必要的傷害。
所有的家長都有『知的權利』,當務之急我們一定要先讓大家『瞭解事實的真相』,這也是家長會要緊急召開全校性說明會的原因。相信您我都希望傷害僅止於此,但是唯有瞭解事實的真相,才有助於解除恐懼、彌補傷害,並提供孩子真正安全無虞的校園環境。
我邀請了正在協助受害者的人本教育基金會來幫忙我們,除了將對各位簡述事件經過,幫助您瞭解相關法令外,還會提供大家最謹慎的確定自己小孩是否受害的方法,以及家長們可以付諸什麼樣的行動,要求政府當局給予緊急的協助及資源?請您務必撥冗參加這一場說明會,讓我們團結一起幫助可能受害的孩子。」
這場緊急說明會來了三百人,把偌大的會議廳擠得水洩不通。張碧華不疾不徐地解釋事情經過及校方的消極態度,讓現場驚呼連連。最後眾人決定籌組志工團,協助受害者討回公道,並要求市政府成立跨處室的「危機處理小組」,追蹤歷年來謝老師教過的學生是否受害。
說明會結束,人潮已漸漸散去,除了某位陌生的媽媽。她緩緩走向張碧華,神情嚴肅地說,我可以跟妳談談嗎?
當她們的目光相遇時,張碧華的直覺告訴她,終於,終於,有新的受害者出現了!她深深吸一口氣,領著臉色慘白的媽媽坐下,注意到媽媽臉上的黑眼圈,恐怕已經幾天沒睡好了。媽媽強忍著淚水說,當兒子世明(化名)將公開信交給她時,他驚懼不安的眼神告訴媽媽,他也是受害者!
推薦閱讀:老師說女學生都是自願的!信任、崇拜、權力不對等的校園性侵
世明告訴她說,謝老師好兇啊,光是眼神就嚇死人了,每次想要拒絕,老師便說:「我是在教你性知識 ,你懂不懂?從小我爸也是這樣教我的」,並恐嚇這是兩人的秘密,絕不能說出去,否則他會讓世明一輩子抬不起頭來。
「現在,我終於知道他為什麼洗澡要把門鎖起來,又拼命用手去剝指甲剝到流血,排斥我們親他抱他,情緒變得很焦慮⋯⋯」媽媽顫抖著身體說:「去年十月就發生的事,為什麼我們現在才知道?他說,補習班的同學還安慰他說,不只是你啦,像○○○,○○○,都是這樣啊,誰叫你功課又好,體育也棒,謝老師就是喜歡這一型的。」
聽到這裡,張碧華忍不住打了個冷顫。
「小孩子都知道的事,學校怎麼可能不知道?如果學校有好好處理,悲劇就不會一再發生,孩子就不會這麼悲慘了。可是學校到現在還在一手遮天,如果我能早一點知道⋯⋯」媽媽不禁哽咽了起來,「我的心好像淌血,真的好痛!」
家長與人本同仁組成的志工團在校門口發動連署,要求校方解聘謝老師,並請市府出面調查清楚,釐清相關責任。這個始無前例的抗議行動,吸引了大批媒體關注。H 校長在攝影鏡頭注視下,優雅地走向志工媽媽,伸出雙臂擁抱住她,讓志工媽媽她頓時愣住了。H 校長兩度鞠躬道歉表示校方沒有立刻通報是為了保護孩子,此時此刻最重要的是大家必須共體時艱,不要造成孩子二度傷害!說罷轉身走回學校。她一離開現場,那位被她抱住的志工媽媽立刻要求記者:「我剛才並不想被抱,是她硬要抱的,請你們把這段畫面刪掉!」
連署活動的熱絡回響以及媒體的大幅報導,讓學校電話幾乎被打爆,只是這樣單純的呼籲與訴求,並未得到市府回應。人本與市議員張廖萬堅召開公聽會,邀請副市長、教育處、社會處、教育部性平委員及家長代表出席,希望市政府在一周之內成立危機處理小組,加強校園性侵通報系統,正視連署訴求,但市府只同意組成醫療團隊為當事人進行輔導,記 H 校長一支申誡。
真相就像一根不起眼的脫線線頭,只要抽起它,源源不斷地拉扯,最後不知會冒出什麼更驚人的事實。連署活動策略的奏效,讓愈來愈多線索湧入人本:
有人說,謝老師擔任指揮的合唱團成員轉學的很多,建議人本追蹤他們下落。
有人說,謝老師經常辱罵合唱團的男同學,說他們唱得很爛,再分別將他們帶去地下室。至於謝老師到底做了什麼,兒子說不清楚,他也不敢追問。
有人說,他兒子被謝老師亂摸,並恐嚇如果說出去將對全家不利。事後他們夫妻出面警告謝老師,但沒有追究下去。
有人說,兒子咒罵謝老師是變態,是魔鬼,直到新聞見了報,兒子才說自己被謝老師他拉進廁所,用相機拍他的下體。
張碧華循著線索逐一去電瞭解,多數人不是堅決否認,就是婉拒她的關心。好不容易找到畢業兩年的志成(化名)願意談談,她立刻約志成出來見面。
志成說,謝老師說要教他怎麼清尿垢,要求他脫褲子。他覺得不舒服,說了聲「不要」,轉身就跑。謝老師沒有追上來,也沒再找過他。
「那時候你會不會很緊張?還是很害怕?」張碧華問他。
「還好吧。」
「如果一到十分讓你選,你覺得你的緊張害怕有幾分?」
「嗯⋯⋯五分吧。」
「你有沒有跟其它人說過這件事?」
「一直到最近新聞出來,我才跟○○○(小學同班同學)說。而且我想了一下,覺得這好像不是性教育。」
「如果以後需要你當證人,你願不願意?」
「最好是不要啦,」志成顯得有些猶豫,「其實他對我們蠻好的,上課也蠻認真。」
短短一、兩個月,人本發現至少有十多名受害者,但他們寧可隱身起來,孤獨傷懷。畢竟出面指控可能會洩露個人身份,他們無法承擔這樣的風險。
自從接案以來,人本的保密功夫做得極好,孩子的身份都沒有曝光,爸媽也不時提醒孩子,若是有人問起,一律以「沒聽過,不清楚,不知道」回應。只是學校就這麼點大,謝老師教的學生就那幾個班,他們還是被辨識出來了。除了同學指指點點,老師更私下議論:「男生被親一下,摸一下,會怎麼樣?」「明明看起來好好的,哪裡需要輔導?」「看起來都沒事啊,怎麼可能被性侵?」那樣的冷言冷語,就像利刃一般,刀刀刺在他們的心。
推薦閱讀:非典型性侵受害者告白:我最害怕的,是社會說我不夠傷心
當謠言耳語充斥,集體情緒凌駕一切,真相常被每個人的預設立場、刻板印象所遮蔽,被每個人的成見、意氣與憤怒矇住了雙眼。
一群人奮鬥了這麼久,卻好像什麼都無法改變,怎麼辦?
身處紊亂激越的情勢,仍能冷靜分析事理的,大概就屬眾人眼中的「點子王」蕭逸民了。他認為一般對性侵案沒有瞭解的意願,是因「與我無關」,於是一樁樁的悲劇,一次一次的訴求,風一般的吹過了,浮上來又沉下去了。如果要擴大輿論關注,就必須讓人們發現事件與自己切身相關,才能產生同情心或同理心,因此若家長願意現身,讓外界理解他們的處境,便能得到媒體輿論的支持,進而對公部門造成壓力。
這樣的策略真能引起關注嗎?就算引來了關注,又能關注多久?如何避免媒體獵奇與煽情的陷阱?蕭逸民分析事理向來理路清楚,判斷與策略亦精準正確,基於對他及人本的信任,家長一致決定,撂下去,拼了。
透過人本的穿針引線,他們有計畫、密集地在媒體曝光,訴說原本在心頭收得妥妥的心酸。對著陌生人訴說這樣的心情,從來都不容易,但他們還是說出來了:
「我原本擔心兒子要上法庭說明,不敢告,但兒子說一定要告:『打老師也沒用,他對我們做變態的事都沒悔意。他要判無期徒刑,我才不會害怕再看到他。』一月中老師被關後,他才鬆口氣,跑去踢那老師的桌子、吐口水。他主動提要看心理醫師,因為學校調查報告誣衊他是自願,他吃不下、睡不著;校長騙全校說只有摸屁股;有老師說他不想知道這件事、看起訴書很噁,還有人說我們為了錢才鬧大。我兒子很難過:『同學都講很難聽。有些女生不知老師猥褻還為老師哭,我很生氣,要是她們知道老師對我做了什麼,就哭不出來了。』」──克強媽媽 [1]
「我只是一個平凡的上班族,為何放棄平靜的生活,四處陳情投訴呢?⋯⋯事發半年多了,台中市的官員們卻只有一個偉大的發現,那就是校長可能涉嫌延遲通報。我不明白這種五分鐘就可以查出來的事,官員們還可以在市議會及媒體前洋洋得意的發表。以這種處理事情的態度,不知要等到何時,台中市政府才能提出有效的危機處理方案...當我得知一個又一個的受害者陸續被發現,心中的那種痛實在無法形容,對他們的心情更是感同身受。我要告訴這些家長,等事過境遷後,你們一定會認為你們尋求協助的決定是正確的,因為只有正視面對,才能早日走出傷痛。」[2]──以凡爸爸
這樣的心聲有如一塊塊扎實的磚頭,堆疊出令人不忍直視的人生,各界紛紛將矛頭指向學校及市府。與此同時,因出現新的受害者(世明),檢察官決定重啟調查,確認謝老師犯下的不是猥褻,而是性侵,罕見地提出三份追加起訴書(97 年偵字第 11094 號、97 年偵續字第 198 號、97 年偵字第 17215 號),改依「強制性交罪」起訴。
二○○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台中地方法院宣布一審判決,謝老師犯下二十九次強制猥褻、五次口交性侵、七次強制拍下猥褻照片,總計刑期達一百六十三年十個月,應合併執行二十年徒刑。謝老師的委任律師不滿表示:「判太重了,又不是殺人放火!」
無論如何,謝老師的罪證大致抵定。度過這艱難的一戰,大家決定將更多力氣放在對學校的究責。
那是個燠熱的典型夏日,家長們身穿「孩子別怕,我們保護你」的粉紅色上衣,向台中市法院按鈴申告 H 校長及 Y 主任,理由是隱瞞事實,淹滅證據,涉嫌觸犯刑法「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與「隱刑事證據罪」。台中地檢署以「案件通報內容有登載不實之嫌」,依偽造文書罪嫌將 H 校長及 F 主任提起公訴,但最後因「無法可罰」,讓他們逃過一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