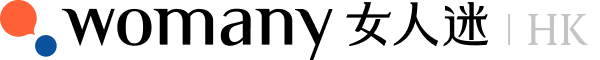《建築城市》聲稱結合多媒體藝術、劇場語言、建築特徵與音樂能量的跨界衝撞,藉此想像香港作為一座獨特城市的未來⋯⋯。
為了觀看「進念.二十面體」(Zuni Icosahedron)今年 1 月於香港文化中心演出的實驗劇作《建築城市》( The Architectural of the City),特地去了香港一趟。雖然過去多少透過不同類型的文本閱讀,擁有粗淺的香港印象,但我從未實際拜訪,對於香港劇場作品的了解更是貧乏。
《建築城市》聲稱結合多媒體藝術、劇場語言、建築特徵與音樂能量的跨界衝撞,藉此想像香港作為一座獨特城市的未來,光主題就非常吸引我。加上它的音樂,來自鋼琴家KJ黃家正與樂團何超與海膽仔( Josie & The Uni Boys)的現場演奏,原本在古典與搖滾山頭各據一方的兩者,會選擇以什麼樣的方式合作,又如何和劇作結合,讓我相當好奇。
沒有休止符的香港初體驗
劇作開演前,我先在香港街頭晃了一天,初次造訪的新鮮感,讓我走到哪裡都睜大眼睛。不,換個說法更為精確:即便只想被動地身置其中,來自四面八方的海量資訊,也會自己攔截經過的人。
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轉速和音量都遠超過台北日常的人為噪音音景。人聲鼎沸裡,夾雜著各處施工的敲擊聲,不間斷的車行低音,和行人過馬路時,伴隨綠燈亮起的急速機械連音,構成了沒有休止符的步行節奏。
不顧先來後到,路牌、廣告傳單、霓虹燈標誌、電子看板,色彩鮮豔的文字,密集來到眼前,它們毫不畏縮,住進尺寸一個比一個大的商業招牌,直接從視野上切割街道的半個天空。
「看我!看我!」這就是香港給我的第一印象:帶著絕對自信的自我張揚,每個人似乎都有話嚷嚷,但看久了也像是無話可說,甚至隱憂著自己不被記得的恐慌。
坐在劇場裡,遙望一座看不見的城市
「建築/變成一些刺激的影像/空間被影像消失了/人們從前/生活在真實的空間」
「我知道了時間永遠向前走/不能回頭」
「那是一個曾經有過如此豐富/街道生活的城市」
作為一個外來的遊客,我穿過 2019 年的彌敦道,走入位於鬧街盡頭的劇場座位,在此上演的劇作,卻企圖帶我重返街頭,只是它遙望的,似乎是一座指向過去的城市───看不見的城市。
那座在香港居民的記憶裡,由熟悉的氣味、聲響與空間構築的城市,如今在哪裡?它真的存在過嗎?
「忘記一座城市/和忘記一個人/有什麼不同」
《建築城市》由何超與海膽仔重新編曲的兩首自創作品〈搏擊會〉( Kickface)、〈何飄移〉(Skitzo)開場,刻意爆頻的音響效果,從一開始就向觀眾丟出感官的震撼彈。在震耳欲聾的背景噪音中,三位演員(張耀仁、吳昆達、曾兆賢)以四種語言(國語、閩南語、粵語、英語)不斷重複朗誦,節錄自義大利建築師 Aldo Rossi 同名理論著作《建築城市》中的台詞。

圖片|攝影 Drill Team 162 Ltd/進念二十面體
同一句話,講一次是真理,講兩次像問句,講三次以上時,詞與詞之間便開始產生空隙,錯落成虛實交疊的夢囈。同樣的形式,展現在影像設計的概念上。數以千計的香港老照片,被懸空投影在大螢幕和演員身上,熱鬧的攤販、新生的社區、門牌尚未生鏽的大樓,以每張不到 1/30 秒的速度,從觀眾眼前重現,又無情地消逝。
如果當代生活已經讓人們習慣,觀看影像,像皮膚揚棄角質那樣地輕易剝落,沒有機會深入血肉,那麼建築呢?必須結合地基、可觸物料與搭蓋技術,一層一層往上堆疊,由此形成真實空間的、堅固的建築呢?
搭建起記憶空間與未來想像的「建築元素」
《建築城市》劇作中,運用了來自香港傳統建築技術的創作符碼「竹棚」(Bamboo Scaffolding),作為和其他藝術語言對話的基礎。竹棚,是全世界僅剩香港仍在使用的臨時搭棚技術,取用竹材的輕盈與便利性,應用於樓宇建設或翻造時,快速建成方便工人輕易在高空穿梭與工作的平台 [1]。
有過香港步行經驗的人,肯定難以忽視竹棚的存在。它們就像某種快速繁衍的寄生植物,以或寬或窄的面積,在城市各端發芽抽長。建築工人在竹棚邊爬上爬下,極有效率地修繕了某些東西後,竹棚立即又蔓延到了其他地區。市場走廊,大廈外觀,巨型建築物的某個死角,昨天的竹棚拆了,今日又增建,而一切都是暫時的。

圖片|攝影 Drill Team 162 Ltd/進念二十面體
在香港,竹棚和人們生活的空間緊密相連,形成一種介於自然與人為之間的奇特景觀,具有獨特的生命力。但在《建築城市》中出現的竹棚,卻異常工整且毫無生機,它離開了高空,沉靜地座落在舞台上,遠看更像孩童兒時攀爬的懷舊遊樂設施。
兩個元素之間的對比和對立——恆常變動的投影影像,與永遠不動的竹棚——像一種反諷的詰問,演員或動或靜,穿梭其中,而音樂是串起兩者最重要的繩索。對我來說,《建築城市》中的音樂與聲響,才是真正搭建起記憶空間與未來想像的「建築元素」。

圖片|攝影 Drill Team 162 Ltd/進念二十面體
音樂,作為一種聲音的建築工法,透過舞曲〈波麗露〉(Boléro)的巧妙貫穿,開啟一個通往他方的虛幻入口。黃家正自由的鋼琴演繹令我驚艷,他的琴聲為這首百年前寫就且結構嚴謹的樂曲,創造了時間的破口。聽覺像一道牆,被音樂刮花,一如他演奏時穿在身上的衣物,刻意毀損、仿舊的布料上,投影著香港的無數可能。
難以言說的缺憾,南柯一夢般的壯志,皆在樂章主題旋律的重覆中,化為從平地不疾不徐升起的大樓,我們想像一座偉大的城市正要誕生。
永遠不變的就是永遠在變的城市
諷刺的是,在〈波麗露〉演奏最澎湃之際,投影影像所對應的思想城市正在崩塌。解構自 Aldo Rossi 理論的語句,斷裂成詞不達意的單字——生活的空間、集體記憶、獨特性、有所選擇的自由——它們分崩離析,終至傾圮。
「一個城市就是一個不停在變化的有機體
城市不停的變化/沒有城市是永遠不變的
永遠不變的就是永遠在變的城市」
劇作中,吸引我目光停留最久的角色,是一位從頭到尾沒有出聲的演員(楊永德)。素白的衣面,嵌著一支忽明忽暗的白色燈管,當他打著太極,緩慢遊蕩過舞台所有角落,沒有人察覺他的存在,彷彿他真的徹底隱形。
他可以是任何事物的象徵。
他是建築?電影?街道?是抽象的城市?還是實際的生活?曾經看似永遠都在的,某幢大廈或電影院的破舊樓梯間,某個轉角總會遇見的茶餐廳的霓虹招牌上,如今是否也有支燈管已半好半壞,像獨居的老人費力呼吸,卻無人覺察。
希望我們不會忘了回家的路
七嘴八舌的人聲、道路噪音、木樁施工的音效,在劇末,隨著何超與海膽仔樂團 [2] 演奏的〈Rule your world〉漸次褪去。何超身上由巨量花材、全球化的消費性商標,與香港傳統文化道具混織密縫的風衣,到此也卸下了一半。她即興起舞,無所拘束,像對香港一無所知的觀光客們盡興喧嘩,又像無視城市的瘋狂演化,一意只想尋回城市初心的搖滾歌手。

圖片|攝影 Drill Team 162 Ltd/進念二十面體
《建築城市》表面上談的是關於城市建築的理性論述,最終渴望表達的,其實是挖掘「家」與「非家」的深層情感——活在真實生活空間裡的人們,才是建築城市的本體。演後訪談時,音樂總監于逸堯一度感慨,香港曾是一個以效率自豪的城市,但如今是否除了效率,什麼都沒有了?如果城市是集體回憶的軌跡,那麼未來的人們,將如何回憶這座城市?在劇烈的改變與不變之中,又有什麼能夠真正被留下來?「很怕有一天,我們會忘了回家的路。」時常在國外奔走演出,偶爾回到香港,總會發現熟悉的地方,一夕之間又改變了許多的何超,也忍不住感性地說。
漫遊香港街頭時,我經常被迎面而來的魔幻感擊中。我記得當我搭乘半山手扶梯,從被橫切過的坡路攀升,和坐在某棟房子的三樓窗口喝咖啡的人近距離對視,並輕易地行經與俯視,城市中鳥類棲息的陽台,我忘了自己身為人類的侷限。
香港也像是一本巨大的詩集,光是路標和建築物的名字,就能為空間帶來無限遐想。深水埗的宇宙大廈隔壁開著動物診所,楓樹街直行過荔枝角道後會遇到詩歌舞街,而詩歌舞街的英文卻叫做無花果街(Sycamore Street)。西方殖民與繁複歷史為此地留下無數珍貴遺產,可惜的是,關於這座城市的深度閱讀,今後顯然必須依靠記憶去補遺,無法再提及某些禁語。
我見過最有生機的竹棚,出現在 2014 年港人爭取真普選的抗爭運動現場(媒體稱之為「雨傘革命Umbrella Revolution」)。參與運動的竹棚師傅,將竹子兩端削尖,在運動現場快速架構成一方與公權力對峙的堡壘。竹棚脫離了日常應用的脈絡,不是為了被搭蓋成戲台而建造,而是為了修繕與捍衛一個具有「家」的意義的城市。

圖片|攝影 Drill Team 162 Ltd/進念二十面體
在不同的時空脈絡中,相異的藝術語言相互碰撞、對話,展現出超乎想像的生命力。這是否足以呼應「進念.二十面體」與導演胡恩威創作《建築城市》的初衷,或者說是願望:最前衛的科技,和最傳統的技藝,可以被放在一起實驗;古典音樂和搖滾電音當然也能夠彼此融合。在舞台上,在香港,誰都可以自在地做自己最想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