補教名師發聲明,表明曾經交往,自己不是狼師。我們想藉此機會,從法律層面談論權勢性侵與慣常的脫罪之詞,也從心理角度談復原之路,所有人都可以做更多,改變談論性侵的方法,打造讓人安心的社會環境。
女作家離開了,留下觸目燒灼的房思琪文本,誘姦事件連日爆開,補教界狼師現形,立法跟進要求補教界實名制,社群網絡的受害者敲下當年無人聞問的事件,被迫沈默已久的聲音,有了發聲口型,性侵的安全防護網仍有許多破洞。
被老師當做洩欲工具的他,決定走法律流程,律師告訴他證據不夠僅算猥褻,社工說他太正常不像受害者,傷害他的人鑽法律漏洞知道自己能安全下莊,長年他精神耗損,法律不是他的救贖,現實讓他很絕望,事件一再重演。(參考:(吉了狼師會怎樣案例分享)
她鼓起勇氣說出自己長年遭補教名師誘姦,邀請其他受害者出面,更多網友的留言語帶嘲弄,唸她母豬,說她得了便宜賣乖,妳不是也有爽到嗎?或是責怪她妨害家庭與通姦,這是不是妳一手策劃的仙人跳?
補教名師近日發出五點聲明,「我是陳國星,不是李國華」,指稱自己不是狼師,表明曾經交往兩個月,那是愛不是性侵,小說中多有時空錯置與幻想手法,自己已經為此身敗名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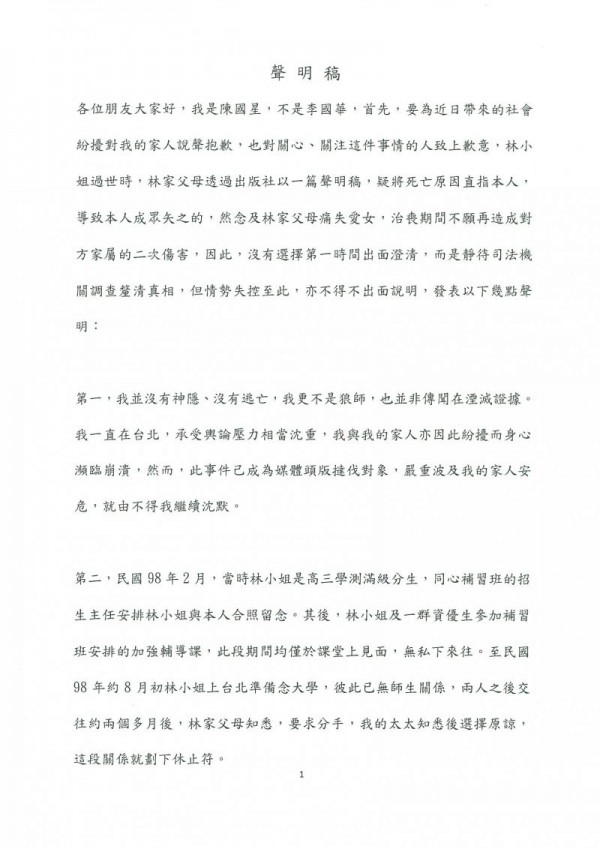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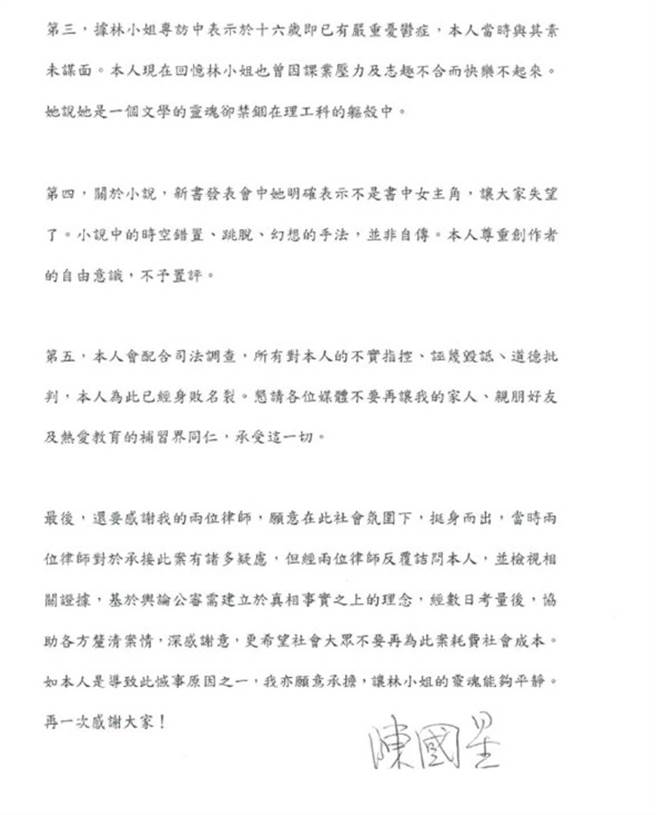
好多人,一路往下掉。房思琪不只一個,事件不只一個,指責受害者的目光不只一個,加害者脫罪的說詞不只一個,家庭與校園缺席的性教育,大人與小孩錯過的性教育,該是時候填補起來。
誘姦與權勢性侵:身體的撕裂與關係的背叛
讓我們從名詞談起,什麼是誘姦?什麼是權勢性侵?
根據刑法妨礙性自主的第 228 條,權勢性侵指的是對於因親屬、監護、教養、教育、訓練、救濟、醫療、公務、業務或其他相類關係,受自己監督、扶助、照護之人,利用權勢或機會為性交者,處六個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加害者和被害者間,存在上下從屬支配、優勢弱勢之關係,權勢性侵是建立在信任、親密、權力關係之下的性侵,讓被害人在壓力下配合或難以說不,權力的暴力,讓他違反自身意願的走入關係。
推薦給你:林穎孟:女人的性,當我沒有說要,就是不要
「這不只是一個『女孩子被誘姦或是被強暴』的故事」,而是「一個『女孩子愛上誘姦犯』的故事。房思琪注定走向毀滅且不可回頭,正是因為她心中充滿了柔情,她有慾望,有愛,甚至到最後她心中還有性。」

權勢性侵的受害者,遭受肉身的侵害,更會感到關係的背叛,信任的毀棄,安全的破壞,因而產生更多咎責或拉扯的矛盾情緒。
我仰慕與信任的老師/教授/家長/上司,他這麼好,為什麼做出讓我痛苦的事?他的手伸入我,我好痛,我不會,我不願意,他一直說愛我,如果我選擇不說不,我選擇也愛他,會不會這是個旁人眼中的浪漫故事?
權勢性侵的受害者也面臨說出口的難,目前人們對性侵的認知很粗淺,談論性侵的方式很粗暴,認識性侵受害者的方式很單一,但權勢性侵的情況很複雜。人們不去看在那樣的權力關係底下,受害者感到的背叛與無助,只一再問他,你怎麼說不,你為什麼不說不?
「蘿莉塔,我生命的光芒、我胯下的烈火,我的罪,我的魂。蘿─莉─塔:舌尖從上顎下滑三步,第三步,在牙齒上輕輕點叩。蘿,莉,塔...在我的懷抱裡,她永遠都是蘿莉塔。」——《蘿莉塔》
「想了這幾天,我想出唯一的解決之道了,我不能只喜歡老師,我要愛上他。妳愛的人要對妳做什麼都可以,不是嗎?思想是一種多麼偉大的東西!我是從前我的贋品。我要愛老師,否則我太痛苦了。」——《房思琪的初戀樂園》
情慾自主與「我們交往過」的詭辯
蘿莉塔不只是文本,而是「文明化」與「合理化」的權勢性侵,老師誘拐女學生,上司密約秘書上床,領頭建立組織內的後宮,奠基於關係之上的誘姦,是陽剛文化裡不成文的默契,以權力狩獵,交換自己性征服的戰績,權力是讓自己發春的春藥,我要你,不管你要與不要。
推薦閱讀:誘姦者的慾望與文明的暴力:千千萬萬個沒有發言權的蘿莉塔
現實生活中有很多房思琪,在不同的結構裡逃。工運界近日爆出集體性侵消息。女子現身說法,桃園市產業總工會秘書長與幹部長年運用權勢性侵,組織默許甚至鼓勵性侵文化。
「他們要逼我說出這一切是我自願的,是我自己喜歡姚光祖、想要和姚光祖上床的、是我搞不清楚自己是情慾流動者還是守貞者所以才會現在跑來控訴說是權力的問題,他們說我所有的問題都是情慾的問題。」
權勢性侵最常出現的抗辯之詞:這是成年人的情慾自主,這是情慾流動。於是沒人問加害者為何要強行壓上來,卻反覆問受害者有沒有拒絕?怎麼拒絕?合意如何判斷?為何你不大力推開?為何你沒有逃開?
責怪受害者的意識形態,與女性受害經驗的「性慾化」,也加深父權社會中,女體被視為慾望、權利、性的客體與受害者的既定形象,反過頭來形塑了支持加害者的系統。
因而,情慾自主與性慾政治的目的,本意在揭示與消減女性作為慾望客體的被動處境,主動追求個人身體與情慾的主體性,爭取性的自主與平等,也是在改變我們談論性侵的態度與方法。
我們要說,「情慾流動」名詞的誤用與詭辯,即是忽視了女性的主體位置與反對聲音,削弱性侵受害者的多元形貌,加強了「沒說不要就是要」的粗暴。
從姚光祖的回應與補教名師的聲明,我們看見另一個慣見的,常被大眾接受與原諒的抗辯之詞,「我確實很喜歡她」、「我們有交往過」、「可能我有做得不好的地方」、「我已經為此付出代價」,彷彿只要有愛,傷害都是合理的;因為曾經交往,所以伸入身體沒有問題;性侵之痛輕易以愛之名脫罪。

這樣的意識形態很恐怖。馬來西亞曾有一起性侵案,最終結案,是因犯案者願意娶受害者為妻;土耳其法案,容許性侵犯透過與受害人結婚來消除犯罪紀錄;黎巴嫩日前女子穿上帶血婚紗,抗議黎巴嫩法條,表明「白色無法掩蓋強姦罪行」。
台灣的距離其實不遠。記得鄧如雯嗎?鄧如雯是九零年代加害者強娶受害者的悲劇。林阿棋曾是鄧母戀人,對鄧母長年施暴與性侵,也仗其權勢,強暴當時僅國三的鄧如雯,迫其懷孕生子。其後,林阿棋以家人要脅,強迫鄧如雯結婚,婚後持續虐待鄧與孩子,甚至性侵鄧妹未遂。暴力是重演的惡夢,鄧如雯難忍困境,殺死林阿棋,僅是為求一夜安眠。
我們對性侵與性傷害的想像如此單薄,以為愛與婚姻可以做為補償,沒想過此舉是對受害者的二度與永久傷害,我們問過他要與不要嗎?愛永遠無法圓融性的暴力,多數時候,這是單方面要脅的性,單方面強迫的愛;而即便在雙方同意的親密關係裡,無論交往或婚姻,也都沒有發生性關係的義務,也都可能有性侵狀況發生。
性侵復原的一條路,我們要做的是什麼
性侵復原是一條漫長的路,需要的不僅是創傷倖存者的努力,更是整個社會風氣的調整。

從我們怎麼談論性侵議題做起,小心名詞誤用,避免以愛為名的脫罪,也不要以正義之名,肉搜補教名師,詳列名單,擠爆名師女兒的留言牆。諸如此類的正義讓許多人狂熱,留下可怖的性恐嚇,其實正是複製了性暴力的惡性循環。
「嬌喘微微,你爸也這樣教你國文嗎?」
「不知道你被綁成螃蟹看起來會怎麼樣?」
「女兒這麼美,老爸為何不欺負女兒就好?」
與怪物戰鬥的人,不要也成了怪物,凝視著深淵之時,深淵也凝視著你。我們真正該做的,是協力建構這條給創傷幸存者的安全環境,讓他感到信任與安全地,踏上復原之路。
性侵的創傷有多巨大?Finkelhor 與 Browne (1986)提出四類心理動力,說明性侵害創傷所遺留的心理影響,可能跟著倖存者一輩子,讓他自此之後畏懼親密關係,討厭性,無法原諒自己。

-
創傷的性化經驗(traumatic sexualization):受害者對性的感受、態度都在發展上以不當、人際失能的情境下形成。這種被當作性對象的物化過程可能使當事人產生混亂、困惑、罪疚及羞恥感。Ochberg 用「負面的親密」(negative intimacy)說明個人界限遭受侵犯後產生自憎,使原來的親密變質,他並指出治療中需要處理負面親密延伸的厭惡、羞恥感。
-
烙印(stigmatization):凡是受害者接收到他們「壞、不潔、丟臉、不清白」的訊息,都會影響他們形成中的自我概念。Sgroi等(1982)提出「壞損物症候群」("damaged goods" syndrome),即指當事人認為身體上的傷害是無可彌補或逆轉的,伴隨著恐懼、沮喪、低自尊、壓抑的憤怒、失去信任的能力、模糊的家庭角色界線、失控、無法自主等反應。
-
背叛(betrayal):受害者發現他們所仰靠的人不可靠,無法保護甚至給他們帶來傷害。失去信任還包括施虐者先脅迫對方保密,然而一旦東窗事發,施虐者通常會否認、說謊抵賴,並反控受虐者,讓對方感受到背叛困惑不解。卻又被成人世界所建構的謊言讓他們覺得不幸是自找的,他們是罪魁禍首,罪有應得,這對爾後他們和異性或權威關係間的信任、他們對自我及世界的看法都有很大的影響。
-
無力感(powerlessness):當個人意願、想法、能力感與身體一再受到壓制、否定與侵犯時,無力感便油然而生,更何況施虐者常利用女性的無助與依賴做為控制手段。
復原之路之所以必須建立,是把關注重心放回性侵倖存者身上,還其主體性,透過打造安全與信任的環境,給予陪伴與訴說的管道,進而重塑社會。
研究兒童性虐待的美國學者茱蒂斯·赫曼(Judith Lewis Herman)於書作中《創傷與復原》提出創傷復原的五步驟,更強調除了創傷個人的循環努力,更需要社會大眾共創協助復原的環境。
「社會的反應對於最後能否解決創傷問題,有強大影響力。彌合受創者與社會的裂縫,首先有賴於社會大眾對於創傷事件的認識與態度。」

-
安:找尋/建立一個安全的環境,滿足你的基本生活需求、也不需感到恐懼和害怕。
-
說:向信任的對象或治療師,訴說自己的創傷故事,嘗試從面對的過程中去哀悼創傷。過程建議有專業的人員陪伴(諮商師或社工),避免不當的同理造成二次傷害。
-
轉:從訴說(或書寫)中轉變自己創傷的回憶,看見自己生命的亮點。
-
建:重新發展對人的信任、建立與人的關係。
-
解:和自己,也和過去的創傷和解,再次找到自己生命中的使命感與意義感。
「受創者在目睹其經驗的人們身上找尋的不是赦免,而是公平、同理以及嘗試了解。」
當然,我們要謹記無罪推定原則,循法律途徑向加害者問責,但更首要的,是全面改變我們談論性侵與創傷事件的方式,讓受害者知道這不是他們的錯;透過學校與家庭教育,重申身體的自主權與積極同意權;教育孩子與大人,親密關係該建立在民主與平等之上,最後,協同社會織起這面接住受害者的防護網。
從陪伴、訴說再到復原的路很長,而我會說,每一個我們,都值得不再與性別/性教育錯身而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