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迷名家施舜翔繼惡女力之後的第二部作品《少女革命:時尚與文化的百年進化史》,爬梳一百年的少女歷史,替始終在場卻無人理睬的少女翻案。理由很簡單,要動手寫一本自己想看的書,而誰是少女?她們是摩登女子 Flapper,她們是野女孩 Garconne, 她們是 It Girl,她們無所不在,她們無所不能,她們就是我們。
很多人問我,為什麼想寫《少女革命》?我每次都說,因為我想寫一本自己也想看的書。
從二○○九年正式接觸女性主義理論開始,我發現自己真正感興趣的,居然不是《陰性迷思》(The Feminine Mystique),不是葛洛莉亞.史坦能(Gloria Steinem),不是那些早就被視為女性主義經典的論述,而是《慾望城市》(Sex and the City)、是《金法尤物》(Legally Blonde)、是瑪丹娜(Madonna)。後來我才知道,原來她們被視為「後女性主義」(postfeminism)的代表,因為情慾的解放與陰性的復興,象徵了九○年代女性主體的重塑與轉向。這個時期的研究,成為我的第一本書,《惡女力》。
當時的我還不知道,原來早在《慾望城市》以前,就有《慾望單身女子》(Sex and the Single Girl);原來《金法尤物》艾兒口中的「柯夢女孩」(Cosmo Girl),出自《柯夢波丹》(Cosmopolitan)傳奇總編輯海倫.葛莉.布朗(Helen Gurley Brown);原來瑪丹娜在自己音樂錄影帶與演唱會中多次引用的畫家藍碧嘉(Tamara de Lempicka),在咆哮的二○年代,也是一個擁有雙性情慾,戲擬陰性特質的摩登女子(flapper)――藍碧嘉簡直就是一百年前的瑪丹娜。
原來在九○年代引發女性主義學界持續至今論戰的「後」女性主義,早在「前」女性主義的時期,就有了自己的祖師奶奶。
原來,這些祖師奶奶們都和她們未來的分身一樣,在過去一百年的歷史中,被排擠在女性主義大論述之外。原來,不管是二○年代的摩登女子,六○年代的柯夢女孩還是九○年代的金法尤物,都有一個共通點――她們都是「少女」。
那一刻,我決定替一百年來不被書寫、不被記憶的少女們,寫下一部少女革命史。―― 《少女革命》是一部以少女出發的百年史,寫的不只是少女的傳奇故事,更嘗試建立少女的另翼史觀。
七○年代的女性主義者說,女人是女人,不是少女。少女幾乎是從一開始便註定被排除在女性主義大論述之外。可是,如果女性主義有三波,那麼,少女革命也該有三波。少女革命的三波逃逸於女性主義的大歷史之外,以身體、以情慾、以陰性,開創一條不同於正統女性主義的革命之路。
二○年代的摩登女子是第一波少女革命。沒有人說得清到底「新女性」(New Woman)指的是街頭上那些爭取投票權(suffrage)的女權份子,還是在舞會中展演性叛逆的摩登女子。如果說,街頭的女權份子是二十世紀初第一波女性主義的縮影,那麼,摩登女子就是溢出了女權框架,以身體與性作為逃逸路線的第一波少女革命。
推薦給你:【女人迷X施舜翔】從摩登女子到賽柏格:性別理論與文化研究的12堂課
一九一三年,美國的「性時刻」(Sex O’Clock in America)敲響,摩登女子穿上短裙,剪著鮑伯頭,在舞會派對中與男人曖昧調情,引領美國少女,掀起二十世紀第一場性革命。女權份子對摩登女子搖頭嘆息,她們畢竟要的是「心」的革命,而非「身」的革命。可是,摩登女子卻擾亂了身心二元對立,就如費茲傑羅(F. Scott Fitzgerald)那本《摩登女子與哲學家》(Flappers and Philosophers)所暗示的,摩登女子既與傳統哲學家相對,又是代表咆哮二○年代的新興哲學家。摩登女子在第一波女性主義之旁,挖掘出一條屬於身體與情慾的女「性」主義革命,預言了往後一百年的少女革命走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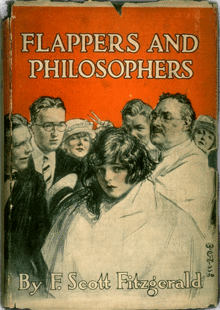
六○年代的單身女孩是第二波少女革命。那時候,第二波女性主義風起雲湧,帶領女人走出家庭,燒掉胸罩。一九六三年,傅里丹(Betty Friedan)以一本《陰性迷思》,化為第二波女性主義教母。可是,早在《陰性迷思》出版的前一年,海倫.葛莉.布朗便以一本《慾望單身女子》,引領女人解放情慾,享受單身,寫下屬於單身女孩的女「性」主義,掀起美國第一波單身女孩革命。
布朗逆轉了單身女孩與已婚婦女的高下位階,使得單身女孩成為六○年代嶄新的時尚代表;她也解構了父權社會的貞潔迷思,使得單身女孩成為六○年代性解放的革命英雄。一時間,單身女孩成為六○年代最鮮明的文化代言人。奧黛麗.赫本(Audrey Hepburn)在《第凡內早餐》(Breakfast at Breakfast)中隨意擺設、恆常流動的房間,成為單身女孩公寓的經典象徵。就連來自「搖擺倫敦」(Swinging London)的時尚情侶檔大衛.貝利(David Bailey)與珍.辛普頓(Jean Shrimpton),都忍不住跑到曼哈頓街頭漫遊,創造出時尚攝影史中最傳奇的單身女孩代表。
推薦閱讀:單身女孩趴趴走:珍辛普頓、單身女孩與六〇年代時尚攝影
延續二○年代摩登女子逃逸於第一波女性主義之外的情慾革命,單身女孩同樣在第二波女性主義之外,以單身身份與情慾解放,挑戰了父權社會的雙重污名,打造出不同於政治權益的少女革命路線。
九○年代的少女力是第三波少女革命。來自西岸華盛頓奧林匹亞的龐克少女,與東岸華盛頓首府的龐克少女互相串聯,共同掀起九○年代流行音樂史中最驚天動地的一場少女運動:咆哮女孩(Riot Grrrls)。那時,她們改寫女孩拼法,重組女孩身份,使得女孩終於成為力量象徵,也創造出九○年代最矛盾的文化關鍵字:「少女力」(girl power)。
一九九六年,英國的辣妹合唱團(Spice Girls)以一曲〈我想要〉(Wannabe)崛起,延續了來自美國的「少女力」革命。辣妹合唱團雖然不是少女力的原始創作者,卻絕對是少女力的流行推廣者。九○年代的少女不只創造出少女力革命,更創造出第三波女性主義。
不同於摩登女子與單身女孩從前兩波女性主義運動中逃逸,少女力本身即是第三波女性主義的一部分。第三波女性主義是反認同,是世代衝突,是革白人母親的命。所以,這同時也是少女挑戰母親的時刻。一九九三年,凱蒂.洛菲(Katie Roiphe)以一本《宿醉之晨》(The Morning After),化為女性主義的頭號公敵,也成為女性主義的壞女兒代表。
延伸閱讀:女性主義壞女兒:凱蒂洛菲的少女世代叛逆
千禧年以後,第三波女性主義的情慾書寫鬆綁了前一波女性主義的禁慾教條。在前兩波女性主義大歷史中銷聲匿跡的摩登女子與單身女孩,原來早在幾十年前就預言了第三波女性主義的誕生。於是九○年代的叛逆少女,在創造出第三波女性主義時,也串聯起一百年來的三波少女革命,寫下了一百年來的女性主義少女史。
――

很多人問我為什麼想寫《少女革命》,也很多人問我怎麼寫出《少女革命》。少女革命不像女性主義大論述,走入學院,成為經典。少女革命散落在一百年的歷史洪流中。所以,《少女革命》是我在這片洪流中,一點一滴打撈起來、一片一片拼湊出來的小歷史。
這段百年史擾亂了女性主義大論述的義正詞嚴,解構了女性主義線性史的理所當然。這部百年史的位置是邊緣,結構是零碎,敘事非線性,史觀非進步,可這正是這部百年史真正顛覆之處。它顛覆的同時是貶抑少女的父權社會,忽略少女的女性主義。
《少女革命》完成之際,我突然想起一件小事。大四時,我修了伍軒宏老師的「文化研究」。我想要在期末報告中分析經典男同志偶像,研究瑪丹娜與女神卡卡(Lady Gaga)之間的關係。瑪丹娜早在九○年代學術圈形成「瑪丹娜學」,資料很好找;可是,女神卡卡才剛崛起,文獻很有限。那時我問伍軒宏,女神卡卡的資料很少,怎麼辦?伍軒宏說,很少,那就自己寫啊。
一直到很後來我才發現,伍軒宏的那句話,成為支撐我往後研究的一股力量。沒有人寫,那就自己寫,親手寫一本自己想看的書。而《少女革命》就是憑著這股理直氣壯所寫出來的女性主義邊緣史、陰性史、少女史。
閱讀少女,成為少女!更多內容,都在施舜翔的《少女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