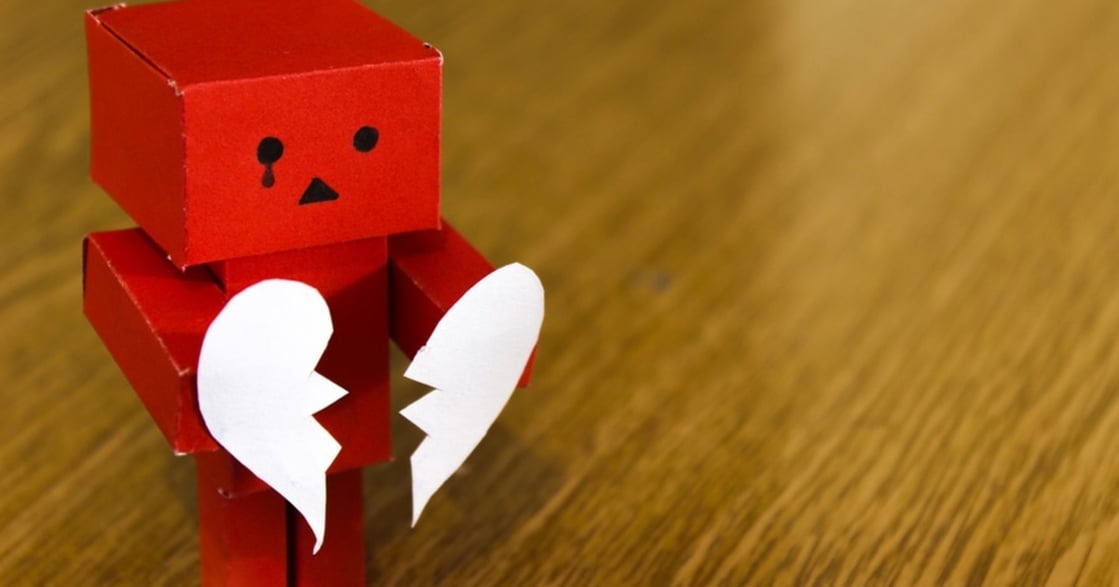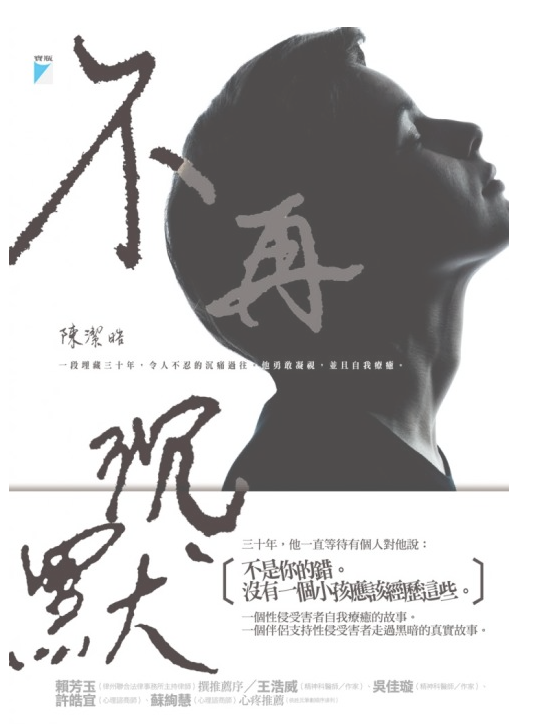《不再沈默》的作者陳潔皓在三歲時被性侵,他的伴侶在他回復的過程當中,陪伴他走過傷痛。這是一條漫長的旅程,三十年來的折磨被釋放後,是心碎,也是堅強。
文/徐思寧
不知不覺,三郎記起兒時被性侵的事情已一年半。在這段時間,他全心全意處理這個深刻的創傷,並把這些經歷寫成了這本書,希望能給予其他倖存者鼓勵和支持。我深深佩服他的勇氣和堅毅,因爲寫下這些回憶,是很痛苦的歷程。
很多朋友親人叫我們要放下不愉快的回憶,往前看,不要被前塵往事所困擾。其實,我們也很想每天快快樂樂生活,忘記悲慘的事情。不過,我很快發現這是不切實際的幻想。不是說我們沒法再享受快樂的日子,而是童年性侵經歷,確實帶來非常長遠且嚴峻的影響,我們不得不花極大力氣,去撫平這個創傷。
三郎忘記了這段回憶三十年。我記得之前因有傭工叫小孩親她下體的新聞,我的朋友擔心聘請傭工照顧小孩是否安全,我跟三郎很深入討論有關幼兒性侵的預防及安全議題。他那時真的一點也記不起來,還很冷靜的給我不少建議。直到一段描述育幼院兒童寂寞與被虐待的文字,才不經意打開這封印三十年的記憶盒子。
剛回復記憶的當下,三郎說不出一個字,整個身體顫抖著,哭了很久很久。後來,他用很小很小的聲音告訴我,他小時候是在奶媽家長大,不是在家裏成長。自那天起,他慢慢跟我述説在奶媽家的寂寞、奶媽一家人的暴力對待、哥哥們的排擠與感情疏離、爸爸媽媽回憶的匱乏……我靜靜聼著,重新理解他的童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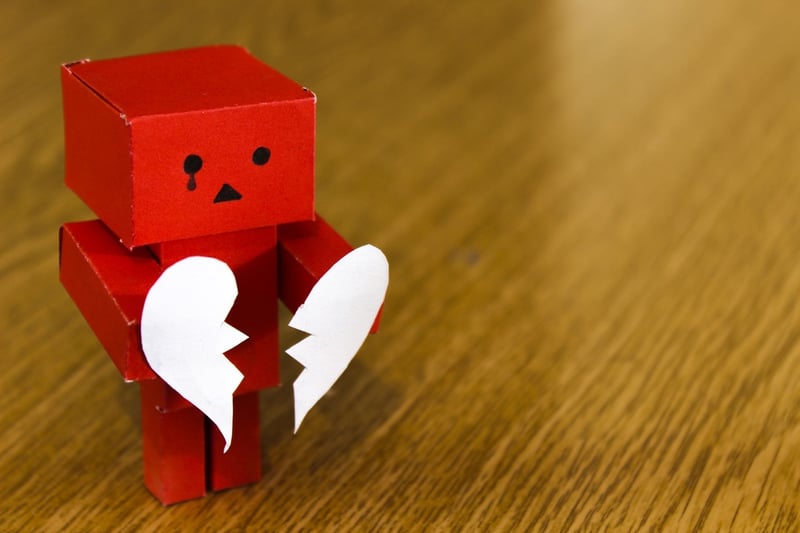
我對於三郎爸爸媽媽把小孩完全交托他人照顧的選擇,感到非常疑惑。我跟他分享我在研究所讀書時,理解到幼兒成長期間跟父母互動的重要,以及我與家人照顧姐姐孩子時的點滴。當時他還沒透露任何性侵的事。現在回想才理解到,三郎當時好像在考驗我是否能成爲可信任的聆聽者。當我接納他兒時無法與父母同住的哀愁與寂寞,他才開始慢慢透露奶媽一家對他不當的身體與性互動。
一切的述説是那麽的謹慎和緩慢。我感覺到他不停觀察我對他的回應,憂慮我對他的看法。隨著三郎確認我對兒童發展與保護的立場,建立對我的信任,他所說事件之嚴重性也越來越超乎我想像。我知道我要保持冷靜和專注,因爲過於害怕、抗拒與淡化的反應,會減低他敍述的意願。
當三郎回憶的片段一個個重現,當時我們實在是不知所措。我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麽辦。我害怕還有其他更恐怖的回憶。我不知道該如何理解這一連串事情。他經歷的事情,可歸類為性侵害嗎?我能肯定成人與兒童進行性交是性侵害,但強迫三歲幼兒觀看成人性交呢?青少年要求幼兒進行口交及撫摸性器官呢?
那時我很想與他人討論和請教,但三郎當時非常恐懼他人對他的想法,我也答應他不告訴其他人,所以我們便開始查閲相關知識,理解如何定義這個經歷。我們在閲讀《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及兒童保護的相關書籍後,便能確定他小時候的照顧者引誘及強迫他從事性活動,是對他的色情剝削(sexual exploitation)及性侵害。當我們能確認面對的困難,給它一個正確名字,這童年創傷便不會被淡化或扭曲,並能開始一步步的療傷。

三郎剛回復記憶的那段時間,他整個人變得很不一樣。他變得非常怕生,不敢獨自一人,也害怕出門。那時,我像在照顧一個三歲的小孩一樣,要隨時把他帶在身邊,或要在他視線範圍内,他才安心。他會不停嚷著要吃冰淇淋,每次他想吃冰淇淋時,還會小心奕奕的問我可不可吃冰淇淋。他會在網路上找回小時候擁有的玩具,透過銀幕觀賞良久。他找回陪伴他成長的卡通,並希望我能一起觀看。他喜歡用被子包著自己,露出一雙眼睛,靜靜坐在家裏的角落。
三郎像一個小孩一樣,在學習表達情緒和需求,重新理解原來哀傷、恐懼、憤怒、快樂、愉悅等情緒,是可被身邊重要的人知道和得到接納。他起初沒辦法流出眼淚。當他想哭時,鼻子只會很酸。後來我發現當我看著他的時候,他便會把眼淚忍下來。觸碰身體也會讓他立即隱藏所有情緒。他開始流淚時也會立即用雙手大力擦乾,不讓他人看見他的眼淚。所以我便嘗試在三郎哀傷想流淚時,不直視他,但依然留在他身旁,而且不分心做別的事情,而他則閉起雙眼,讓眼淚留過面頰,不急著擦掉眼淚。
我知道我不是要替代他媽媽或爸爸的位置,但我得接納伴侶在復原期間的某些時刻,會回到經歷創傷的時間點,像一個三歲的小孩。他依然是我認識和深愛的生命夥伴,我們只是一起安撫童年時受創的小三郎,一起接納他所有情緒,給予他安全感與無限支持。
三郎在復原起初,出現嚴重的睡眠困難。他對睡眠感到焦慮,也擔憂無法入睡。他仿佛回到三歲時在奶媽家時的恐懼,害怕入睡後奶媽奶爸會把他搖醒,強迫他參與他們的性活動。他會不停打電動或看電影,直至自己累倒,不能再睜開眼。一旦入睡,他則不停做噩夢,身體不時不自主抽動及用力磨牙,而且會不願睡醒來,好像怎樣也睡不夠。有時他睡太久了,我叫醒他吃飯或喝水,他便會生悶氣不說話。
後來我們才理解三郎不願醒來,是害怕醒來時奶媽會打他、把他關起來或對他做不好的事,所以他希望能一直睡到爸爸媽媽來帶他走。雖然三郎已離開傷害他的環境三十多年,但身體留下的恐懼依然要一段很長的時間,才能平復。
因爲睡眠的節奏大亂,他吃的餐數變少,很難看到陽光,心情變得更不穩定,而且也越來越瘦。我嘗試了不少改善睡眠的方法,不過沒太大幫助。後來我直接問他需要什麽協助。三郎雖然不是每次都能直接說出自己的需求,但他開始思考和表達自己的需要。他後來希望我能哄他入睡,所以我參照我哄姐姐小孩入睡的經驗,幫他建立一些睡前小儀式,然後為他說床邊故事。我也為他朗讀兒童性侵復原的書籍。雖然有時會朗讀到天亮,但當他開始累積安心入睡的身體感覺,他的睡眠素質就得到明顯改善。

陪伴三郎的這段時間,我不時感到困惑。我擔心自己做錯、怕自己遺漏了什麽、怕自己說錯話。基於我的壓力與難過,三郎後來同意我跟家人述説他曾被性侵的經歷。每當我打電話給身處香港的家人時,他都會靜靜坐身旁聆聽,然後問我他們的反應。他擔心我的家人把他看為怪物和異類,質疑和否定他的回憶以及批判他的人生。幸好我的家人給予我們高度的關懷和支持,沖淡我們很多難以消化的哀傷與難過。我的壓力也因家人的支持得到釋放。
後來,我們開始跟朋友說出三郎小時候的經歷。我們發現每次清楚說出被性侵的經歷,好像有療癒作用。而與其他倖存者的交流,更有難以言喻的支持與安慰作用。他不但更能接納自己的過去,掌握創傷的面貌,也漸漸減弱對自己的羞恥感,並理解原來說出真相,並不會毀滅世界。在過程中,我們也理解朋友家人雖然會嘗試給予我們支持,但有些回應卻讓我們感到更難過和迷茫,所以我們也學會坦誠互動的同時,警覺具有傷害性的回應。
推薦給你:你的痴漢,她的傷害:我們的社會欠性騷擾受害人一個真正的協助
努力了一年半,我知道三郎仍有困難,心靈的傷口依然沒完全癒合。不過三郎現在會笑,會哭,可說出感受,重奪人生掌控權。復原期間的努力與投入,並沒有白費。他每天都比過往好一點點。
無論你曾在童年經歷難過的過去,或你的伴侶、朋友童年曾遭遇性侵或其他不適當對待,希望你們理解復原的路雖然不容易走,但一旦決心走上復原的旅程,事情只會變得更好,而所有努力也是值得的。當找到方向,我們便可探索出路。
*備註:文中的三郎,即為《不再沉默》作者陳潔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