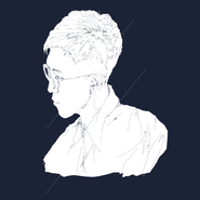從家庭心理學看《返校》,也許,重要的不是想起,而是知道。
環觀一些影評或身邊友人的觀後感,《返校》所得到的評價其實蠻兩極,主要可分為兩點:(1)如果它是一部政治色彩的電影,它有否成功反映白色恐怖時期的樣貌,和對此展現出反思的批判?以及,(2)要是如電影監製李烈說「《返校》注重的是人,所以不應拍得太政治化」,那女主角方芮欣的回憶或贖救之路,有否成功達至結局的「致自由」(個人/政治)?
放心,今天這篇不全是爆雷的影評,我會先從這些疑問去思考家庭無形的影響力,繞道到最後才來回答《返校》的影評為何如此兩極。

圖片|《返校》劇照
「這原來是我的錯!」是的,但這句話不全然對
在心理治療的工作裡頭,常常強調唯有當個案意識到他所抱怨的種種家庭、人際、感情困擾中,其實自己也摻了一腳,甚至是由自己的潛意識挑起,即錯不全然是別人的時候,他就因著「背負起自己的責任」而漸漸走上改變的路途。這的確是一個令心理師和個案都感動的時刻,經典的對白是:
「啊!原來這些事是我所造成的,這原來都是我自己…(怎樣怎樣)…的問題。」
不過在心理學上,我們會發現一些個案其實是過度神經質(excessively nervy)的小孩,他們常常會自惹麻煩,變成別人眼中的討厭鬼,甚至引來別人的霸凌。要是心理上的問題沒有得到處理,他們長大以後,又會常常在關係上受挫,在別人眼中成為任性又自我的攻擊者。事後,他們又總是為此愧疚,無奈於不受控的情緒爆發和自我的惡(badness)。而為了能讓自己感到安心,他們就要有能力在外邊看見自己內心的善(goodness)[1]。
好比一位個案,他很需要在各種志工服務上讓自己看到自己內心的「善」,來對抗他常常在關係中不受控地反應的「惡」。在一段長時間的心理諮商後,他漸漸意識到自己在意著甚麼、因甚麼受挫、內心有甚麼念頭、最後造成怎樣的結果。因此,於是他──就如《返校》的方芮欣──回過頭來承認自己的「惡」和面對自己一手造成的「錯」。
然而,「面對恐懼以後才有自由」的自我救贖之徑,並未順利上路。每次投身於關係之中,不管個案他帶著多大的善意,做出來的、或別人感受到的,常常與自己想像的不同。原因我會說:因為他又把問題全都攬到自己身上!但更準確的說法是,他「記」起來的問題並不是全部,他其實仍被一個無形且不自「知」的、更大的背景深深影響著──所以現在讓我們來問還未問的:這個小孩怎麼會過度神經質?

圖片|《返校》劇照
不是不想記不起來,而是根本記不起來
人不可能獨立於環境而長大的。所以早期環境,即家庭對個人的無形影響力,應該得到更多的重視。我聽過有一位女性,她從小受到父母極高要求的管教,只要無法於 XX 女中拿到第一名都會被慘慘的修理。長大以後,即使受憂鬱困擾的她,也一再希望以工作上的成就來換取父母的認同。但當她的心理師點出:
「其實你是很怕父母不愛你(意指她從來沒有真正感受到父母的愛),某程度而言,你不敢相信你父母小時候對你是很差的。」
她被這句話嚇壞了!一般人認為淺顯易懂的事實,卻是她為了活下來必須防衛的。
這位女性個案從來沒有思考過、也意識不到自己今天的情緒問題,其實跟早期家庭環境有怎樣直接的關連。所以她瞎忙了半輩子,用盡不同方式調解自己生活上的各種問題,認為有好好面對自己的「惡」與「錯」,還是沒有如願。同樣,上文提到的那位男性個案之所以會如此神經質,是因為一連串交織的隔代教養、家暴、父母對他的態度、他對父母的複雜情感所造成的。然而,這些東西已經淡退至能發揮最大潛意識影響力的背景之中,不經過長期的諮商,我們都難以發現並思考這些過去怎樣於今天仍舊無形地作用著。
所以在心理治療的自我救贖之旅中,「記起」那些自己的惡所招致的錯,並不必然能解決問題(當然也是重要的一步),因為常常真正重要的是「記不起來的」、在無形中引領著「錯」的環境影響。
要面對它,不是用「記起」,而是要去「知道」,就是重新建構起來。
可惜的是,不只心理健康程度較差的個案,連一般人也不一定能夠/想要「知道」,因為它就在我們的內在隱身著。

圖片|《返校》劇照
「原來我不被(國)家所愛!」當認盡一切的錯,反而贖錯了罪
繞了一圈回來,是時候回應《返校》的影評為何如此兩極。相信有認真看上文的讀者已經自行猜到,評價兩極的原因就在於:《返校》的確注重人,方芮欣內心的贖罪與自由,卻忽略了這個人的政治環境影響力。
《返校》裡那隻提著燈籠去抓人的怪物(衙差?香港電台的《頭條新聞》就是用衙差來影射香港警察)的臉是一面鏡子,當芮欣選擇去面對自己對他人所造成的傷害時──「我不要忘記,我要記得」──鏡子就破掉了。而且她不跟魏仲廷一起離開翠華中學,要去找自己間接害死的張老師。鏡子所映照的,或那句「你是忘記了,還是害怕想起來?」所指的,始終是在「局外」的芮欣自身的罪惡感而已,若說有甚麼跟「局內」政治有關的,就是她利用了這個國家機器來實踐了自身恨意的遺憾與創傷。
一如有文章一針見血地問道:如果芮欣的舉報沒有導致張老師被國民黨捕殺,她還會內疚嗎?她還會對政權有所不滿嗎?[2] 我相信不會。因此,芮欣的贖罪,只做了一半!她記起來的也只有一半!民主與自由精神只是牽強地跟她扣上半邊。
她雖然記起「都是我的錯」,卻不知道自己的錯的生成背景為何──從家暴的父親和不管孩子的母親環境下長大,到白色恐怖的政權下當一個不唸禁書的乖學生認同,背後都指涉著她不敢思考「原來我不被(國)家所愛!」、甚至一早被它所害、塑造成我今天討厭自己的樣子。
《返校》影評的兩極化,就如同監製李烈希望注重電影中的是人,那些個體的罪與贖,但又希望把民主自由這些政治意識扣上邊。或反過來說,《返校》明明就是一齣政治意味濃厚的電影,不幸是芮欣辛辛苦苦的贖罪,卻又逃避了身上的「政治環境/家內戒嚴」問題──一種整個世代的創傷都以「不該提」的方式傳遞[3],或以精神分析的用詞,這些事情被「內在的監控者:超我」禁止去知道。
有時候,「這不是你的錯~」這種俗辣的心靈雞湯也是有道理的。只是它的表達過於無力,一如還魂的張老師對芮欣說:「害死我們的並不是你」,或人們只會把所有錯都歸到自己頭上。也許,要真正面對這段(國)家的環境創傷,是「害死我們的既是『你』,亦是你還不知道、卻在你內在的那個『非你』」。
「對我感興趣的人,必然有點甚麼瘋狂的東西」:哈理斯的精神分析躺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