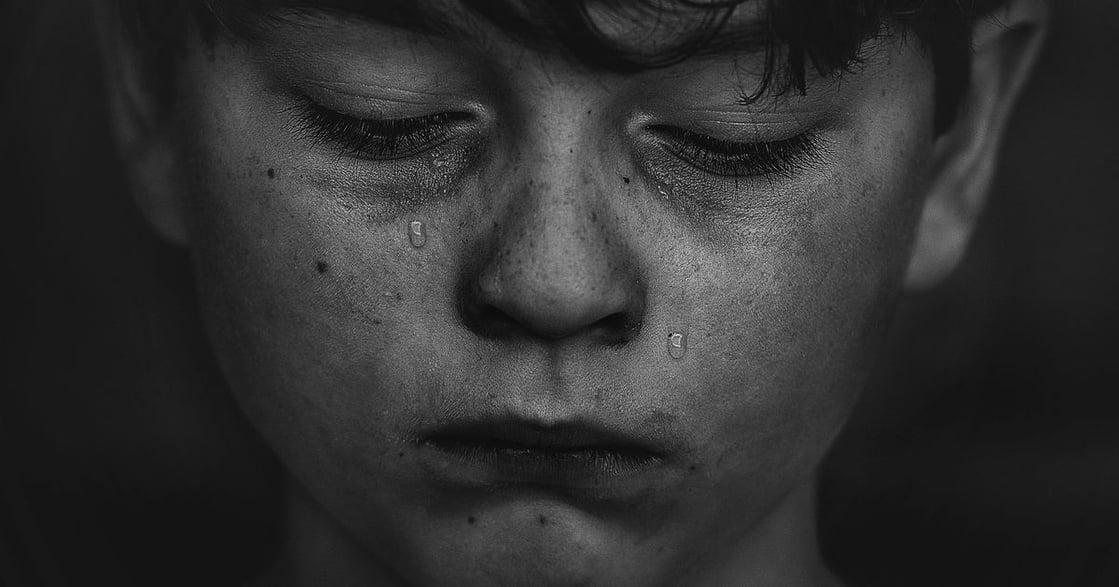根據美國研究,每三個親密關係暴力受害者中,兩個是女性,一個是男性。除了女性困境外,我們同時看見被歧視的男性聲音,以及總被貼上標籤的同性伴侶,他們求助無門,甚至很少求助。我們至少可以做的,是盡自己的努力,營造一種寬容的話語氛圍,允許他們存在。這是我們能夠為他們,同時也為我們自己所做的最少的事情。
11 月 25 日,是聯合國「國際消除對婦女的暴力行為日」。在世界範圍內,暴力侵害婦女的行為已經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
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對親密關係中暴力(備註 1:親密關係暴力是狹義的「家庭暴力」,家庭暴力有時也被用來指代親子之間的暴力,親密關係暴力特指發生在戀愛伴侶之間的暴力)的受害者會存在這樣的刻板印象:無助的、瘦弱的、滿身傷痕的女性是受害的一方,而暴力的施予者則是男性形象。
(備註 2:語言本身具有賦予或削弱力量的色彩,「受害者(victim)」其實是一個削弱力量感的用詞,我們其實並不提倡。我們鼓勵人們更多使用「幸存者(survivor)」稱呼那些經歷了親密關係中的暴力、以及其他困境的人,希望他們能看到自己經歷困境而依然存活的力量。但本文中出於方便大眾理解的目的,還將沿襲中文對於「受害者」一詞的慣常使用。)
但實際上,在異性戀伴侶中,接受暴力的一方並不總是女性,男性也會成為受害者;此外,親密關係暴力不止發生在異性戀伴侶中,它也會在性少數伴侶之間(同性戀、雙性戀、泛性戀等等)發生。
對於遭遇了親密關係暴力的男性和性少數人群來說,求助更加羞於啟齒,援助渠道更加缺乏,能夠受到的社會支持也更少。今天KY的報道關注的就是被我們忽略的那些親密關係中的「特殊受害者」。
我報警後,警察憋著笑問我
「你一個大老爺們,人高馬大的,怎麼可能被老婆打?」
無論是媒體的報道、機構的調查,還是政府和民間機構提供的援助渠道,資源都更多地集中在「親密關係暴力的受害者是女性,施害者是男性」這個設定里。但男性遭遇親密關係暴力其實也並不罕見,我國和歐美國家都有相應的統計數據顯示出這一點。
美國疾控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Prevention, CDC)2010 年發布的數據顯示,美國有 28.5% 的男性曾在親密關係中遭受過強姦、肢體暴力或者盯梢(女性為 35.6%)。另一份根據警察記錄整理的報告則顯示,在英格蘭和威爾士,2014-2015 年,2.8% 的男性(相當於 50 萬人)和 6.5% 的女性(相當於 110 萬)遭受過不同類型的親密關係暴力,這意味著每三個受害者中,兩個是女性,一個是男性。
在中國,社會學教授風笑天(2010)在對第三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數據(N=22025)的研究分析中發現,24.9% 的女性和 22.8% 的男性都曾在婚姻中(至少一次)遭受過不同形式的暴力。

圖片|來源
中國性教育工作者陳潔瑜對男性親密關係暴力受害者早有關注。她告訴 KY,在今年年中她在北京主導的調研中,許多男性訪談者認為男性不會是親密關係暴力的受害者。也沒有人舉出男性作為親密關係暴力受害者的例子,無論是關於自己的還是別人的。
陳潔瑜認為這可能反應了一種認識上的偏差,當然也可能是因為男性在訪談中不願意透露自己的受暴經歷。她說,人們談論親密關係暴力時,往往會有這樣的預設:親密關係暴力主要是肢體暴力或者婚內強姦,而其施暴者是男性,受害者是女性。
延伸閱讀:性別小辭典|親密關係暴力有哪些?
這個預設包含了兩個誤解,a. 第一個誤解是「男性不會是肢體暴力或者關係內強姦的受害者」。在人們的觀念中,女性的身體力量不如男性,在對抗中男性總是會處於優勢,因此,他們不太會「被打」或者「被強姦」。(此處主要闡述異性戀中男性遭受暴力的情況,男性在同性戀關係中遭受暴力的情況將在本文的第二部分中統一闡述。)
但男性被施以肢體暴力的案例並不鮮見。在風笑天的調查中,5.5% 的女性在婚姻中(至少一次)遭受過肢體暴力,而這一比例在男性中為 2.5%。
過去四年裡,心理咨詢師王大為一直為中國白絲帶志願者網路提供服務,這是一家反對性別暴力的公益組織,其特點是呼籲男性加入到反親密關係暴力工作中。王大為介紹說,他接到的男性遭受親密關係暴力的案例中,幾乎全都發生了激烈的肢體暴力,並持續了相當一段時間。
另一個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反親密關係暴力機構援助者表示,女性常使用咬、掐等方式來施加暴力。她援助的一名當事男子,因長期被妻子在身體看不見的部位掐出傷痕,連夏天也不得不穿長袖襯衫來掩飾。
在一些案例中,肢體暴力是相互的。一個 50 多歲的中年人曾向王大為求助,他和妻子婚後居住在妻子的娘家,長期遭到妻子和娘家人的羞辱和恥笑,之後發展為被妻子毆打。後來,他也會動手予以反擊,最後發展成為他和老婆長期的互相毆打。
但當男性遭受暴力的情況出現時,當事人往往得不到相應的支持。四年前,在遭到妻子的又一次毆打後,姚威(化名)鼓足勇氣走進派出所求助,然而警察的一句回應則讓他落荒而逃。
「就感覺他憋著笑,還問我,‘你一個大老爺們,人高馬大的,怎麼可能被老婆打?’ 當時覺得周圍所有人都瞅著我,笑話我。如果地上有一個洞,我立馬就能鑽進去。」 在此以後,姚威沒有對任何人講起自己的遭遇,直到離婚。「難道只有女人才有可能遭到親密關係暴力嗎?」這使得姚威困惑至今。
陳潔瑜說,b. 第二個誤解是「親密關係暴力只有肢體暴力這一種形式」。其實,肢體暴力僅僅是親密關係暴力的一部分,親密關係中的暴力有經濟控制、情緒 / 精神虐待、身體虐待、性虐待、言語虐待五種形式,身體以外類型的受害男性,更加容易被忽視。
在風笑天(2010)的研究中,男性在婚姻中(至少一次)遭受非肢體暴力的比例為 22.7%,遠高於他們遭受肢體暴力的比例(2.5%)。

圖片|來源
但是,當一個男性遭遇非肢體暴力時,人們往往更不容易將他們當做受害者來看待。
在父權社會中,政治、經濟、法律、家庭等領域的權威位置都被默認保留給男性;人們對「男性氣質」存在一定的想像與期待,男性是堅強、剛毅、支配、管理的角色;女性則被認為更感性、脆弱、處於從屬地位。這種思維模式是二分法的、非此即彼的,比如陽剛與陰柔、理性與感性、主體與客體會分別被用來形容男性和女性。
這帶來的影響很多。例如,人們會更多地認為,男性不應該那麼容易受到情感傷害。陳潔瑜告訴 KY,「因為刻板印象的支撐,很多時候,人們談及精神暴力相關問題時,會下意識地認為,感情創傷、情緒問題更容易出現在女性身上,而男性遭受到情感傷害,因為對方的冷暴力而感受到痛苦,則被認為是與‘男性氣質’不符合的表現。」
除此之外,在陳潔瑜看來,人們對性暴力的認知也普遍存在誤區。在一段親密關係中,男性往往被認為是性關係的主動方,但事實上,人們忽視了女性對性的需求也可以主動的,也忽視了男性也會遭到強迫。而一旦男性遭受性侵害後,人們往往也會施以嘲笑而非同情,比如發出「你是男人,明明占便宜了」、「你是不是男人啊」諸如此類的嘲笑。
社會對男性的刻板印象不僅使男性更難得到外界的支持,它也同樣內化於男性的價值觀中,也使得他們成為一個更沉默的群體。在過去四年的時間里,王大為接到過近200名親密關係暴力的當事人求助,但在所有來求助的人中,女性占90%,男性只占10%。
王大為介紹,這些受害者都是在實際生活中遭遇了長期和持續的肢體暴力,實在無法忍受之後,才前往尋求幫助的。
「這個過程中我們不難發現,父權文化不但對女性進行壓迫,同樣給予了男性壓迫。」王大為說。當父權社會的結構實際上將男性禁錮在單一的性別角色中,男性也會在不知不覺中內化這樣的價值,極力去扮演好「合宜」的角色。
由於深受「男性氣質」所困,男性受害者格外羞於尋求幫助。王大為表示,「相比於女性受害者,男性受害者更加孤獨。」女性受害者更有可能跟好朋友哭訴,尋求朋友的支持和幫助,但對於大多數男性來說,他們可以和朋友喝酒聊天,但永遠不會談論這些話題。
即便他們邁出求助的一步,也很難順暢地說出自己的遭遇和痛苦。
美國記者 Philip W. Cook(2009)曾與親密關係中受到暴力的男性進行訪談,他發現,這些受害者往往會以幽默的語氣來描述自己所經歷的痛苦,試圖讓自己和別人感受「這並不是一件太嚴重的事」,這種「幽默」被認為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方式。
這與王大為的工作經歷非常符合。王大為說,這樣的情況在男性受害者中非常普遍,男性受害者們往往並不會將自己的遭遇描述成一件非常嚴重的事情。在過往的援助中,大多數女性受害者們打來電話的第一句話就是「我遭到家暴了」。而男性則大多則先是用隱晦的方式詢問:「如何解決婚姻中的矛盾」,「和老婆有了衝突怎麼辦」。在之後的深入瞭解中,援助者才會發現,他們曾經遭受了不同類型的、嚴重的暴力對待。
「因為畏懼輿論,他們會採用試探的方式來看自己是否會被理解、被支持、被保護,還是會被歧視。」
王大為說,在遭受暴力時,他們往往同時要承受暴力和內心羞恥感的雙重打擊。
一位來自北方的男性受害者,曾在深夜致電王大為尋求幫助,在電話接通後,他欲言又止。這名男子生活在北方農村,經濟條件不好,花費很大代價才娶到老婆。然而,老婆對他日漸不滿,從言語暴力漸漸發展到出軌,甚至帶著情人對他進行了毆打。在與王大為的三次交流中,這名受害者卻認為主要的問題在自己,他不斷重復著這樣自我貶損的話:「是我太無能了,老婆都管不住,被戴綠帽子,被瞧不起⋯⋯」
在進行了一系列訪談後,陳潔瑜提出了疑問:「目前,男性受暴者的報告案例確實比女性少,但我們不知道,這是因為男性受害者更少,還是因為男性受害者更加沉默,或者是因為援助機構對男性受害者的求助不予以重視、乾預不足?」
「打人是不對,但是你也不要搞同性戀了」
當我們和陳潔瑜聊到男性作為受到忽視的受害者群體時,她還提出了人們對親密關係暴力的另一個認識誤區:
親密關係暴力被窄化為僅僅發生在異性戀關係之間,然而,它其實同樣發生在性少數群體的親密關係中。
事實上,在我們採訪的過程中發現,這也是一個相當龐大的群體。2015 年,反家庭暴力立法民間倡導工作組發布的中國首份親密關係暴力的全國網路調查報告《親密關係中的暴力調查報告》顯示,通過對(包括 877 名非異性戀者在內的)3334 名對象的調查,同性戀與雙性戀的親密關係受暴比例分別為「68.3%」與「67.6%」,甚至略高於異性戀群體的「62.7%」(備註 3:此處「受暴」的定義是在過去一年內,至少遭受過一次包括身體、精神、語言、性、或經濟上的暴力)。
美國疾控中心(2010)的一份報告中顯示,一生中至少遭遇過一次(肢體或非肢體、各種不同程度的)親密關係暴力的比例,在同性戀女性中是 44%、在雙性戀女性中是 61%、在異性戀女性中是 35%,而這一比例在男性中,分別為 26%(同性戀),37%(雙性戀)和 29%(異性戀)(備註4:可以看出,在美國,性少數伴侶中親密關係暴力的普遍程度也要高於異性戀伴侶)。

圖片|來源
然而,性少數群體作為一個本身在社會主流話語中本就未被承認的群體,能夠獲得的幫助和支持非常少。
一名來自美國服務性少數群體反暴力機構 The Network/La Red 的工作人員說道,「由於這一群體本身所遭受到的社會歧視與排斥,在他們身上所承受的暴力更難被公眾所看見」。美國疾控中心也在他們 2010 年的報告中承認,「對於發生在性少數群體中的親密關係暴力,我們目前知之甚少。」(轉引自Shwayder, 2013)
國內民間非營利組織、性少數權益機構同語 2009 年發布的《中國女同(雙)性戀者家庭暴力狀態調查報告》指出,遭受暴力的女同(雙)性戀者向「正式支持系統」(備註:「同語」發布的報告里把「正式支持系統」定義為 「社會服務機構與政府單位,如警察、司法、衛生、醫療、教育、就業等公共資源,和半官方性質的婦聯組織」)求助過的不足 1/5。在求助案例中,近 2/3 的人認為求助效果很小或完全沒有效果,甚至在有些案例中,公權力部門在執法過程中對女同性戀進行了進一步歧視,導致受暴性少數女性的求助遭受了極大阻礙。
「站在街頭無處可回,誰會看我一眼?懷著對自己和戀人失望、又被社會拋棄的深深的無助感,這就是我看到的性少數親密關係暴力的受害人。」彩虹暴力終結所的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員告訴我們。
作為國內首家專門面向性少數群體的親密關係暴力求助機構,今年 6 月對外開放後,彩虹暴力終結所已經接到了幾十次親密關係暴力求助,這名工作人員表示,「從肢體衝突到性暴力、經濟控制以及精神暴力都有涉及,從涵蓋的暴力類型來看,性少數群體與異性戀親密關係的暴力沒有大的差別。而最大的不同則在於,性少數群體在遭遇親密關係暴力後,無處依靠,甚至無人知曉。這是別人看不到的受害群體。」
社會公權甚至否認他們的存在。2015 年年底,中國第一部《反家庭暴力法》通過表決,新聞發布會上,發言人郭林茂在回答記者提問時公開表示,「在我國,還不曾發現同性戀之間的暴力事件,因此,新出台的《反家庭暴力法》中共同生活的人員不包括同性戀。」
在彩虹暴力終結所遠程陪護的一個案例中,當地的公安局「一面說打人是不對的,一面告誡受害人,但是你們也別搞同性戀了。」這樣的公共事件與發聲,也讓性少數群體對於社會支持系統有了本能的不信任感。

圖片|來源
珊珊是一位女同性戀,畢業前作為社會學專業的學生,她與婦聯等機構有過一些接觸。畢業後,珊珊與她的女友捲入親密關係暴力中,在她想要向外界求助時,婦聯被她首先排除。「我絕對不會去找婦聯這種機構,他們眼裡的性別角色標簽太重了,很多時候還需要我去給他們做性別意識提升,更別提同性親密關係了,他們沒有這方面的處理經驗,我也不覺得他們可以幫助到我。」
事實上,不僅是向傳統的支持系統求助可能會帶來二次傷害,在馬修眼裡,「就連很多身邊的朋友也會對我們另眼相待」。最初,在遭受男友多次冷暴力後,馬修試圖向朋友尋求幫助,直到有一次他發現,自己覺得「私密和丟人的事」被朋友當作笑話跟別人吐槽,他感到傷心。「無論是 gay 圈的人還是異性戀朋友,大家喜歡把同性戀的事情傳的非常 drama(戲劇化)。他們傾向於把同性親密關係這種身份代入八卦或是不好的東西。」
一邊是社會支持渠道的缺乏,另一邊是群體本身的不信任,暴力中的性少數群體愈發面臨很少求助的境況。
延伸閱讀:打人才叫暴力?性、言語、金錢控制都是暴力
彩虹暴力終結所協調人(coordinator)李悅說,即便「同性戀」、「性少數戀人」這些名詞對大眾來說已經逐漸不再陌生,國內目前仍然沒有一家專門針對性少數群體親密關係暴力的官方援助或培訓機構。政府官方的支持系統對性少數群體的歧視和忽視,與性少數群體對他們的不信任,在無聲地相互影響著。
「出櫃威脅」成為性少數群體忍受親密關係暴力的原因
較之肢體暴力,容易被忽視的精神暴力也更加頻繁地充斥在性少數群體親密關係中,《親密關係中的暴力調查報告》(反家庭暴力立法民間倡導工作組,2015)顯示,在嚴重精神暴力方面,同性戀和雙性戀無論是施加還是遭遇的暴力都顯著高於異性戀者,雙性戀者遭遇嚴重精神暴力的比例(25.7%)甚至高於同性戀者(21.8%)和異性戀者(18.2%)。
報告研究者認為,這是由於性少數群體經歷的心理暴力常常與針對「出櫃」(即暴露同性戀身份)的威脅和恐嚇相關。
在忍受了男友一年多的「冷暴力」之後,男同性戀者燕子終於與男友分隔兩地,燕子鼓起勇氣提出分手,卻遭到了對方的威脅,說要把燕子的個人信息和照片發布到學校的貼吧,「讓大家看看,這個人是個同性戀」。
「我當時非常害怕,只能打電話請求他,從晚上十點一直到凌晨四點」,男友提出了很多過分的要求,最終,因為害怕出櫃,燕子選擇了順從。
女同性戀者珊珊在試圖結束上一段親密關係時,也遇到了「出櫃威脅」,與燕子不同的是,她自己早已對外出櫃,但女友卻把出櫃當成了籌碼,分手時,一直排斥出櫃的女友告訴珊珊:「為了你,我才出櫃了,你不能離開我」。珊珊感到哭笑不得:「出櫃應該是個人的選擇,開心就好。卻因為它可能背負的社會壓力,成了一種威脅的武器。」
回想自己被「出櫃威脅」的經歷,燕子開始反思性少數群體里的暴力,「因為我們是性少數群體,受到暴力的那一方發聲會更加困難,甚至根本不敢發聲,所以,施暴的那一方就會變本加厲。」
「出櫃威脅常常會將暴力升級,因為害怕被出櫃,暴力受害人往往會選擇忍受暴力,同時更難向外求助。往往在這個封閉的過程中,暴力開始急劇惡化。」李悅告訴我們,「出櫃威脅,對遭受親密關係暴力的受害者來說,幾乎是個兩難的絕望境地,而這樣的兩難不僅是暴力發起人造成的,更是社會對同性群體的歧視、社會體系的缺失與不接納造成的。」
性少數親密關係背後,也有傳統性別歧視的影響
在珊珊試圖與朋友講述自己遭受女友的精神暴力時,朋友們的第一反應經常是:「你這個強勢的女漢子,怎麼會被女友暴力對待?」這是因為,她平時的表現更加「男性化」一些。
在一些性少數關係中,存在著「攻」和「受」、「1」和「0」、「T」和「P」這樣的稱謂,一方(「攻」、「T」、「1」)往往被認為是更強勢、更偏傳統意義上的「男性化」的,另一方(「受」、「P」、「0」)則是更弱勢、更偏傳統意義上的「女性化」的。這種角色分工,實際上是性少數伴侶對異性戀伴侶關係中,傳統的男女性別角色分工所作出的一種模仿。
珊珊覺得,外界和性少數群體自己,也都在用性別刻板印象來看待性少數群體。而事實上,暴力是一種行為,不是一種男性性別屬性。然而也因為這種偏見,珊珊這類被認為在性別氣質上「更強勢一方」的受害人,也面臨了更多的尷尬與漠視。
男同性戀者馬修也曾因為性別角色觀念遭遇過男友的精神暴力,「他骨子裡覺得,‘攻’就要做老公該做的事,‘受’就要做老婆該做的事。他甚至要堅持不出櫃,未來進入形婚。我們因為這個發生過很多爭執,他雖然是性少數,但仍然會用傳統的性別規範要求我,甚至訓斥我。」
同語的《中國女同(雙)性戀者家庭暴力狀態調查報告》(2009)中顯示,表現出同性關係中性別角色的伴侶(比如 T 或 P、攻或受),比未表現出性別角色的伴侶,發生親密關係暴力的可能性高出 47.6%。這直接說明瞭,傳統性別規範與同性親密關係暴力的相關性,可能比當事人意識到的還要密切。
「一部分親密關係暴力受害者不被認真對待,這意味著,反對性別暴力工作是不全面的。同時,在社會實踐層面,這群人將變得更加邊緣,他們沒辦法從受害者角色之中被解救出來。而這也將導致,性別刻板印象將繼續固化下去,」陳潔瑜表示。
我們呼籲官方、民間各類機構組織、大眾,在關懷異性戀伴侶中女性受害者的同時,關注男性和其他性別身份的受害者,關注性少數伴侶關係中的受害者。對一種對象的最嚴重的排擠,並不是在話語領域內去反對它,而是把它驅逐到話語的範疇之外,它不被談論,從而被人遺忘,這些他者,從此成為了行走在這個世間的憧憧鬼影。
而我們至少可以做的,是盡自己的努力,營造一種寬容的話語氛圍,允許他們存在。這是我們能夠為他們,同時也為我們自己所做的最少的事情。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