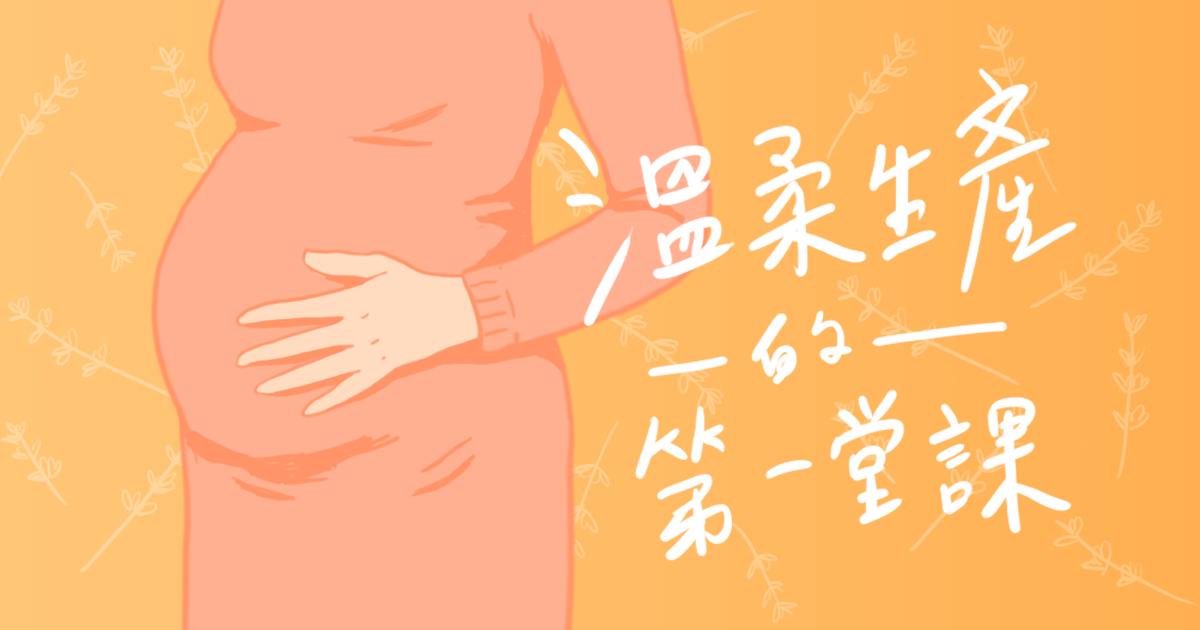助產學是歷史最悠久的生產專業,在歐美許多國家仍是主流的生產照護,如同 2016 年生產的凱特王妃,英國皇室新成員多由助產士接生。由助產士照顧低風險產婦,產科醫師處理緊急、複雜的孕產狀況,是國際間視為理想的分工與照護方式,但在台灣,助產學罕為人知,也常被視為落伍。
文|官晨怡/國防醫學院博士後研究員
二○一五年十月,寶貝誕生於家中浴缸,是計畫好的居家生產,母子均安。我上臉書向親友報平安,友人除了恭喜,表示驚訝的也不在少數,其中一則留言這麼說:「妳居然選擇這麼瘋狂的方式生!但是我敬佩妳!」 在台灣,不在醫院生產是難以想像的。許多居家生產的夫妻為避免家人擔心,事前都不讓家人知道這樣的計畫,我也不例外。平安生產後,爸媽與弟弟們趕來,見到家中新成員健康誕生,欣喜之餘仍忍不住責備我的大膽行徑,他們臉上的驚恐和困惑告訴我,若事前得知,他們絕對不會接受我居家生產。事實上,根據國際健康報告,低風險產婦最佳生產場所依次
是家裡、助產所,然後才是醫院,在台灣,居家生產卻成了「不能說的祕密」,醫院生產被視為唯一的安全選項,然而真是如此嗎?
在醫院生產比較安全?他們沒告訴你的風險
要去醫院生?還是在家裡生?懷孕期間,自己也曾掙扎一番。年近四十,終於有機會當媽媽,自然不願意多冒險,平安生產是我最大的考量。在醫院中,生產被嚴密地監控著,警訊一旦出現,醫療立即介入,這種人為控制下完成的生產,理當最讓人安心,但過去的研究經驗卻告訴我,醫院生產不見得是最安全的。為了收集博士論文資料,我長時間在醫院與診所裡蹲點,近距離接觸台灣醫療生產環境,這些見聞在日後幫我做了人生最重要的決定之一。
作研究時,我很少能在產房裡感到放鬆,因為那是個高壓的工作環境。根據統計,台灣有九十九%的生產在醫院中發生,是助產士接生率最低的國家,造成產科總是擁擠、緊張。產婦被推到走道上,用拉簾隔出一個機動性待產空間,是我在醫院裡常見到的景象。這樣的情境裡,時間控制成為醫護人員的工作重點,制式化管理成為解決結構性困境的辦法,催生、廿四小時臥床胎心音監測、剪會陰等,在許多醫院成為常規做法。
除了管理目的,在醫療觀點裡,生產是充滿不確定性的過程,若要避免風險,並「幫助」產婦完成生產,醫療介入是必要的,然而,這些醫療干預同樣帶有風險。舉例來說,施打催生藥會不會影響胎兒?一位資深醫師曾在門診空檔告訴我,為了「清空產房」,台灣的催生有些過度,而這可能造成胎兒心跳突然上升或下降,必須緊急剖腹產。事實上,這樣的風險早在一九七九年就有國外醫師提出,但台灣卻仍未正視過度醫療干預帶來的風險。
「所有生產都一樣」:消失的自主空間
醫療干預成為常態,意味著產婦的自主性被迫消失。「所有生產都一樣」,我曾聽一位主治醫師這麼告訴實習醫師,那是田野調查中最震懾我的一幕。那天,我一如往常到產房報到,一位產婦正從待產區被推進生產室裡,她的寶寶要出生了。我匆忙換上無菌衣,跟著實習醫師進到生產室,在那裡見到了全武行的接生陣仗。病床擺在正中央,產婦採截石式[1]躺著,正前方站著刷完手的主治醫師與助手,右側一位住院醫師手抓真空吸引器,準備隨時支援。另一側,護理人員站上高台,準備必要時推產婦肚子(這個動作又稱為「壓宮底」)。產婦其實還沒用力多久,這些陣仗就全用上了。現場一陣忙亂,寶寶「被娩出」後,由護理人員抱到媽媽面前,但媽媽已無力抬眼好好看他,而是面無表情地躺著。看著這一幕,我久久無法從心疼與驚恐中平復,只聽見一旁的主治醫師對實習醫師說:「生產就是這回事,以後你就知道,所有的生產都是一樣的。」
或許該說,在醫院裡,生產不被允許「不一樣」。不論產檢結果如何、風險是高是低,產婦一律接受制式化的醫療干預,不得討價還價。儘管個別媽媽與寶寶的生心理條件有差異,每個生產都必須符合醫學定義的標準產程,若有落後,醫療便行介入;不論對生產的期待為何,產婦必須配合醫院規定與運作,個人的習慣、情感與期望,必須置之度外。在讓每個生產都變得一樣的環境裡,疲憊、茫然、壓抑、忍耐,是我最常見到的表情。對於正在經歷的一切,產婦充滿疑惑,但已無力提問。
「我能接受生產變成那樣嗎?」預產期前夕,我這樣問自己,此時居家生產成了再清楚不過的決定。
「我無法想像自己生」:台灣缺乏的助產學觀點
單是了解醫院生產的問題,並不足以讓我敢於居家生產,真正帶給我力量的,是研究期間接觸的另一種生產專業與觀點,也就是助產學。
助產學是歷史最悠久的生產專業,在歐美許多國家仍是主流的生產照護,如同 2016 年生產的凱特王妃,英國皇室新成員多由助產士接生。由助產士照顧低風險產婦,產科醫師處理緊急、複雜的孕產狀況,是國際間視為理想的分工與照護方式,但在台灣,助產學罕為人知,也常被視為落伍。
不同於醫療觀點,助產學認為在大部分狀況下,生產能由母體與胎兒合作完成,接生者的任務就是小心觀察、等待、並適時輔助。這並非一廂情願的「自然最好」,相反的,助產學有其扎實的科學學理基礎。研究期間,我大量閱讀助產學文獻,也有幸結識台灣助產士,參與研習活動與接生,從中學習關於生產的每個環節,從不同產程中胎兒與母體的變化,到子宮、產道間不同肌肉層的相互協調合作。接觸助產學,我看到自然界為生產主體「內建」 的巧妙機制,並常為之讚歎。由於醫療主導生產,民眾難以接觸助產學知識,生產因而被視為危險、困難的過程。再者,醫院裡的時間壓力,讓產婦與胎兒鮮少能依著自身節奏完成生產,除了催生,產婦還常過早被要求用力,導致最後無力娩出胎兒,被迫接受真空吸引、推肚子等全武行對待。在這樣的生產情境裡,靠自身力量完成分娩,宛如奇談。某日,我遇見另一位也帶著幼兒的媽媽,聽見我居家生產,她很訝異,閒聊間,她細訴在醫院經歷種種醫療介入,最後生到沒力、寶寶被吸引出來的經驗。「我實在沒辦法想像怎麼自己生。」這是她最後下的結語,悲傷地總結了助產學缺席對台灣產婦的影響。
居家生產:跟著身體的節奏
相較於多數台灣產婦,我很幸運。因為研究生產的關係,我結識許多致力於生產改革的朋友,有助產士、醫師、紀錄片工作者,還有推動溫柔生產的媽媽,也是後來組成的生產改革聯盟。平日的戰友,成了自己最堅強的接生團隊。我發現落紅後,心情興奮,但不緊張,這一天終於來到。根據之前做的功課,我知道積極產程還得等上一段時間,於是先發簡訊通知朋友,隨即到家附近剪頭髮、採買食物,準備了許多糕點招待參與接生的朋友。我用手機的APP記錄宮縮的長度與頻率,確定進入積極產程後,我發了第二封簡訊,而那已是隔天清晨。
延伸閱讀:溫柔生產宣言:當一個擁有「主體」也尊重孩子「主體」的母親
朋友陸續報到,各自帶了小禮物,包括巧克力、蛋糕和漂亮的育兒背巾,很有派對的氣氛。我穿著寬鬆睡衣,坐在產球上和大家話家常,每當骨盆腔裡的痠痛襲來,我便閉上眼、深呼吸,等待該次宮縮結束,朋友見狀也不打斷,只是觀察我張開眼睛後的反應,確認沒事後再繼續剛剛的話題。接近傍晚時,我感到疲倦,進房小睡,以養足精神與力氣,面對即將到來的生產。
劇烈宮縮在晚餐後出現,朋友見我已無法談笑,教老公用雙手大力擠壓我的骨盆兩側,為我減輕疼痛。儘管如此,當時的疼動已非我能招架,我提出進浴缸的要求,那是我懷孕晚期每夜幫自己舒緩痠痛的地方。很快,我泡進了溫水,但陣陣來襲的產痛,使我忍不住大喊,浴缸旁圍繞著先生和朋友,有人握住我的手,其他人則忙著調整水溫、遞水和毛巾。面對遠超乎我預期的產痛,我數度驚慌,擔心自己無法完成這個過程,但聽著周圍朋友持續報告產程進展,還有當她們告訴我「看見頭髮了」,這真是為產婦打氣的最好方式。順應著身體的感覺,我繼續用力、變換姿勢,最後,終於聽見寶貝洪亮的哭聲。回到房間後,朋友為我和寶寶做了簡單護理,將寶寶抱在胸前,我仔細端詳終於到來的小生命,並請先生取出冰箱裡的香檳,犒賞辛苦的大家,慶祝這美好的時刻。

圖片|來源
這就是我的居家生產,一個美妙、難忘、充滿力量的生產經驗。它發生在我最熟悉、有親友環繞的環境裡,我沒有經歷催生、打點滴、剪會陰等不舒服的非必要干預,也沒有被迫綁著胎心音監控。我的身體自由、心情平靜,專注面對產痛,順著身體的節奏完成生產。這不是無知、大膽,我是在確認自己是低風險產婦後做出這個合理的選擇。
居家生產是一項選擇,但不是唯一終點
最後,要恢復產婦的主體性,居家生產不該是唯一終點。不同產婦對生產有不同需求和期待,生產環境應該多元,改變既有僵化的醫院生產體系、落實生產計畫書、成立專門提供孕產照護的生產中心等,都是值得推動的方向。
另外,我也必須強調,支持居家生產,並非「反醫」,生產畢竟有其不確定性,而醫療也確實拯救了許多寶寶與母親,主張生產不該有任何醫療介入,在許多時候的確是過度天真。但如何讓醫療的角色恰如其分,適時提供保護,卻不過度主導生產,是台灣社會需要思考的功課。
孩子將滿週歲,一路走來,體驗最多的就是孕育新生命的艱辛,媽媽該得到最大的尊重和支持,讓多元、友善的生產環境成為最好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