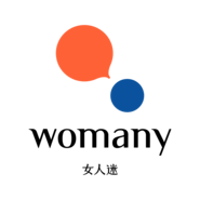在「後宮說」與「政治淫婦」後,讓我們聽更多女性發聲。上海書店邀請政大新聞系副教授康庭瑜、女人迷主編 audrey,對談英國學者瑪麗‧畢爾德的《女力告白》。
當有人嘲諷女力、女權「太高漲」,其實他可能誤解了。女權的權,指涉的是「權利」(rights)。既是人權,就不會因為給予他人而變少,也從不會太高漲。
文|Womany 佳琦
每個人都有這樣的經驗。
有個親身經歷故事想要表達,卻擔心沒有人聽,或者更糟,被當成笑話。
關於同工同酬。你嘗試說道,應該爭取人們不因性別與性傾向而得到不同待遇。他們卻回應,世界上本來就沒有同工這件事情,因此自然沒所謂同酬,也永遠不應該有。是你要求太多了。
關於被性騷擾。你在心裡演練一百次,努力想把事情說清楚,卻被當成炫耀。他們說,那一點都沒什麼,對方只是示好而已。你的不舒服,是自作多情。
關於熟人性侵。他們說,只有道德敗壞的國家才會發生。但當有台灣女性親身說出被熟人反覆性侵的經驗,他們卻說,你沒有報警,就是你自己同意的。
後來你才意識到,不論你說什麼,只要和性別有關,都會非常輕易地否定或切割。
彷彿世上從不存在任何尚未解決的性別難題。
因為安靜太久了,所以從未被人深刻理解
4 月 26 日,星期五夜晚,台大校園外的上海書店舉辦了一場對談,主題是「不再被安靜:女性的權力與力量」,談聯經今年出版了英國劍橋大學教授、歷史學者瑪麗‧畢爾德(Mary Beard)的《女力告白:最危險的力量與被噤聲的歷史》(Women & Power: A Manifesto)。兩位對談人分別是是政大新聞系副教授康庭瑜、以及女人迷主編 Audrey。
因為被要求安靜的時間太長了,所以,女性的聲音,從未被人深刻理解。

圖片|聯經出版提供
2020 年總統大選,黨內初選已悄悄開跑。座談開始前,所有人都有些浮躁。原因是不久前,才發生數起政治人物要女性閉嘴的事件。
「昨天大家應該有看到郭董事長的發言,我昨天還很苦惱自己要舉什麼例子,才能表達女性在公眾場合的被噤聲,完全就是這個例子。」Audrey 說。「一直以來,政治都被認為是男生的事情,女生別插嘴。這件事情有個古典的緣起,在希臘神話,在奧德賽裡。它存在了幾千年,到現在都沒有被好好地拆解。」
第一起,出自於不久前宣布參選總統大位的企業家郭台銘。他於一場專訪中表示妻子反對他參選,但是「軍國大事,後宮不應干政」。無獨有偶,在同一天,作家吳祥輝也於臉書上直指蔡英文與黨外勾結,是「通姦」的「政治淫婦」。
延伸閱讀:性別觀察|從「後宮」到「政治淫婦」,政壇何時擺脫女性噤聲與性羞辱
延伸閱讀:性別觀察】「軍國大事,希望後宮不要干政」且看世界女力領導趨勢
我們非常憤怒且困惑,為何當人們攻擊女性的時候,一定要剝奪她的語言、或使用羞辱的性語言來描述她的為人,將話語塞進她的嘴裡。
這也成了為什麼我們必須坐在這裡的原因。這本書討論的是,女性的噤聲歷史,到底有多長,還有更重要的是,它何時能終結。
「瑪麗畢爾德,是英國女性主義界的網紅戰神,所以衛報這些左派報紙,都會一直為她寫文章,看她去戰英國川普、包理斯強森(Boris Johnson)。這本書就是她的演講稿,賣得非常好。」康庭瑜說。
「它被介紹來台灣,是個相當有趣的時間點。女力在台灣,常常被解釋為女性已經很有力量了。但這本書其實是在談,女人是沒有力量的。當三千年前女性沒有力量,就算了,但是三千年前女性被閉嘴,這些邏輯跟現在是沒有太大兩樣的。」
學術圈的「被閉嘴」:康庭瑜談被噤聲的女性研究者
被問起兩人,一位在學術界,一位在媒體界,是否也有曾經「被閉嘴」的經驗?康庭瑜說,即使在被認為相對「左派」的社會學界,這樣的事情也時常發生。她分享一個例子。
我是社會科學家。照理來說,這裡該是相對「左派」的世界,大家都該是女性主義者,但其實不然。我常看到奇怪的事情。例如前陣子有個學術場合,在場學者專家,有男有女。主席面對男性,說 XX 教授你好,面對女性,則改口 XX 小姐。但是在場有位教授,她偏偏是個女性主義者。當他稱呼她為小姐的時候,她就拍桌站了起來,說:「不好意思,請叫我教授。」
全場都笑了。
康庭瑜接著說:「我相信這位主席絕對不是惡意的,他只是無意識地說出來。我更想知道的是,這樣的事情能怎麼改變?當然你可以微觀地說,這位教授應該此後在每個被藐視的場合都勇敢地站起來,提醒對方這種無意識發言,就是性別歧視。」
但除了個人化的解決方法之外,我們更需要結構性的改變。康庭瑜補充:「例如如果我是個主席,我開了三十年的會,每場都是男性,很少有女性,那我當然會下意識地認為女性不是教授。所以學術界正在推動一件事,就是任一研討會的任一性別,都不該小於三分之一。」唯有結構開始鬆動,才有可能讓每個人無需抗爭,就能享有被當成對等個體的權利。

圖片|聯經出版提供
Audrey:作為性別媒體,結構的問題必須用結構來解
「每個人都會有無意識偏見(unconscious bias)。」Audrey 說,這是很自然的事情,因為當人們從小到大都生活在特定場景下,就很容易認為,某些歧視是很「自然的」。也因此,當有人提出不舒服,不是希望攻擊特定人士,而是希望能拿出來討論、改變。因為很多時候,無意識偏見是集體的,不只有單一個人會有這樣的行為。「結構的問題,就必須提出來,用結構來解。」
Audrey 說:
「我工作的地方是女人迷。我們定位自己是一個性別媒體社群。我們在處理許多議題的時候,時常被噤聲、被勸導、被阻止、被反諷與責罵。我漸漸發現,女人迷的這種經驗,和一個女性被噤聲的經驗,其實非常相似。」
她說,這種「被噤聲」的主要有幾種方式,第一種:「常常我們試圖要談某件事情的時候,這社會都會認為,妳在無理取鬧、在無限上綱。」例如,某件事情到底是不是性別議題?或者是時常會聽到「台灣已經很進步了,還要再提這個嗎?」
「我常常感受到,作為女人迷,我們有相當高的說服成本。我們時常被認為是小題大作、是想太多。這件事情,跟女性經驗是非常相似的。」
例如當你身處某個空間,你感受到不舒服,你試著說:「我剛剛其實有點不舒服」,這件事情成本是非常高的。你會不斷擔心,大家是不是認為我反應過度?你會不斷處於自我質疑的恐懼中。
我剛開始很不能理解,有些文章,同樣在其他媒體和我們的媒體刊載,但只有我們會收到「又在小題大作」的回應與嘲諷。雖然到現在,我也沒有比較好過,但我至少理解這件事情。
「第二個狀況,是我們會不斷被糾錯。一旦你有資格來談某個主題,你絕對不能夠犯錯。你一旦犯錯,你就會立刻被拉下馬,你會立刻、永遠、失去參與某些事務的機會。」她說。「女性失去參與公共事務的風險,是遠遠高過於男性的。」
在這種前提之下,我們時常因為一個很小的錯誤,而被否定所有我們先前的努力。我們時常有失去資格的感覺。這個感覺,其實也和一個進入公共領域的女性經驗,是很相似的。
只要她們一犯錯,就會立刻被說「我們對妳很失望,我們再也不給妳機會了。」這其實也暗示著,女性之所以能短暫地拿到麥克風,是「被給予」的。而且整個社會隨時能夠收回。因為某些人認為,這不是你天生就配擁有的東西。
「第三個,我覺得很有趣。就是作為女人迷,你被期待可以談論某些事情,但也只限於某些議題。」
她回憶。「例如,我還記得我們最開始要試著談女性的政治議題時,我們其實收到非常多問號的留言。」例如,女性媒體,為何要關心政治?你們一直以來都很溫暖、溫柔,為什麼要談這種尖銳的東西?我喜歡的是原本的你們。
Audrey 說:「我突然意識到,原來,我們獲得的話語權,只侷現在溫柔可愛的那一面。一旦我們試著不那麼溫柔可愛了,這些話語權,也會立刻被收回。」
面對無所不在的噤聲,她鼓勵在場的人們,要勇於說出自己的不舒服。「我很想鼓勵在場的各位,當你覺得哪裡不對勁的時候,請勇敢地說出來。」雖然很困難,但只要嘗試過發聲之後,你往往會很訝異地發現,你並不是寂寞一人。
「女權」、「父權」到底是什麼?翻譯給了人們錯誤的想像
我們知道,這種要女性噤聲的厭女情結,是千年傳統,全新感受。過去幾年,全台灣眼見一個不那麼美好的時代朝我們直面撲來。它不只是性別的,世代的,也徹徹底底是人權的──年底公投挺同大敗,厭女政治言論不斷,保守勢力隨時準備席捲而來──面對這種種反挫,女性主義社群灰頭土臉之餘,康庭瑜也從結構說明原因。
康庭瑜說,在台灣有一個錯誤的想像,是人們常常把幸福想像成「零和遊戲」。好像這世界上的幸福,只有這麼多。如果今天我們給女人多一點幸福,男人的幸福就會少一點。但我認為,這個想像並不符合現實。
這種想像,讓「追求幸福」變成一種權力鬥爭的產物。康庭瑜解釋,這可能也跟一個字眼的翻譯想像有關──就是「女權」。
中文世界裡,有些人喜歡把「女性主義」(feminism)翻譯成「女權主義」,這種翻譯方法,它把「權」誤想像成權力(power),而非權利(rights)。這會導致一種誤解:當你談女權主義「高」的時候,男性權力相對而言就會「低」。因為「權力」的定義,是一種單向支配的力量。它可能讓人誤以為「哇,只要女人有權,她就有可能指揮我。」
「其實女權的意思,是 women's rights。權利和權力不同。所謂的人權這種東西,並不會因為給予他人,自己就變少。」
「其實女權的意思,是 women's rights。權利和權力不同。所謂的人權這種東西,並不會因為給予他人,自己就變少。」
當女性從被噤聲中解放,不會帶來男性壓迫
當這種「權力」的零和遊戲錯誤想像不斷被放大,容易導致許多人害怕「會不會女性一旦有機會說話,就只想要男人出來切腹謝罪?」有些人甚至會消極地想,男性生下來,是不是就是道德有問題、就是壞人。
當然不是如此。加害者與被害者的關係,從來不是這麼淺薄的二元對立。
她說,女性主義之所以努力發聲,在於他們希望致力於拿到話語權,對抗「父權」(patriarchy)。這又是一個因為翻譯而常常被誤解的字眼。她解釋:
什麼是「父權」?父權,並不是一群老男人整天站在那裡指揮別人,不管對方開不開心。父權以白話來說,是「一組社會的潛規則,告訴你生下來,只要你有特定的性染色體,這個社會就期待你作某些事,而且不能違背。只要違背,就是道德敗壞者。」
這並不代表男性就是壞人。這也是為什麼,對抗父權,從不等於「對抗男人」。康庭瑜說,女性主義想做的事情,就是嘗試去挑戰這組潛規則,如果規則能改變,它並不會只圖利女性一方。
「我們不要任何人因為他的生理性別,阻止自己去作想做的事情。畢竟有些男性,也不是父權之下的得利者啊。」她說。
延伸閱讀:專訪城男舊事心驛站主任黃重仁:至少別讓男性覺得自己孤立無援

圖片|聯經出版提供
世界很艱難,如果你不舒服,練習說出來
在最後,除了憤怒不平以外,我們還是想要回文章開頭的這兩個例子。隨著選戰將近,我們知道,這些指控、排擠特定性別與性傾向於政治場外的事情,絕對還會發生。
我們憤怒,我們悲傷,但是我們會持續關注、閱讀、聆聽、發聲。如果你感受到不舒服,也請練習說出來,告訴我們。
延伸閱讀:TED Talk 談女性憤怒:我想當個快樂的女性主義者,但真的好難
我們永遠知道,世界不夠完美,時常令人疲倦,但也請相信,在這個世界上,依然會有你的同類。
延伸閱讀:專訪聶永真:這個世界上,有你的同類存在,你並不奇怪
我們就在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