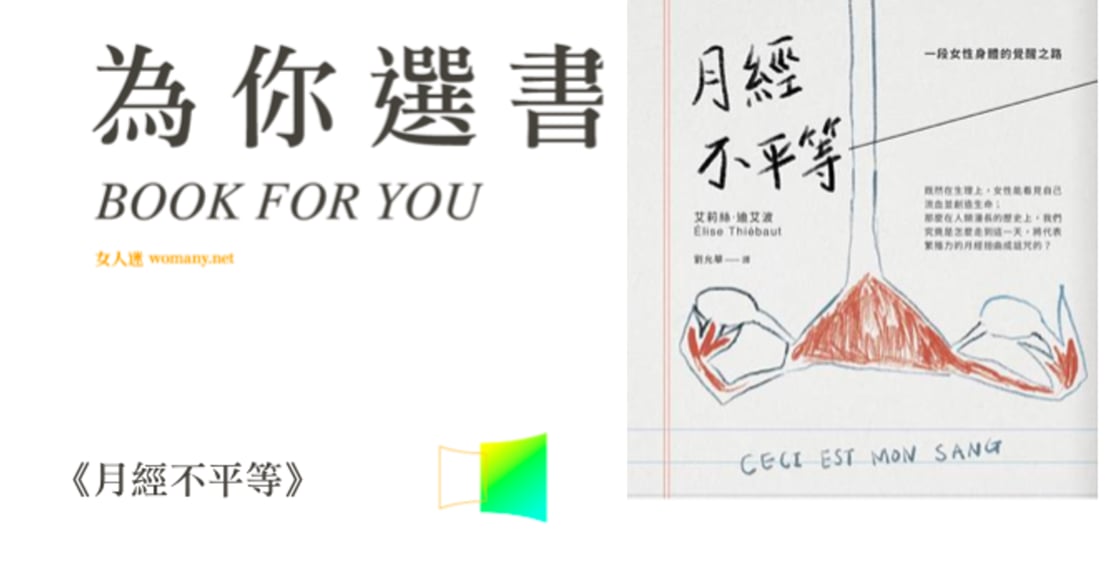女人迷【為你選書】,透過身為「母親」會經歷的各種角色經驗與課題,細看女性從青春期到為人母的煩惱、成長與自我覺醒。
編輯選書原因|
母親節選書,艾莉絲‧迪艾波的《月經不平等》談女性身體意識與月經污名。
母親與少女共有的煩惱,月經連結了女人的生命經歷。《月經不平等》以「月經」為題,重新思考社會加諸於女體的意義與限制。從歷史對月經的歧視傳統談到女性當代正面對的身體戰爭。
當人們在日本擺出有蘋果糖和紅豆飯的盛宴來慶祝「花開」、在巴西人們換髮型、在澳洲人們跳舞時,在西方倖存的初潮儀式只剩下打巴掌。這種暴力─—至少我們可以說─—不是太好的徵兆。
一九六○年代,雜貨店裡還在賣教鞭,小學也始終籠罩在鐵腕統治的陰影之下:犯小錯者打手心、較大的錯誤則打指尖。被打屁股或打耳光構成了日常經驗的一部分。但我家則不太正常:在這裡體罰令人痛恨,我與弟弟擁有在餐桌上說話的權利,也可以任意離席。為了要進一步培養我們正常範圍以外的人格,我的父母還離婚了。
在當時,這種家庭狀態能讓你瞬間失去社會地位,人們才不會去那些父母離異的人家裡作客。儘管合法化墮胎的條文在一九六七年過關,但合意離婚的法案卻要到一九七五年七月才公告實施。因此,我的父母得要發明一些具有恨意的動機,來說服法官取消他們的婚姻。作為兩名幻想家,他們找到了達到目的的方法,便是彼此指控對方拋棄與不貞,但私下還是保持情誼,也常帶著新伴侶相見歡。無論有沒有離婚,他們依舊是共產黨員,也因為這政治使命而保持聯繫。不幸的是,他們不斷帶我去人道主義節與其他的革命活動,且總是在我的經期期間,造成我的痛苦。
推薦閱讀:用經期百科改革印度!最溫柔的 TED 演講:「月經不是疾病,也不是詛咒」

圖片|來源
國中時,我自然而然得選俄語作為第二語言,渡假的地點也因而必須選在友好國度,譬如日耳曼民主共和國 譯註1。我的青春期,有一大部分都在躲避國中校園裡的募兵專員,以及靠閱讀來逃避其他政治活動:閱讀是唯一能讓我父母產生足夠尊重,讓我免於永無止盡的、在新庭市舉辦讓人淋得濕透的音樂會,或示威遊行,或討論共享計劃的枯燥會議的方式。
如果我媽知道賞初經女孩一巴掌是斯拉夫風俗的話,或許她會屈服在這種誘惑之下,邊唱《國際歌》譯註2邊給我來上這麼一記。好在的是沒人想提醒她。根據塔札那‧阿嘎布欽那的研究,在俄羅斯廣泛流傳一則風俗,那就是要求母親或家中的另一位女性,給她初經的年輕女兒一巴掌「好讓她臉頰永遠有光彩」。「在白俄羅斯,人們大力掌摑年輕女性,讓她害怕,也讓她從此以後月經規律,而且就算來潮時臉上也有顏色(因此周遭的人就無法猜測她的月經週期)。在賽爾維亞,要讓年輕女孩幸褔又有顏色,母親會用初經的血稍稍塗抹她的額頭與眉毛。」
基於一巴掌引起的震撼,這個初潮儀式目的也在讓人印象深刻,是從孩子過渡到成人的標記:這是我們最後一次被打巴掌而不還手,就像騎士的初始儀式。但歷史卻證明這個耳光並非結束,而是一場耐力考驗的開始,因為就算幾代過去,女性能還手的次數還是寥寥可數。
紅色同時也是布爾什維克 譯註3的顏色,我覺得我父母應該會把這個生動的風俗,看作一種能刺激我革命情懷的方式。但是,在我成人的過渡時刻,家人遵循的比較像是美洲印第安人的風俗,由父親走出帳幕,向整個部落宣告他的女兒從今天起成為一個女人,而其他人則為他準備草藥薰香。當時我父親長髮及背,呼草量驚人,足以擔起準備草藥薰香的責任。我的母親邀請他和他的伴侶晚餐,慶祝我的初經,並為我準備了最喜歡吃的菜――多芬諾瓦焗馬鈴薯(我祖母的配方)。在晚餐最後,桌上瀰漫著心照不宣的沈默,我父親舉起最後一杯酒敬我,接著用嘲諷的語氣說:「聽說妳已經變成一個女人了?」
那就是句陳腔濫調,當年最紅的妮可‧克霍伊希(Nicole Croisille)的歌「女人,和你一起─—,我變成了女人─—」─—,妮可有著把任何一首歌都變成聽覺攻擊的天賦,但或許對父親來說也有一點諷刺。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在那晚刺耳地回應父親:「不然你以為我之前是什麼?猴子嗎?」

圖片|來源
我還記得在這個夜晚之後,某種東西在我心中沸騰不已,卻說不出是什麼。但今天我知道了,將這種私密事件廣告周知,事實上是一種針對年輕女性的暴力,讓她們突然不再屬於自己。現代並沒有任何儀式慶祝男性首次的夢遺,甚至還取了個好聽的名字叫「初遺」。沒人會想要舉行一場家庭晚宴,跟青少年說:「嗯,顯然你昨天射精了?幹得好,你成為一個男人了,你昨晚夢遺量大,該是學著洗自己床單的時候了。」
在《餐桌禮儀起源》一書中,克洛德‧列維-史特霍斯敘述,幾個世紀下來,美洲印第安人如何將經期(特別是初潮期)與嚴苛的節食連上關係:「在各種不同強加於少女身上的食物禁忌中,可以找到一些共通之處。在北美洲的西部與西北部,也是這些禁忌的傳統起源之處,少女不能飲用熱或冷的流體,只能喝溫的。固體食物也必須是溫的,不能生食(例如在時常生食的愛斯基摩人之處),根據休斯瓦普人所說也不能帶血,另外也不能是冷的;在夏安族那裡,還不能是沸騰過的。」
藉由與初潮儀式有關的飲食生活等規矩,列維提供了幾個這類的例子:「當初潮到來,查科與鄰近地區的印地安少女會被懸空綁在吊床上,在連寡部落多至三日,在奇里寡諾部族則可能多至三個月。」那個晚上,顯然我並沒有意識到自己可能像乾腸一樣被整整掛上兩個月;但我仍然感到某種壓在心頭上的威脅。
推薦閱讀:韓國衛生棉為何貴兩倍?衛生棉要藏好、月經是「那個」的污名文化
在大人們繼續喝酒、抽菸並談論政治的時候,我走上陽台去看星星。那個晚上沒有月亮。父親來加入我,遞上一根大麻,像是遞給我一只訴求和平的印地安煙斗。我們花了點時間抽菸,什麼也沒說,我成為了女人,而他並沒有。接著,我便帶著許多問題、許多衛生棉和一大隻尚未離去的布偶熊上床睡覺。
我這輩子再也沒有碰一根大麻。然而,我還是產生了許多讓我不知所措的、不敢問的、沒人能回答的問題。就好像我剛遇見一個巨大的,而事實上全世界都否認的祕密。
譯註 1 當時的東德。
譯註 2《國際歌》(L'Internationale)。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最著名的一首歌曲或頌歌。
譯註 3 在俄語中意為「多數派」,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的一個派別。布爾什維克派的領袖人物列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