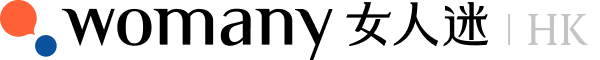2018 女人迷第一季專題「女人的幸福仕事」,透過台日問卷大調查,描繪職業女人的幸福樣態。專訪香港作家卓韻芝,所謂幸福職業,是去感受經歷,看見不斷蛻變的自己。
「我是卓允芝,國語說得哺胎好!」歪斜上揚的音調,硬生把「韻」的四聲重音向上掰彎,攪和粵語的影子,我慢慢聽,終於指認出熟悉的國語音。
這是我與香港作家卓韻芝的第一次接觸。
專訪那天,韻芝與兩位友人前日剛從香港抵台,旋風般地一日行程:早起參加國際書展,簽書會,來不及吃早餐就匆忙趕到女人迷樂園接受專訪,專訪完再旋風般地奔回書展,帶著她蓄積一年多的新書《峰迴路轉》,對讀者演講。
行程滿檔,約訪時間已過半响他們仨人才風塵僕僕抵達。我像愛人終於出現的少女,見到韻芝興奮地啪拉啪拉說了一串,介紹自己,介紹台灣,介紹女人迷,最後一個話音落下。換來三秒寂靜。

卓韻芝不笑的時候,精緻古典的臉上掛著個性鳳眼,直勾勾盯著你,有被老鷹注視之感,我冒出三滴冷汗,那三秒,像一季更替那麼長。然後她瞇起眼睛,撓撓後腦,「我是卓允芝,國語說得哺胎好,請多多指教!」
像看似兇狠的鬆獅犬,挪著龐大身軀在你腳邊蹭。這個努力說著一口夾雜粵語普通話的香港人,好生可愛。
我是棟篤笑主持人,替香港尋一個笑聲
成為全職作家前,卓韻芝從 13 歲便開始職業生涯,像經典劇情,陪友人試鏡電台主持人,誤打誤撞自己上了,一個門外漢就此跨足廣播圈,後來甚至以自創的廣播劇於冷門時段開創高收聽率。如同阿甘正傳裡的台詞: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遠不知道會吃到甚麼口味。
1979 年出生,1992 年開始接觸電台,後來興趣太多,人生有趣的事情太值得探索,學美術出生的卓韻芝開始嘗試導演、編劇、作家與棟篤笑主持人等身份。當社會給出一條中規中矩的路,你可以選擇踏上,或另闢一條。我想卓韻芝永遠是往深山峻嶺跳,往無人之境闖的那類人。
誰說從小到大得追逐成績,升學之路後,找個有錢事少離家近的鐵飯碗端著?對卓韻芝來說,人生有很多可能性,你選擇從事的工作與職業也代表你想探索的領地。天涯那麼大,何必單戀一枝花?
推薦閱讀:【職場筆記】不工作的時候,我專心成為自己
人生像個驚喜盒,更似恐怖箱,你伸手向未知撈取,被驚喜還是驚嚇,都是必經的生命之旅。
卓韻芝的眾多身份中,我對棟篤笑主持人的經歷感到特別新奇。「棟篤笑」文化,是香港盛行的單人喜劇秀,簡單來說,就是一主持人,身配一支麥克風,帶著滿腹的墨水與思想,上台一個人講足 120 分鐘的獨角秀。
相較於台灣與日本社會,棟篤笑這類的單人喜劇秀,在香港多以調侃方式,諷刺時事,針砭社會百態。我問韻芝,如何看待棟篤笑文化在香港當代產生的影響力?她歪頭想了一會,輕鬆語調裡有慎重其事的目光:「很多人以為來看棟篤笑表演的人們,是花錢看主持人耍花槍,搬大斧,斜眼等著看把戲。但事實上我看見現場的每個人,都用一種極其渴望的眼神等我開口,一開口,他們就像找到可以發笑的機會,努力地笑。」似抓到苦悶生活裡的浮木,竭盡全力、拽緊機會地笑,彷彿笑出聲來,細小卻無所遁形的苦悶就不見。

回望歷史,1997 年香港回歸,面對成定局的形勢,香港人文化生活和身份認同的轉變從那年開始悶燒醞釀。90 年代,回歸後,身份認同的問題之於香港人,不僅是困惑,也是抉擇。經過代表火紅中流砥柱的七十年代﹐經濟起飛的八十年代﹐移民潮的九十年代﹐至回歸後的廿一世紀﹐寫《我們這一代香港人》的作者陳冠中指出,香港現今面對的問題並非不是一朝一夕﹐而是過去五十多年累積下來的結果。
面對自我認同的矛盾,有人願撐開雨傘,站成希望的傘花圈,佔領港島市中心 79 天,除爭取普選外,或許更多的港人,是在為一個更遠大的願景,做身份認同的抗爭。有人在夜晚花錢循著笑聲,有些改變不了的事,我們試著笑。
延伸閱讀:從《亂世備忘》看雨傘革命:這不是一場 79 天的夢
「我覺得香港歷經回歸,這些年民眾對於經濟政治的國際情勢、國內民生物質高漲現狀,很多是無奈且無能為力的,這種情況下有些港人的哲學,就是將無可奈何的事,用笑,笑過去了。」從香港歷史談到當代,對韻芝來說,自己從事棟篤笑主持人的工作價值,是想在人們生活感到苦悶的時候,替香港尋一個笑聲。
「你相信笑聲,別人才會笑。我覺得這是屬於『笑』的力量。透過主持,我希望讓社會多點必要的幽默。讓我們用比較輕鬆的面向去面對生活裡的艱難。」或許在這樣的一個年代,我們不必經歷批鬥或流血戰爭,但仍可以用思想,在自己人生野蠻地執著信念,用信念去影響身旁的人,也不失為屬於我們這世代的熱血革命吧。
我是作家,從日常裡出走是為了感受生命
從主持棟篤笑的生命經驗延伸,卓韻芝人生道路岔出很多支線,都是她逼自己以不同角度看待人生,思考議題得到的方向。現職作家的她,書寫文字裡不脫旅行,過去我們談旅行,總會急於定義旅行的意義,但對她來說,旅行跟生命一樣,不能定義,你只能感受它。
「世界很大,很多東西我們必須嚐嚐,很多事物我們必須遇見了才會知道。我喜歡旅行,渴望旅行的原因是,每次旅程裡我都看見不同文化,那些文化開拓了我生命的選項,『原來!除了自己認知的那樣之外,還有很多其他的選擇』,就是在這樣不斷發現新的可能的過程裡,更認識自己一點了吧。」


韻芝跟我分享她有次去加拿大森林健行的經驗,「那天下過雨,滿地泥濘,我試著邊閃避泥黃色的水攤,在濕黏的路上雙腳拐來拐去,生覺走偏一些兩腳就會撞在一起,摔成四腳朝天。顧著閃避水坑,根本無暇看身旁的景色。後來一個聲音喊住我,吆喝一聲,一掌拍到我肩上說:『你就踩下去,直直地朝那些水坑踩下去,走好你的路』。」是的,人生總有走避不及的坑洞,你只管踩下去,踩下去雙腳弄髒了浸濕了都是經歷,踩下去,才發現崎嶇的路是自己走出來的,勇敢踏進水坑,面對看起來會摔得四腳朝天的困難,你會發現,沿途參雜明媚風景與野草辛香。
談到這裏,韻芝主動提起我訪綱列著,卻遲遲沒談到的題目。
幾年前因母親重病,韻芝不忍母親經常受病痛折磨,在一次治療過程中放棄急救母親,這件事一直是她心底最深邃最不想踩踏的水坑,「像妳在訪綱上問,過去我因母親重病,選擇放棄急救的決定曾經讓我非常非常痛苦,也試圖自殺。可是走過來之後,直接面對那些傷痛以後,會發現面對人生的態度,其實就是一種選擇。這也是我在旅行的時,常有的體悟。」
我們常在生命裡堅持找到一個答案,但其實沒有標準答案,那都是我們如何去選擇而已。
這樣的體悟或許是悲痛後的釋然,也是徒步走在人生路裡找到的自適,當我們選擇不去看見人生的可能性時,你也阻止自己擁有更多的選項,去成為更好、更自由的自己。
我是女人,我是還渴望成為「其他」的卓韻芝
在卓韻芝多元的職涯裡,從演員、主持人到作家都是一種創作的思想體現,我好奇她有沒有想藉由這些身份特別關注的議題?她答得有備而來:「這個問題,我先前沒特別想過。可我覺得這是很好的題目,昨夜認真思考了一下。我覺得,我特別喜歡談、特別關注『女性』的議題。」
「過去主持棟篤笑表演時,也有人質疑過我,說女生不會搞笑吧?不能當眾開黃腔吧?可為什麼不?有人說女人不可以做這個不可以做那個,可男人跟女人除生理性別不同,能力上有什麼差異?」
透過談女性議題,韻芝也用生命經驗實踐自己相信的女性議題,她不受社會價值綑綁,或者該說,她從不覺得自己該因為「女性」的身份,去思考自己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我覺得自己內心還是有著叛逆的反骨吧,越多人說女生不能做的事,我偏要做,我從來不覺得自己身為女生不能做什麼,也許是因我沒把自己看作『女生』吧哈哈,我就把自己想成一個『人』,任何事情,有興趣我就想嘗試。」
推薦閱讀:無靠性別,全靠努力:這些女作家站出來打破書寫的性別天花板
透過身體力行,韻芝努力的長出屬於自己的生命樣態,因為自己身為女人,所以女性議題對她來說,是一直內建在體內的感應雷達,支撐她成為現在的自己,很重要的堅實核心。但她除了是女人,她是人,還是渴望不斷嘗試各種可能性的卓韻芝。


同為心有反骨,內建框架抗體的女生,我們話匣子開,從自己當女人感受到的壓迫,談到社會給女人的壓迫,最後我們在彼此眼神裡表示認同,得出一個滿意結論。回想起來,韻芝那時是這麼說的:「不只日本、台灣、香港,每個國家的社會都隱約制約了『完美女性』的想像,」或許要出得了廳堂下得了廚房,最好還要能言善道,教孩子還很有一套。「但其實,什麼是完美的女性?人生完美的路是什麼?每當我越走入世界,看見各國文化的不同、世界的絢爛、人種的多元時,我越質疑社會教育我的『完美』是否真的完美?」
身為女性,一個很熱愛自己工作的女性,一位不想被完美綑綁的女性,對卓韻芝來說,所謂女人的幸福仕事,就是去感受生命,享受生命帶你看見不一樣的自己,「我仍舊不知道完美的定義是什麼,也不知道生命的意義該是什麼,但對我來說,去感受『生命本身』,就是生活的價值,也是我不斷透過職業與自我對話,得到幸福工作的定義。」儘管追尋你心中的小聲音,然後努力實踐它,或許就是屬於女人幸福仕事的定義吧。
推薦閱讀:【女人幸福仕事】2018 調查報告:台灣女權過剩?三分之一女性在職場受差別對待
寫稿的現在,我始終會想到專訪那天,韻芝骨碌碌轉動的雙眼;想起專訪完,陪著等計程車,上車前韻芝給的豪爽擁抱,那麼磊落自在。
我相信不論在世界各地的哪個角落,哪個職涯身份上,她始終會帶著對世界永不生厭的眼,去城市探索,去世界流浪,去站在危險之上,把顛頗過成生活,把遠方走成家鄉。
卓韻芝之於時代,是輕盈的。像水泥圍城裡,偶爾瞥見松鼠殺出重圍在大城跳躍,成為城市人眼裡,最突兀卻也驚喜的風景。持續感受生命,持續推翻他人給的定義,她在滿是標籤的鋼筋叢林裡,從容成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