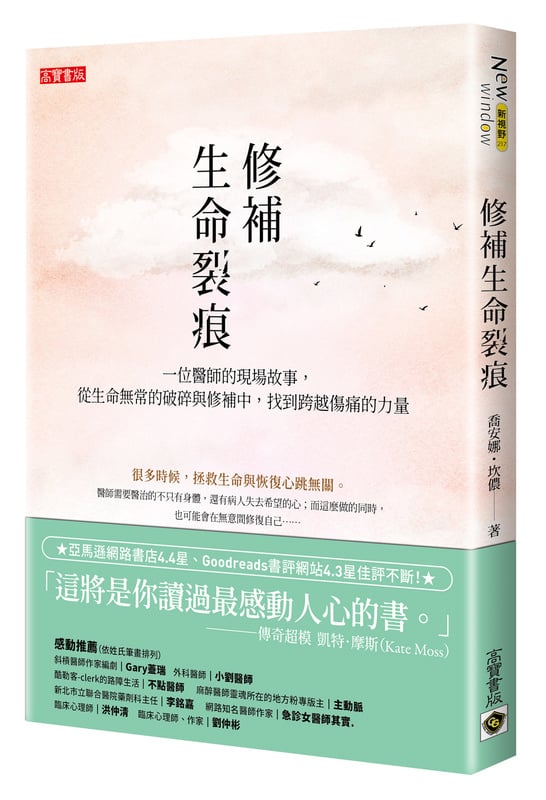錯誤的善意,可能會對人造成傷害。或許我們可以思考,傳遞出去的善良是「同情心」還是「同理心」。
身為醫師,最需要意識到的重要事情之一,就是患者將永遠記住你如何對待他們。
即使經過幾十年,他們也可以立即回憶起醫師對他們說的話、看著他們的方式,以及那些話語和表情帶來什麼感覺。我之所以知道這一點,是因為我自己也曾經是病人,而我也非常清楚記得那給我的感覺。
我經常想起我經歷的那場車禍,通常是在開車時想起,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我很少走車禍發生的那條路,那件事也不常出現在我腦海裡(不過,如同許多重大生活事件一樣,我確信它就在大腦的某個地方,就藏在其他想法的後面)。
有時候,我會順帶提到這件事,通常是有人提議搭計程車或共乘時。我必須搬出一貫的「幾年前我發生車禍,所以不喜歡其他人開車帶我到任何地方」這番說詞,每次我參與有關如何從 A 點到 B 點的決定時,都會出現一種熟悉的焦慮感。
還有些時候,當我開車駛過北德比郡荒涼的山丘,視線中沒有任何車輛時,我就會開始想起那次車禍。

圖片|Photo by Jan Baborák on Unsplash
在經歷過一段難以置信、足以改變人生歷程的創傷性經歷後,大腦似乎會篩除所有重要細節,只留下一些細微的記憶。聽覺的、嗅覺的、結構性的記憶。
我不記得事故本身,但非常清楚記得事故發生前的時刻。我記得我沿著一條筆直的鄉間小路行駛,被許多汽車超車,因為我是個超級慢速駕駛(感謝老天)。我記得爬上山坡。我記得那是一個涼爽晴朗的夜晚。我記得自己在想著回家後要吃什麼。
然後,接下來的記憶就是我睜開眼睛,意識到汽車不動了。我完全靜止。就在我面前兩公分之遠,我的大燈照亮了一片乾石牆,明亮如劇院舞台。我研究了覆蓋石頭表面的整片苔蘚,微小無花但卻如此美麗。
我心裡想,我每天經過這條路,以前怎麼從來沒有注意到這些。但我知道哪裡出了點問題,我知道我不應該在逆向的馬路中央驚嘆著青苔的美,所以我伸出手打了危險警示燈。那時我才看到自己手上全都是血。
我在試圖理解發生了什麼事的時候,一定又失去意識了。當我下次再睜開眼睛時,有個人站在汽車旁邊。他說他是警察,這是他下班途中恰巧碰上的第二起事故。所以,我想我應該是出了車禍。
我想問他問題,所有的問題。但是他在整個說話過程中都沒有看我,我只好盯著他夾克袖子上鬆掉的鈕扣,心裡想著那個鈕扣很可能會不見,然後就再也找不到了。
最後,我被抬出車外。他們讓我坐在警車前座,把我一個人留在混合口香糖及吸塵器吸過的汽車座椅氣味之中,試圖安頓腦海中四處游移的混亂思緒。
附近某處有警用頻道發出嘶嘶聲,在我聽不懂的亂七八糟詞彙之中,我聽到對方說這是致命的撞車事故。致命?那時我沒有意識到還有另外一輛車牽涉其中,我的整個腦子陷入恐慌,試圖思考誰可能和我一起在車上,而且死了。我想過每個我認識的人、關心的人。
我竭盡全力思考所有可能性,最後確定我是自己一個人在車上。但是,如果我是一個人在車上、而這是起致命事故,那麼死的就一定是我了?這個念頭停留了很長時間。
或許實際上只是片刻而已,但那是我一生中最恐怖、最超現實的片刻,我心裡想著這一定就是死掉的感覺了—在一片黑暗中又冷又孤獨,聽著遠處陌生人的聲音。
直到他們把我放到救護車上,綁在一個鋪著毛毯的狹窄地方並接上儀器之後,我才接受了自己還活著的事實。我還在這裡。我只是到很晚很晚才意識到這是多麼不可能。
跟剛剛那位剛下班的警察一樣,醫護人員也沒有看我,他盯著他的靴子。他在一片黑暗的救護車中,透過小窗戶向外望。那個窗戶是用緊急服務車那種奇特的磨砂玻璃製成的,我記得我還在懷疑,既然完全看不到外面,為什麼還要盯著窗戶看。
我試著要和他交談,但不確定那些字到底有沒有離開我的腦袋,從嘴巴裡吐出來。他當然沒有回答。那時的我沒有覺得哪裡痛,唯一能感覺到的就是嘴巴周圍濕濕的,感覺像是鼻子在流鼻水,而我一直試圖用手背把它擦掉。
「不要碰你的臉。」他告訴我。
這是他在整個車程中說的唯一一句話。在我生命的那個階段,我對醫護人員的參考點來自於影集《急診室》中的喬許。但這起事故的醫護人員不是喬許。在我的第二本書中,有一整個篇幅專門描述醫護人員。書中的護理人員都非常友善、令人安心且體貼。
我想,作者有時可能會重述一段生活經歷,並把它轉變成自己希望的樣子。
到達醫院後,我被推過一個充滿注目眼光的等候區,進入急診區,那裡有一群人圍著我的推床。我看不到他們是誰,只能看到他們的前臂和海軍藍色的袖子,他們刷洗過的手,以及在我頭上傳遞的東西。
我被送去進行掃描和 X 光檢查,在經過走廊時,我可以看到天花板上一條又一條的燈管。另外,我在整個過程中都一直希望有人能為我擦掉鼻水,我只記得我想要他們做這件事。
後來,當我在急診區工作時,始終會想起那次的經歷—當你的視線只能看到人們的袖子和手臂,以及天花板上炫目到令人眼瞎的螢光燈時,那會是什麼樣子,又有多麼恐怖。
那群藍制服小組確定我穩定下來之後,又迅速移動到外圍去,而我又被獨自一人留下。就在這時候,她出現了。一個初級醫師。她很年輕,也許只比我大一點,她靠在我的床邊。
「別擔心,」她說,「我的朋友在希臘潛水時撞到岩石,也是傷到臉。」
我確切記得她每一個用字。我記得同情從她的眼中溢出。
「一開始很糟糕,」她小聲說道,「但現在根本完全看不出來。」
我想說,我臉上不過是擦傷而已。沒什麼。他們可能會縫個幾針,然後就要我回家。你為什麼這樣看我?為什麼這麼擔憂地看著我?
但是我什麼都沒說。我只是盯著她。因為在陌生人安慰我的這個短暫時刻,她的話讓我意識到,我變成了一個需要被憐憫的人。
當我自己成為初級醫師時,也體會到了這一點。因為,你總是被自己永遠比不上的聰明人、經驗豐富的人所包圍。你感到毫無意義,感覺自己是多餘的。
你覺得無能為力,所以只能付出自己唯一有信心付出的,那就是同情心。你會說一些話——過多的話——來彌補那種幫不上忙的感覺。急診區的那位初級醫師只是想表達善意,但是她的好意把我嚇壞了。
過了很久以後,我才理解到她為什麼會那樣說。當我被送到病房時,我說服護理師讓我自己去洗手間。我站在裡面,隔著洗手台抬頭望向鏡子。那是我在事故後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新面孔,我震驚地向後退了一步,因為我以為有別人闖進來了。
最後,我終於知道為什麼我一直感覺在流鼻水。車禍的撞擊壓垮了汽車的整片引擎蓋,而我整個人往下滑,膝蓋撞在駕駛座下方的擱腳處。撞擊使我的頭部先撞向儀表板,在那個安全氣囊還沒問世的年代,我的臉撞壞了方向盤。
堅硬、鋒利的塑膠碎片刺進我的嘴巴和鼻子,從骨頭上把肉撕裂下來。被撕裂的肉多得可以—如果你想要的話,可以把我整個臉從頭骨上拉起來,就像面具一樣。我之所以沒有感到痛苦的唯一原因,是因為那裡已經沒有留下任何神經末梢,向我傳遞痛苦的訊息。
我在開車時會想到這種種事情,但卻不太會想到受傷、康復的那幾個月,以及我花了許多年適應新面孔。我最常想到的,是急診區的那位初級醫師。我想著她出於好意但錯置的仁慈,是如何在我本以為自己不可能再更害怕的生命時刻裡感到恐懼。
我思考著仁慈的危險性。
事故發生後的許多個月,我由於口腔受損而無法進食(我必須用一根細吸管喝香蕉口味的安培營養飲料,即使經過多年,每次要開這個處方給別人時,我都還記得它的味道),我也不會說話。
或者應該說,我可以說話,但發出的聲音對其他人而言一點也不清楚(即使在我聽來完全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我被迫寫下所有想說的話。寫下想說的話是一個很棒的練習,它教會你要少一點脾氣,少一點暴躁,多一點專注。
以我當時不快樂和沮喪的程度來說,先把想法寫下來,代表我不會不經思考就拋出那些不快樂而沮喪的字句。我心想,如果所有人在說話時,都能像寫字時那樣謹慎地選擇字句,那麼這個世界可能會讓人比較能夠忍受吧。
我喜歡大家懷抱著同情心和彼此關愛,也喜歡關於小善舉的主題標籤和這種美好精神,但你不能把仁慈像泥巴一樣甩出去,然後期待它會自動黏上正確的地方。仁慈的話語跟其他從口中及鍵盤中冒出來的字詞一樣,都需要仔細留意,並且放在合適的位置。
你真的有可能一不小心就把仁慈「放錯位置」了。仁慈並不是一體適用所有人的。仁慈不是種被追趕的流行,儘管它可能是我們所擁有最強大、最有能力付出的特質之一,但如果欠缺謹慎考慮,它也可能是最殘忍的,像種精心策劃的殘酷行為,會對聽者造成很大的打擊。
因為仁慈善良的回音的確會永遠傳遞下去,不論它是好是壞。而你可能會發現,多年以來,你發自最大善意所說的話,會被一個陌生人想起—當她開車回家,經過北德比郡的荒涼山丘,視線中沒有任何車輛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