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近日發生的各個慘況,卻還能繼續過自己的生活而感到愧疚?其實這是在缺乏感同身受的狀態下的自然反應。
文|陳安
結束疲憊的一天,在通勤回家的捷運或公車上,你低頭滑手機,從螢幕裡接觸世界。
Bottega Veneta 新款雲朵包,和澳洲大火的報導之間,只有幾則動態消息之隔。不論在臉書,或網路新聞頁面上,浮華奢靡、阿鼻地獄並肩而行。而消息接受者(廣大讀者群如我們自身)眉毛一抬,欣賞皮包,查詢價格,估算了一下年終獎金和帳戶存款,有人打定主意要買一個,有人另尋芳草。下一則新聞或許使人皺眉,轉發分享,或許隔天買幾盒綠色紙盒包裝的小熊餅乾。
同場加映:一衣多穿、善用雙腳:在澳洲大火之後,如何從生活保護地球?
聽個音樂,看個短片,捷運到站了。你把手機收起來。捷運站外的空氣有點涼,但不到冷的程度,天氣正合你的意。你忽然想到澳洲的大火,慶幸自己住在台灣。回家的路上你開始質疑,自己是否鐵石心腸。沒錯,你同情澳洲發生的災難,也樂於看到大明星捐助鉅款,但是你沒有打從心底悲傷。你在受傷無尾熊的連結分享按了一個哭臉的符號,但你沒有真的哭,你也不曾心碎。你悲傷的程度甚至不及沒買到吳青峰〈太空備忘記〉演唱會時的難過。
推薦閱讀:「爸爸,我會愛你直到天荒地老」因澳洲大火殉職的消防員,孩子代替父親接受勳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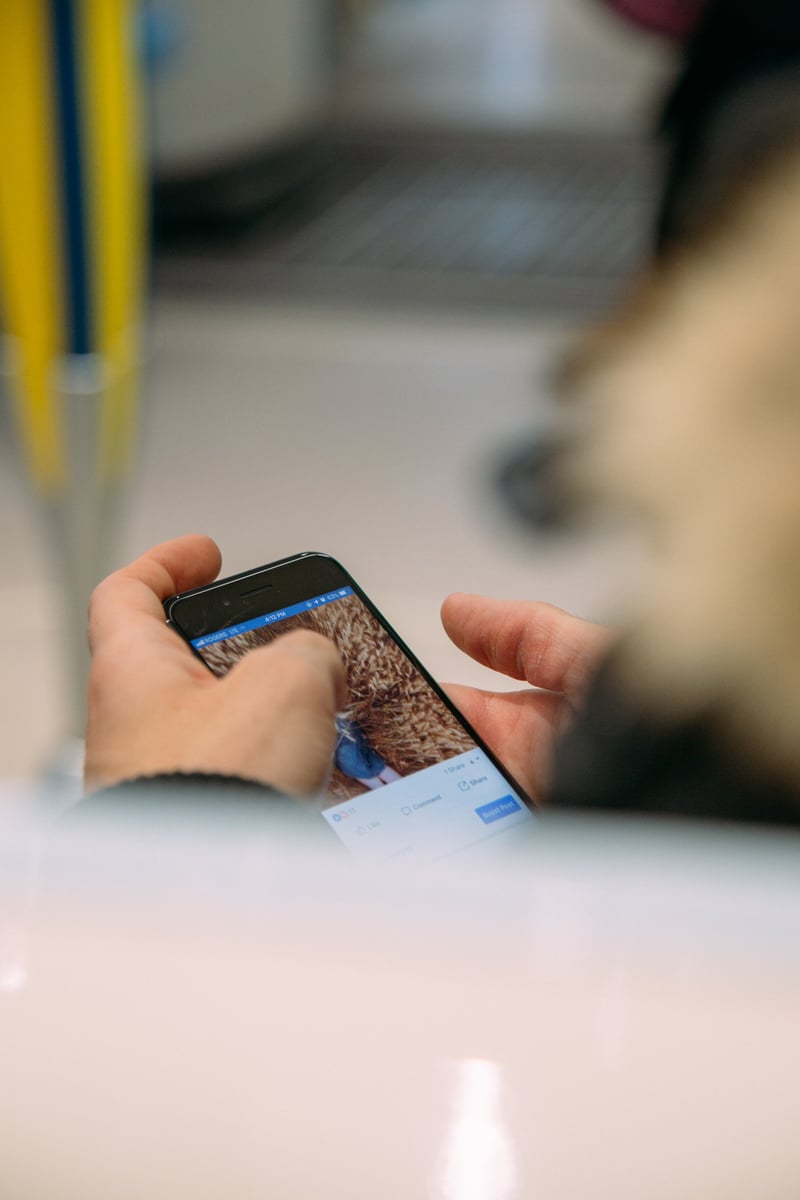
圖片|來源
伊朗和美國交惡,敘利亞的難民欲哭無淚。你瞄過那些數據,「萬」、「十萬」、「百萬」⋯⋯但你記不清楚。回家的路上,你努力喚醒自己的良心,但是想起冰箱裡昨天剛買的巧克力蛋糕,舌頭的渴望強烈過於憐憫。到了家門口,你已經幾乎忘記澳洲和中東,全心都是巧克力蛋糕的滋味。
「我真是個無情的人哪!」你邊吃巧克力蛋糕邊想。但是你知道自己不是十惡不赦的壞人,你也知道大部分人和你一樣,按了哭臉的表情但沒有哭,留言說「看到哭了」但不曾流淚。況且澳洲的天災和敘利亞的人禍,幾乎和你沒有任何關係,不是你造成的,亦不會——至少目前看來是這樣——對你產生影響。
為了讓自己放下最後一點心頭重擔,你找出另一個有力的證據:就在今早,你上班途中,在街頭拉二胡的老人的琴盒裡放了張一百塊鈔票。對,你不是毫無同情心的。於是你切下第二塊巧克力蛋糕,經過浴室的時順手往浴缸裡放熱水,你累壞了,需要放鬆身心。
這樣的現象真的是常態嗎?
早在二十世紀,著名學者 Thomas Schelling 率先提出「可辨識受害者效應」這個概念,說明人們在面對單一個體受害者與大量受害者時,產生的不同反應。在 2007 年,學者 Deborah A. Small、George Loewenstein 及 Paul Slovic 進行了一個實驗,設計兩份文宣,一份包括饑荒的受害者數據,另一份則特別介紹一個挨餓的小女孩 Rokia,並給予受試者一些錢讓他們決定捐款的數目。經過統計後,發現得到單一受害者文宣的組別,捐錢數量最多。這個實驗證明,當人面對數據化的大量受害者,其同情心的能力會大幅下降。更有甚者,當受害者數量從一位變兩位,捐款數目也下降了!也就是說,根據心理學,我們對災難產生的大量死傷,原本同情心就有限,這是人類與生俱來的限制,而非某種性格缺陷。
在 Paul Slovic 於 2007 年後續提出的文章 Psychic numbing and genocide 中,指出同情心麻木和大屠殺的關聯。2003 年持續到 2010 年發生在非洲達佛地區的大屠殺,死亡人數介於五萬到四十五萬之間(由於死亡人數過多,以及資訊流通不易等等原因,死亡人數眾說紛紜)但是得到輿論關注卻極少。
在以色列、巴基斯坦間的衝突,以及敘利亞的戰爭都帶來大量的死亡,然而我們很少談論這些。社會輿論事實上擁有很大的力量,可以改變決策、拯救生命,然而這個社會上對於大量死亡似乎註定缺乏足夠的同情心。

圖片|來源
蘇聯著名歷史人物約瑟夫・史達林說過:「一個人的死亡是悲劇,一百萬人死亡是數據。」似乎所有證據都導向一個結論:我們生來如此,我們沒有錯——我們沒有責任。於是我們繼續吃巧克力蛋糕,泡舒服的熱水澡,心安理得的入眠,對自己冷漠的最後一絲懷疑隨著隔日清晨的煙消雲散。世界正常運轉——有幾個遙遠角落在無聲的崩解,但個人的世界是如此的迷你,以至於除非災難在人跟前跳舞,我們都還能無動於衷的繼續生活。
然而,面不改色地談論大批死亡的難民,以及在澳洲因為大夥及乾旱被射殺的萬頭駱駝,同情心聞風不動——這是大多數人心目中的理想嗎?我不這樣認為。
因為從很多例子可以看出,我們的同情心有很大的潛力。日本 311 大地震的時候,台灣捐款的數目為全球之冠。香港反送中事件,台灣人熱烈響應,積極募資。這兩個事件中,受害者都是大量的、非個體的「不可辨識」受害者(我們不一一知其姓名、背景),然而他們依然引起我們的同情心。這些數據化的受害者,顯然並不僅僅是數據而已。至於背後的原因,我認為和「同理心」有很大的關係。台灣身為一個多地震的國家,人民對於天災便容易感同身受。而我們和香港一樣,受中共政府影響很大,並且台灣人民也經歷過遊行抗爭,自然對於香港面臨的情勢也較容易產生共感。
綜上所述,即便是數據化的災難,只要透過同理心,仍然可以撼動我們的內心。我們不是冷酷無情的。但前提是當我們面對自身的冷漠,能敢於挑戰、突破自己的限制,更多的去瞭解他人的困境,才不至於麻木。在 Paul Slovic 的文章中,他提到藝術創作亦是改變同情心麻木的一個方式。例如文學作品《偷書賊》以及猶太集中營回憶錄《夜》,都和猶太大屠殺有關,透過聚焦在單一受害者的方式,讓讀者彷彿身歷其境,體會到災難的黑暗與恐怖之處,進而培養讀者的同理心。而西班牙畫家哥雅的畫作,以隱喻的方式描繪戰爭,其畫作《巨人》呈現出戰爭時期人民的混亂、恐懼和痛苦。
從演化的角度而言,人類的生存主要以家庭為單位,所以我們情感可擴及的人數不大,由此發展出我們對於大規模死傷無感的結果。然而透過更有自覺的關心社會,以及閱讀小說、看電影和欣賞藝術作品等等,我們方能面對並超越我們先天的限制,在這個資訊量超載的社會,對於苦難永遠保持柔軟的心和救援的雙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