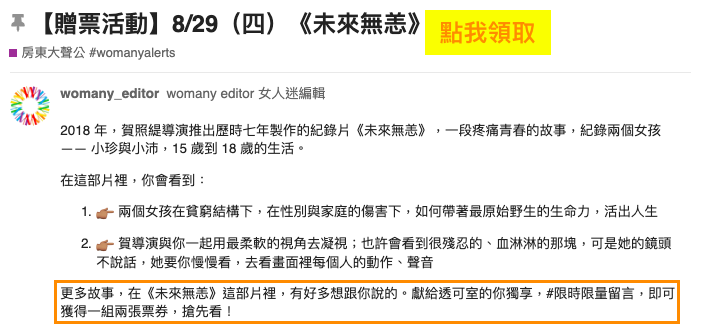專訪紀錄片導演賀照緹,《未來無恙》歷時七年製作,她和兩位主角小珍小沛感情變得很深,成了另一種家人的模樣。看著兩個女孩在生活中跌跌撞撞,卻充滿力量,導演期盼著,在看完這部片子後,我們不再用舊式的受害者腳本看待她們:有時保護者心態,是阻礙受害者療癒的過程。
專訪上篇:最溫柔也最殘忍,少女的 18 歲青春:專訪《未來無恙》賀照緹
家是一種渴望,渴望炒菜香,或者一張沙發
《未來無恙》裡,有關於理想的家的追尋。
拍攝七年間,賀導演和小珍小沛之間的感情變得很深,像是另一種家人的模樣。有時候 messenger 通話完,女孩會對她說:愛你唷。
她也回應:愛你唷。
導演笑意盈盈,一邊模仿著。兩個女孩,將她當作乾媽,裡頭有很深很深的依戀,就像家人。

圖片|《未來無恙》劇照
我問導演,相處七年間,她們有影響你對家的想像嗎?她低頭想了一下,接著像是給了答案,也丟出了問題,她說,這跟人為什麼要有家有關,而每個人對家的渴望,都該有最核心的追尋。
家是一個由具象(House)而抽象(Home)的過程:「你渴望什麼樣的 House,那就是你對家渴望,你最核心的那個東西。」
藉由對某種外物的追尋,我們慢慢組建、佈置一個 House,而對 House 的追求,便是你對 Home 的想像。
但是追求家的過程,牽扯到許多限制,背後有其結構問題。譬如租房,你能夠處理家(House)的自由變小,若你是愛做飯的人,沒有一間好廚房,就很難創造理想的家(Home)。
導演笑說自己很愛煮飯,她甚至沒辦法想像自己的家只有電磁爐,卻沒有牽管線的瓦斯爐,因為對她來說,家是一種氣味,有炒菜香,是大火炒出香氣,為家人做菜的那種氣味。後來有陣子,她對家的渴望,是一張很舒服的沙發,能夠舒展的、不需正襟危坐的,家是一種身體感。
導演看向我,帶著溫暖的笑,她問,你呢?家對你來說是什麼?我愣了一下,回說,是聲音吧。電視機很吵的聲音、有人聊天的聲音。

賀導演曾經問小珍理想中的家是什麼樣子?當時她的回答,是一個夢幻的遠方。聽到答案時,賀導常常很殘酷地去想,或許以她的社經地位,理想中的家是永遠到達不了的地方:「她有對家的渴望,那是因為她在家的關係裡面,幾乎是扮演一個比父母還像父母的角色。」
於小珍、小沛,家可能是一個讓自己受傷的地方,但即便飽受創傷,她們渴望的遠方,依然是家。

圖片|《未來無恙》劇照
讓「受害者」成為「反抗者」,才能翻轉舊式腳本
兩位沒有被社會防護網接住的孩子,她們從大眾定義下的受害者,自己長出力量,站成了主體,成為反抗者,重新敘寫受害者的劇本。然而當一個受害者要展現主體性時,社會不一定會接受,大家要她們符合受害者腳本:要哭、要卑微、最好一點力量都沒有。
「包括各種跟性別有關的當事人,常常都必須用一種⋯⋯被迫必須變成受害、低小的姿態,去吸收這個社會同情的眼光。」她語氣溫柔,卻句句有力:「可是在這樣的位置上,她什麼事情都不能做,她不能有力量,展現力量就會被質疑。」
舊式的受害者腳本,以及社會「保護者心態」,讓受害者認為自己是可恥的、見不得人的。某種程度上,更阻礙了療癒過程:「有一件事很重要。當事人因這件事很痛苦,他必須在有人可以接住的狀態下,去檢視他的創傷經驗,說出一個創傷經驗的新版本,而不是舊版本。」
所謂的新版本,意味著讓自己藉由敘說經驗,站成主體,讓他有力量去面對未來人生。
好比一個在母親控制之下,沒有安全感的人,他可能會想透過愛情彌補空洞。但新版本的人生,能夠藉由敘述,知道安全感必須自己給自己,而不依靠外界。
「這部片的主角也有對過往創傷敘述的歷程,所以透過敘述變成更有力量的人。我們要鋪蓋一個安全的網子,讓他們說出來,讓他們哭泣,讓他們不再自責。」
看著導演,我一直忘不了《未來無恙》,小珍那樣無懼直視鏡頭的眼神,以及小沛追求愛的真摯,是原始且富有生命力的、對未來的企盼。當我們都能站成反抗者,便能重新改寫生命故事。

編輯後記
知道要專訪賀照緹導演之後,一位同事抓著我問:你要訪賀照緹導演?她的紀錄片都很經典啊,《我愛高跟鞋》是傳播學院學生必看耶。我笑著點點頭,心裡可以理解同事們的激動,尤其是在看完《未來無恙》之後。
遇到導演後,我說好喜歡這部片,而她的眼神好溫柔,對我說謝謝。我真的很好奇,在看過那麼多殘酷畫面,為什麼還能溫和地面對這個世界?
她說,十幾年前的她也是強悍的、教條式的,「但硬邦邦的東西沒人要看。一個硬的理論裝進來後,需要透過與世間的相處,才會內化,成為活的東西。」
鏡頭之下,她開始看見許多不得不然,和無能為力,很多事情的發展,不是非黑即白切分就能理解。
「所以我覺得那種柔軟跟溫柔,是不可免,對我來說。那是我跟這個世界接觸的一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