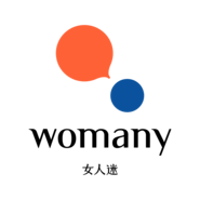性別觀察看向母職,一個母親是怎樣生成的?從懷孕到生產到教養,一位母親離開自己的「人格」,進入了「母親的再社會化」。社會分野出兩種女人,要做一個好女人,要懂得什麼是好母親?讓我們打開母親定義,讓社會主動驅策改變,把身體的選擇還給女人,把孩子的教養方式還給雙親。
文|Womany Abby
生育是誰的責任?六月底 PTT 一篇《一定要生兩個嗎》文章道出一對夫妻的生子計畫。女方以「想重回職場」為由邀請男方帶小孩。最後男方以「不要生小孩好嗎,我不想犧牲這麼多!」拒絕。
兩人的生子計畫宣告失敗。
許多人在下方回帖:「一定是不夠愛,你們不適合結婚。」亦有人認同生子計畫的協議,逐步確認雙方對未來人生的想像,有了孩子後誰帶?有了孩子後誰負責經濟?是誰說,親帶,就是女人自己帶?

(圖片來源:來源)
對女人的母職指點
「女人要有母愛」、「內建母愛才能帶小孩」、「女人負責教育小孩的責任」、「女生比較會操持家務」......。從事件男性也擔心自己成為孩子照護者來看,我們不禁去想,生孩子到底是一種愛?還是一種責任,當男性負擔教養責任說是「犧牲」,何以女性負擔教養責任則是「義務」?
這個社會對女性「以愛為名」的責任期待,其實遍佈在我們的生活裡,我在女人迷曾經做過的討論區(孩子的教養是母親的責任嗎?、家務是女人的責任?你怎麼想、身為女人一定要內建母愛嗎?)調查裡發現,母職想像,是被複製與操演的:
「女性做事比較細心做多一點家會更好。」
「女生潔癖的多一些,下意識就會去整理。」
「女人要有母愛,多一點溫暖正向的特質不好嗎?」
「雌性生物的本能,就會學習如何照料孩子,進而產生母愛。」
以「生物科學母職」強化著女性是照護者的角色:女人有生育力、哺乳力,所以先天具備母姓,以生物學觀點來看,懷孕生子就是「成為母親」與增生母愛的過程。
這種「先天的假設」佐以後天「醫療化母職」的練習:女性由於懷孕、生產過程,全由專業醫生運用科學儀器來處理,在全權控制生產過程之下,成了「醫療化的身體。女性的生育自主權被醫療化,生產、墮胎,都要經過「體系」的認同,漸漸醫療資訊被視為權威,一個女人要如何生養小孩、教養小孩、給小孩吃什麼,都由不得她。以母愛之名,女人們日以繼夜實踐「為孩子好」的母職。
任何一個人,都有資格教育「母親」

(圖片來源:Janet 粉絲專頁)
醫療資源普及,育兒知識百花齊放,更多人試圖凌駕母親之上,教導她如何對待自己「有孕的身體」。譬如藝人 Janet 懷胎與先生在蒙古打卡,就引來以下「提醒」:
「奉勸妳月份越大越要避開去醫療資源較緊張的地方。」
「畢竟妳的肚子月份也大了,要好好的照顧身體,不要太過勞累,興奮!」
「有孕在身,要注意安全及飲食衛生。」
以上提醒拿掉「孕婦」兩個字,似乎也都成立。「女人一旦有孕在身,身體就不是自己的」這句話不證自明。經過體系結婚與生產的「前輩們」被知識體系賦予了權威地位——通過這套規則「成功」的人,就有在任何公共場合教育母親的資格。
延伸閱讀:你並不孤單!Janet 致憂鬱症的告白:身而為人,都有脆弱的時候

(圖片來源:Janet 粉絲專頁)
這麼說有點嚴重,因為上述都是「來自切身經驗的善意關心」,但是回到起點,我們怎麼會以為,自己有權利去善意的「教育」其他母親該怎麼做?
其實不只「決定要不要生」才是生育自主權,在女人懷有身孕的過程中,「生育責任」與身體自主權不斷矛盾。人們都覺得自己有權干涉一個「即將成為的母親」的選擇,人們有權去一起塑造「母親的神聖性」,以鞏固懷孕的文化經驗資產。所以不免在懷孕過程中聽到:這個那個不要吃、動作小一點、不要到處亂跑、孕婦不能性愛、不能健身。女人精密接受著儀器的控制、裸身且去性地站在醫生前被檢視身體,這一副在產科醫療監控和文化規訓的身體徹底失語,所有人都客觀或主觀地告知「意見」。
孕婦被「病理化」,也與人們對「胎兒」與「誕生」的狂喜有關,1965年《Life》雜誌上首度刊登了胚胎在羊水中吸吮手指的照片,胚胎的「在場」,抹殺了母親的「在場」。從此許多國家增生墮胎法令,甚至會以「母親不當管理身體」為由起訴。

(圖片來源:來源)
胎兒與母親,孩子與母親
又例如醫院有「母職親善」設施,推行親子同室,母親與孩子必須 24 小時待在一起、不親餵彷彿就是沒有母愛。2013 年林淑芬立委召開記者會宣告「母職親善對媽媽不親善」,許多母親很想快點「逃離醫院」去月子中心。人類從母嬰一體到母嬰分離的照護關係,應該如何看待?像政府推行的母職親善設施多半按照科學研究擬出的 SOP 與養育手冊,讓母親變成科學的僕人,無法從自然互動中去理解嬰兒的需求,並回應嬰兒的需求。
就像人們對「母愛內建」的期待,母愛像是眾人喊出來的口號,一個女人,怎麼可能沒有母愛?
女人富有強烈的溫暖與同理氣質,永遠願意接納、退讓、溫柔,是集體社會對母愛的錯誤想像。在母親認識「母親」是什麼之前,女孩就必須具備母愛。蘇芊玲曾於《不再模範的母親》一書針對傳統的母親角色、複製在體制裡的痕跡:「為人提供服務、奉獻犧牲、無怨無悔、完全沒了自己的母親角色。除了是家庭裡的母親外,人們還要求在學校、公司、機關裡的女性也化身為『母親』,以提供各式各樣的服務。」
母職無限的情感勞動,分身乏術的她們回應著人類的需求與要求。
「從報紙上看到美國婦女因為傷害胎兒遭起訴的新聞,我就開始思考這種事情是怎麼發生的;身體怎麼變成了一個公共空間,像電話亭一樣被破壞掉。」──Rachel Cusk,《一生的工作:成為母親》
社會極度害怕女性失去母親,因為女人一旦不生殖,社會就難以代代生成下去。女性主義者喜歡說「個人即政治」,亦是反應女性身體長期被公共性、開放性,被評論與指教。
回到大眾為何喜歡對「母職指點」。我們看待女性的觀點自她「成為母親」後就有另一波轉折。對性的雙重標準分野了「生殖功能女性」與「情慾功能女性」,一個檯面上,一個檯面下,服膺體制讓「社會秩序」能繼續運轉。「母親」的名字是登記在家父長制之下,需要經過縝密的條件審核,才能抵達「連男人都不能凌駕、都不能侮蔑」的位置。
從胎兒與母親,到孩子與母親,母親少不了備受指點:有沒有親自做早餐?孩子怎麼那麼瘦?各種「模範母親」條例來教養母親們,手冊裡孩子與母親的關係,太渾然天成、太完美的像刻意捏造出來的戲一樣。母職的傳承從婆媽間來到網路世代、人人都可以教育母親。再再忠告著母親們:你沒有餘地犯錯、你沒有權利放棄,因為你已經被推到「母親」這個位置了。

邱宜君在《做爸媽的一百種方式》提到:「有了孩子之後,我更常覺得自己不再是個『人』,而只是個『媽媽』。我似乎失去了名字,尤其是在因為孩子而建立的新人際關係中,我的名字成了『某某媽媽』,我的某部分存在似乎得依賴孩子才成立。」
當一個男人說:「不要生小孩好嗎,我不想犧牲這麼多!」時,我們應該思考,女性因生育與教養而退步的人生。如果社會還給雙親們更多決定的權利、更多托育支持,或許,我們也不會有那麼多害怕成為病人、失去人格、只剩下「媽媽」名字的女孩們。
除了釋放更多責任給父職,把家庭關係還給雙親,我們也應該重新釐清父母與孩子間的關係。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套成為好爸爸、好媽媽的典範,每個家庭都必須摸索出適合自己的相處方式,育兒生子,是一種情感關係,而非一份工作。
生兒育女不是一種「判斷個人人格完整性」的方式,更不是每個家庭的必選題,也不是進入主流社會的入場券。但我們仍應該進化出一個更友善的生育環境、打開母職的定義,讓一個不隱忍痛苦、追求自我快樂與成長的女性,也能進入好母親隊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