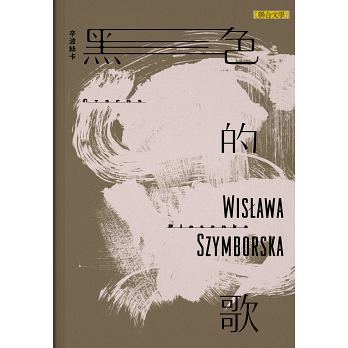辛波絲卡被譽為「詩歌界的莫扎特」。這次選出三首辛波絲卡的詩,讓我們一起看辛波絲卡如何從日常生活的平凡物件中看見詩意。辛波絲卡寫女人,他筆下的女人超越截然的性別二分,沒有刻板與典型的女人形象,哭笑就是純然的哭笑,像人群中每個人的面孔。
天空

必須從它開始:天空。
一扇窗戶,沒有窗台、窗框、玻璃。
只是一個洞沒有其他,
但是開得大大的。
我不必等待一個晴朗的晚上,
也不用仰起頭,
才能看見天空。
天空就在我背後、手邊、眼皮上。
天空緊緊將我包覆,
然後把我抬起來。
即使是最高的山峰
也不會比最深的山谷
更接近天空。
沒有一個地方比另一個地方,
有更多的天空。
雲朵和墳墓一樣
承受著天空無情的壓迫。
鼴鼠和鼓動翅膀的貓頭鷹
都身處天堂。
那些掉落深淵的物體,
從天空墜入天空。
鬆散、流動、有如岩石般堅硬,
明亮並且輕盈的
一小塊天空,天空碎屑,
一口氣的天空,成堆的天空。
天空無所不在,
甚至是在皮膚底下的暗處。
我吃下天空,排泄天空。
我是陷阱中的陷阱,
被寄居的居民,
被擁抱的擁抱,
回答問題的問題。
地面和天空的劃分
不是思考整件事的
正確方式。
它只是讓我能夠
有一個精確的地址,
如果有人要找我的話,
我會比較快被找到。
我的特徵是
讚嘆與絕望。
《結束與開始》,1993 (《黑色的歌》書摘 p. 26-31)
對照筆記:相隔四十多年的天空

辛波絲卡的特色、也是她的詩最為人稱道的原因之一,是她能從一個很小的東西出發,從平凡、普通的經驗講起,然後將這平凡普通的東西提升到形而上的層面,以及哲學的高度。
或者說,不是提升,而是發掘出隱含於這東西本身中的形而上意義(就像〈天空〉中那往下挖,而不是往上飛的鼴鼠),以及哲學意涵。因為對於辛波絲卡來說,萬物都像是一個「回答問題的問題」,這麼地令人驚奇、讚嘆吧。
在〈為了更多的東西〉和〈天空〉這兩首詩中,我們都可以看到這種「由小見大」的意圖。只不過,在二次大戰的背景中寫下的〈為了更多的東西〉比〈天空〉多了一點悲壯與崇高,也有比較多國家的意象(旗幟、軍人、國歌)。
悲壯崇高和國家意象是辛波絲卡早期作品中經常出現的元素,在那個時代看起來很熱血、很符合時代精神,但是在今天就看起來矯情、虛幻 — 畢竟,極端的國家主義可以把個人壓垮,辛波絲卡在波蘭人民共和國時期,應該也經歷過這些。
或許,這是為什麼辛波絲卡在中年以後,就放棄了這種寫作方式,轉而關注生活中平凡偉大的事物。或許,二十二歲的辛波絲卡早已預感到天空的崇高和地面的踏實其實是同樣的事物、其實同樣重要,所以才會在詩的最後兩段提到:我們是為了平日、煙囪裡的煙、不帶恐懼地抽出一本書、一小塊乾淨的天空而戰鬥。
如果我們記得,在戰爭期間,這些平凡的事物其實並不是那麼平凡、理所當然,或許我們更能體會,為什麼辛波絲卡把這些稱之為是「更多的東西」。
推薦閱讀:人的一生不平凡的時間,不需要這麼多
在〈為了更多的東西〉作為尾聲的「一小塊天空」,過了四十多年,成了〈天空〉的開始,也是它的主角與背景。天空到底是什麼呢?我們可以說它是自由、願景、希望──這些都是我們看到天空時,常常會聯想到的事。但它也有可能就是天空而已──那無所不在、無所不包的天空。
生命線
轆轆的馬車聲。
煤炭。
早晨才剛來到。
煤灰在路上留下軌跡。
老女人,妳必須靈活點,
彎腰撿拾那一小塊黑色的煤。
我尋找,這一切是如何在我手上展開:
寬廣的世界,未來的日子,快樂。
我手上的生命線 ──
或許是一個彎腰鞠躬的背。
我的罪過:埋伏等待馬車到來。
巫婆。
臉色發青。
在寒冬中。
1946 (《黑色的歌》書摘 p. 116-121)
在老人院
雅博絲卡,那個過得不錯,總是同意一切,
總是像個女公爵一樣在我們之間穿梭的女人。
而且還做頭髮,還戴頭巾 ──
她的三個兒子都在天堂,也許其中一個會伸出頭來看她。
「如果他們活過戰爭,我今天就不會在這裡。
冬天我會去找一個兒子,夏天去找另一個。」
她就是這麼盤算的。
她十分肯定會如此。
然後她在我們面前點著頭,
問我們那些沒被殺死的孩子在幹什麼,
因為她的第三個孩子,
「一定會邀請她去他家過節的。」
他一定會駕著金色的馬車過來,
而且還是由,喔,白色的鴿子拉著的,
這樣我們所有人都會看到,
並且永生難忘。
甚至有時候瑪莉亞小姐也會在聆聽的時候微笑,
瑪莉亞小姐是護士,
提供我們全天候的憐憫,
除了休假期間和禮拜天。
《萬一》,1972
對照筆記:女人的肖像
雖然辛波絲卡從未刻意強調她女詩人的身分,但是她的詩作卻很有女性特質,也有女性觀點。她從小地方著眼,從日常生活的細節寫大事件,在餐桌上和廚房裡思索人生,而且她的詩總是有一份女性的溫柔(但是不會太過濫情)和悲憫(但是充滿理智)。
推薦閱讀:單身日記:如果受過傷才能夠溫柔
辛波絲卡也寫女人的肖像,為在男性敘事下不能發聲的女人發聲,讓讀者看到女人是怎麼經歷生命、看待生命。她替羅德之妻平反,列舉出她在好奇心之外可能回頭的理由(因為她想家、不想繼續看到羅德、因為疲累、孤寂、害怕、憤怒)。

她為卡珊卓寫下獨白,讓人們看到從她口中說出來的,不只是恐怖的預言。她寫愛人的母親,寫拉扯桌布的小女孩、寫身為青少女的自己、寫因為戀愛而失魂落魄的女人、魯本斯的女人、英雄的母親、自己的姊姊、從火災中救出兒童自己卻犧牲的女老師……。
〈生命線〉和〈在老人院〉也是女人的肖像,而且都在寫社會邊緣的女人。〈生命線〉雖然簡短,但是就像炭筆畫一樣把一個窮困、必須在街上撿煤炭才能獲得溫暖的老女人的形象,寫實地描繪出來了。有趣的是,這首詩令人想到賣火柴的小女孩。小女孩也是點燃火柴才能得到溫暖,不同的是,小女孩在凍死之前有看到幸福的幻影,而老女人則在手上的生命線(也許因為摸了煤炭,線條更加清楚?)看到自己必須一輩子卑微地活著。
〈在老人院〉描繪了一群女人。我們看到外表自信光鮮、盛氣凌人、但內心其實充滿不安、腦袋可能也有些問題的雅博絲卡,也看到面目模糊的「我們」(雅博絲卡的聽眾),以及給所有人提供全天候憐憫及照顧的護士小姐。同樣地,辛波絲卡只用寥寥幾筆就把一個充滿戲劇性的場景呈現在我們眼前。這場面充滿張力,卻沒有對劇中人物提出任何主觀的評斷。
辛波絲卡寫女人有趣的地方是:她以女人的生命經驗和觀點出發,但是她不會刻意去劃分,什麼是「女人的」,什麼不是。她也不會給我們一個「典型的」女人形象(比如典型的賢妻良母、典型的女性主義者)。她筆下的女人會哭會笑,有優點有缺點,就像所有的人一樣。
推薦閱讀:「最美女人」的魔咒:被婚紗綁住的女人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