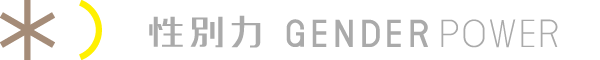從台灣首次選出「女」總統蔡英文,再到目前希拉蕊與桑德斯角逐民主黨總統參選人名額,讓我們從性別的角度思考,我們應該期待更多的女性候選人,又或是我們應該不分「生理性別」,期待更多真正關注性別議題的候選人?
我曾為了究竟該不該因為生理性別來決定我的投票而懊惱不已。我希望台灣可以成為性別友善的環境,希望台灣可以為種族、國族和階級平等貢獻其力。我曾堅定地主張,因為我希望性別比例可以更加平衡,所以我要投給女性候選人。
雖然我很清楚這純然以性別作為圭臬,淪為形式平等的煽動者,但為了數字上的性別比例,為了表面上的性別平等,我曾如此堅信不移。
因為性別,所以你投給誰?
先講程序正義,再論實質正義,這是法律教我的先後順序,形式正義只是手段,實質正義才是目的。基於這樣的邏輯,我曾相信讓女性進入總統府,讓女性坐穩白宮只是手段,是一種宣示和象徵,雖然淪為形式,但或許在達到形式正義後,距離實質正義也就不遠了。
不過,後來有一句話,重擊了我的愚昧:「如果我只因為性別而投給女性候選人,那和我只因為性別而不投給女性候選人有什麼兩樣?」
台灣總統大選已落幕,過程中所激起的性別辯論沒有想像中的熱烈。
但在另外一端的美國,近來黨內初選正吵得火熱,除了共和黨的 Donald Trump 時而口出不當的性別言論,掀起不少性別論戰外,民主黨的兩位主要候選人 Hillary Clinton 和 Bernie Sanders 也因性別而另闢總統選戰的另一戰場。
推薦閱讀:選戰也是性別戰:重點不是換不換柱,而是性別能引起多少關注
年輕女性並不是女性候選人的鐵票倉
直覺上,因為 Hillary Clinton 是女性參選人,所以我假定 Clinton 的女性支持者會比 Bernie Sanders 多,但經過研究,卻意外地發現相較於年長支持者,Sanders 在年輕族群的女性支持者比例較 Clinton 高出許多。為什麼呢?
民調指出,雖然 Sanders 在35歲以下年輕選民的支持度本來就比 Clinton 高,但特別的是,支持 Sanders 的年輕女性選民比支持 Clinton 的年輕女性選民高出20個百分點。新罕布什爾州於今年2月黨內初選的出口民調指出,30歲以下支持 Sanders 的女性選民和支持 Clinton 的女性選民比為4比1,但65歲以上支持 Clinton 的女性選民和支持 Sanders 的女性選民比卻為2比1。事實上,這個現象不是第一次發生,在2008年總統大選的民主黨俄亥俄州黨內初選中,當時24歲以下支持 Obama 的年輕女性選民整整比支持 Clinton 的年輕女性選民多了40個百分點,但在65歲以上支持 Clinton 的女性選民卻較Obama 多出28個百分點。

從美國選戰看女性主義的世代鴻溝
有認為,從年長與年輕女性選民投票喜好的差異,可以發現女性主義在這半世紀以來的世代鴻溝(generational divide)。或許是因為時代的回憶,或是來日所剩不多,在二次大戰後嬰兒潮出生的女性,仍相信女總統的誕生將會是半世紀以來女性主義長期奮戰的勝利。
但年輕女性選民卻不這麼認為,他們相信女性掌權是遲早的事,女性主義早已經歷多種派別的激辯,從純粹鼓勵女性從業、參政,到後來發展出多面向和多層次的兩性分析,甚至是多元性別的倒置和流動思維。女性主義不再只是純然的鼓勵女性自我實踐,年輕世代擁抱性別思考的百花齊放,可見女性主義早已以複數的形式存在,廣納各種派別,富含各種經驗,醞釀各種故事。
年輕選民不是不樂見女總統的誕生,而是年輕世代體會到性別的多元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性別的討論不只停留在純粹的生理性別,而是發散到五花八門的生活議題。(推薦閱讀:誰才是女性主義者的大哉問:期待百花齊放的性別學)
女性主義讓性別只是一種角度,但不是唯一的角度。
性別本不該是唯一考量
中產階級的同性戀女性和貧困階級的異性戀女性,其各別重視性別的程度並不全然相同。基於此,有些年輕女性選民認為,相較性別,Clinton 的政經優勢以及其對社會弱勢的看法,反而讓他們對 Clinton 有所猶疑。
今年的美國總統大選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在年輕選民中,支持 Sanders 者比較願意在網路上發表意見,相較之下,支持 Clinton 者卻顯得安靜許多。有些年輕人覺得支持 Clinton 會讓同儕覺得只是純然因為性別而決定選票,純然為了政治正確而盲目地決定選票,反而成了政治不正確的主張。
近來在青年參政中,純粹就象徵意義而決定選票的思維已逐漸遭到撻伐,積極了解政見、參與討論並將之實踐才是新時代的優良參政,此現象也同樣發生於台灣。Clinton 若要拉攏年輕女性選民,單靠身為女性這個事實是不夠的,與之相比,Sanders 在社會階級、貧富不均和假性平等的政見似乎是成功吸引年輕族群的一大優勢。簡而言之,因為支持 Clinton 會讓性別因素不當擴大,容易模糊政見焦點,所以讓年輕選民有些卻步。(推薦閱讀:第一任「女總統」上任,性別平權的路還很長)
如果只單方面考量性別而發表了某種言論、做了某個行為、下了某個決定、定了某條法律,那將有可能是性別歧視的高危險群。性別不可能個別獨立存在,而是層層交織於切身相關的生活百態。支持 Sanders 的選民相當反對別人認為他們應該要支持女性候選人,支持 Clinton 的選民也非常反對別人認為他們只是單純因為性別所以支持女性候選人。對兩邊的支持者而言,性別固然很重要,但似乎不是最重要的。
推薦閱讀:性別權益不是你的催票工具!2016總統大選缺席的性別政策
有些人戲稱,女孩們之所以投給 Sanders,是為了配合男孩們的喜好,或是被男友們收買了。但事實上,撇開玩笑,女性主義在這半世紀以來的世代鴻溝,不僅限於上述多元交織性的轉變,還包含了另一個女性主義的蛻變:自我認同的覺醒。
同場推薦:女性主義壞女兒:凱蒂洛菲的少女世代叛逆
擺脫母親,創造自我認同與價值
在二次大戰後,隨著消費主義、廣告媒體和大眾文化的興起,個人主義的展現瓦解了母親試圖透過管教拉攏女兒齊同對抗父性霸權的結盟。女孩們學習解放自我,崇拜自由,追求自主,在後續的女性主義潮流中,女孩們於反制父性霸權的同時,也同時轉向罷黜母親長期以來的壓抑和約束。
Clinton 的形象讓這些女孩們聯想到那試圖管教、壓抑和約束他們的母親。之所以支持 Sanders,不是為了與男孩站在同一邊,而是為了與母親站在不同邊,是為了不受傳統女性主義的羈絆,不順從於母親的教誨。女孩們可能難以理解這場選戰對母親來說,將會是女性主義長年奮戰的決勝關鍵,同樣地,母親們可能也無法理解女孩們早已另闢女性主義的新世界,為女性主義栽種新的養分,灌注新的能量。
在2016的美國選戰中,女性主義的蛻變已真實地在世代的鴻溝間湧現,女性主義隨著母親一同長大,但女性主義不會老去,而是在女孩的心中持續更生茁壯。女孩們不會只是一味地將女性送進總統府,他們渴望的,是將性別平等送進投票箱、送進國會,讓性別成為孕育自我認同和多元交織性的肥料,日益壯大。
正如 Sanders 所說,人民不應該依據性別而選擇候選人,而應該依據信念選擇候選人("People should not be voting for candidates based on their gender, but based on what they believe.")。投給女性候選人並不使你成為重視性別的人,投給重視性別的候選人才會使你成為重視性別的人。